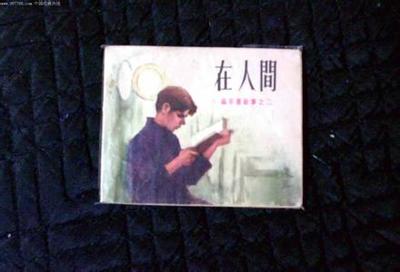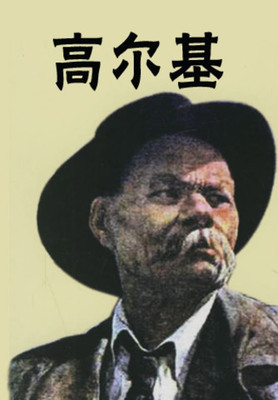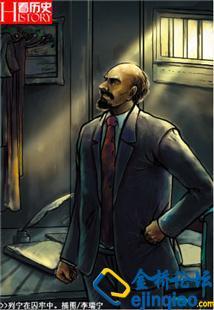摘 要:茨威格将加尔文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形象,是火烧塞尔维特的侩子手,而历史中的加尔文是个改革家,神学家,究竟其功过几分,如何正确看待加尔文?
关键词:加尔文;塞尔维特案;茨威格;宗教改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21-04
16世纪欧洲新教改革既成就了加尔文,也败坏了加尔文。因为宗教改革,加尔文名声大震,加尔文也由此获得神学家、反封建斗士等一系列伟人称号,“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前一个天才是指马丁路德,而后一个天才便是指加尔文。然而,同时也因为宗教改革,加尔文获得独裁者、暴君的称号。“加尔文”一词甚至竟然成了疟疾、宿命论、罪行之类的代名词,其罪名主要源自塞维图斯案。而到底茨威格笔下的加尔文与史学家眼中或历史现实中的加尔文有何不同?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从《异端的权利》中我们可以看出茨威格笔下的加尔文是个十足的暴君,他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专权、暴戾、精力旺盛、残忍。本书描述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是为了反抗罗马教会的约束、桎梏。奇怪的是,新教涌起时,举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等到加尔文到达日内瓦以后,却要求所有的市民发誓只信新教,谁若反抗,谁就得离开该城。反对旧教的专制独裁,标榜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恰到好处就是专制独裁。所不同的是;他现代代表真理,成为正统,而过去他被视为异端,反对个人意志凌驾于众人意志之上的人,现在更专制更无情地要求众人屈服于他个人意志之下,从此个人意志统治众人,加尔文身后有成千上万盲目的信徒,而且还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机器,他的学说成为法律,谁若胆敢违抗,便有监狱、流放、柴堆来给他教训,这是每种精神奴役来结束一切争论的有效论据。通过严密的组织,出色的安排,加尔文成功地使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成千上万迄今为止自由自在的市民转变成一个服从的机器,成功地铲除每一种独立性,为了有助于他独一无二的学说,没收了每一种思想的自由,迫害塞维图斯,压制卡斯特里奥。这种迫害造成恐怖的气氛,城里或国内每一个有权的人物都要屈服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之下,全部官厅和全部权力,市政厅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财政部门和道德、牧师、学校、法院、差役、监狱,写的字,说的话,甚至悄声耳语的话都在他权力的控制之下,在日内瓦只容许存在一种真理,而加尔文便是宣扬这种真理的先知,同时加尔文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甚至派一些“道德契卡”人员深入各家各户,这就是变相的抄家。
虽然茨威格在书中论述可加尔文宗教改革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的界限。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予人类以和平和秩序”①这样人们就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行为之迷。而加尔文就这样应运而生,他给他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成百万人像中邪一样愿意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的“甘于奴役”!但茨威格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宗教改革,没有看出其实质。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阐述“然而,其中必须要考虑一点,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怀的一点是: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的确,旧有的是一种极为松弛的实际上当时几乎让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人们所能想见的最为广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里,对于整体生活样式无休止地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加尔文教派的支配……对于我们而言,是教会所能施加于个人的统治里最令无法忍受的一种形式。”②
看完这段话,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理解加尔文,更中肯对待加尔文制定的教规,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这是当时形势所迫,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应对加尔文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而非感情用事,剑桥世界近代史最后是这样给加尔文定位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加尔文是第二代宗教改革家,是后继者中的巨人。新教运动已经减速,最初的动力已经消耗,已经出现了分裂、疲惫、泄气,加尔文之后新教再次运动起来,高歌猛进,准备为自由发起新的打击。他恢复了基督教情谊活动,他复活了勇往直前去征服并一定要征服的大胆想像。”③
二
不论是茨威格笔下的“恶魔”称号的加尔文还是学界印象中“专制者”之称的加尔文,他地罪状主要起源于塞尔维特案。我们现在对塞尔维特案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看加尔文是否是火烧塞尔维特的侩子手,塞尔维特的死是否是加尔文一手造成的。
在茨威格笔下,塞尔维特也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的学者,他也想在宗教领域独树一帜,1531年出版了《论三位一体之错误七书》,1532年出版了《关于三位一体的对话》,1553年又出版了《基督教的复原》而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与加尔文却有根本分歧,因此二者产生交锋。而加尔文出于忌妒,同时害怕其权威地位遭动摇,所以官报私仇,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先企图借刀杀人将塞尔维特手稿通过告密者呈交旧教的宗教法庭,企图让宗教法庭以散布异端邪说之罪严惩,而宗教法庭虽将其逮捕,但感到这事过于蹊跷,怀疑加尔文想借刀杀人,自己置身事外,于是破例未对塞尔维特严加看管致使塞尔维特越狱成功,这在宗教法庭的历史上大概是破天荒的事情。借刀杀人的计谋未得逞后,加尔文亲自出马最终将其逮捕送进监狱,同时在日内瓦当局的审讯中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白刃战,最终于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烧死,12月23日维也纳宗教法庭也追加了对他的火刑判罚。
这是茨威格笔下的塞尔维特案件,当然其中有符合史实的部分,加尔文对塞尔维特之死负有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为此受到谴责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不论是茨威格笔下的还是史学家笔下的,在塞尔维特案的前前后后,他确实是最积极的一个,从逮捕、指控、起诉书的起草、审讯到死,他都是主要参与者。承认并批判加尔文的错误当然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对整个问题的认识与考察应当遵循真实与公正的原则,要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态度。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把塞尔维特的死全部归结于加尔文一个人身上,有写作的需要,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在详细论述,但其看法有失偏颇,历史真实也并非如此。
首先,塞尔维特的死与其激进的宗教观点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是造成他命运的最主要原因。塞尔维特在《论三位一体之错误七书》中全面否定了尼西亚会议以来的正统教会关于三位一体的理论。他指出,新约圣经里没有“三位一体”“位格”“本体”“本质”等字眼,这都是后来杜撰的,因而是错误的。耶稣基督是真人,上帝之子、救世主,虽具有神性,但次于上帝,并不具有永恒性,道是永恒的,但子不是,圣灵也不是一个位格,它在基督开天后驻留在信徒的心中。在《关于三位一体的对话》中再次系统阐述反对三位一体的观点,在他看来,三位一体是教会腐败的根源,而用来论证三位一体的经院哲学方法又是腐败根源的基础,要消除腐败,恢复真正的基督教,就必须回归古典的《圣经》学术,1553年又出版了《基督教的复原》继续反对三位一体,目的是为了摧毁基督教会。④而当时三位一体为绝大部分人接受,同时基督教的信仰及神学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理论基础上的,反对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推翻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虽然塞尔维特从未有过否定基督教的念头,但其理论的潜在危险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基督只是人而不是神,那他就无法替人赎罪,于之相关的原罪、恩典、救赎等理论势必也会瓦解,上帝的存在也将变成多余的,基督教也将不复存在。从正统的角度来说,这种激进的观点直接威胁到基督教的存在,所以说,塞维图斯遭到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共同批判是自然而然的。当时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也写明:否定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⑤所以说,塞维图斯挑战基督教传统的基本教义,否定三位一体,此惊世骇俗的思想致使他被定罪是必然的。
同时判决塞尔维特死刑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中。茜亚凡赫尔斯玛在《加尔文传》指出塞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自由派与加尔文之间正在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而那时自由派大权在手,他们准备在这重要的事情上向加尔文挑战,甚至想利用塞尔维特打击加尔文在宗教上的权威,同时加尔文一度甚至做好了从日内瓦再度流亡的准备。日内瓦小议会最终判决是;判处
塞尔维特和其所有书籍以火刑。这是一份以全票通过的判决,同时此书中显示了,加尔文听到判决请求小议会将火刑改为砍头,因为砍头比火刑要多一点怜悯,但小议会否决了他的请求。
最后塞尔维特案件过后,本来与加尔文在神学问题有分歧的卡斯特里奥――《异端的权利》另一重要人物,以“苍蝇撼大象”著称的人文主义者,匿名撰文攻击加尔文,提出宗教宽容,他也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火烧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矛头只指向加尔文,而多少忽略了负责审判的日内瓦市政府。卡斯特里奥的攻击赢得了一些人,尤其是为加尔文的政敌的响应。因为加尔文一视同仁的改革措施引起城里一些权势贵族的不满,这些人生活放荡,道德腐败,改革自然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一直以自由为借口,攻击加尔文。就这样加尔文的反面形象逐步深化,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笔下的加尔文将其反面形象塑造达到顶峰,加尔文在他笔下几乎就是希特勒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极权主义野心家,狂热分子,魔鬼,杀人狂,自由的天敌,“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为神权的专政”,“从来不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⑦那么茨威格为何要这么夸张地描述呢?他有何写作目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原因。
三
茨威格1881年11月28日诞生在地处欧洲中部的历史名城维也纳,对于茨威格来说,古老灿烂地维也纳不仅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而且也是他终生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这种”维也纳情结”影响他终身。茨威格把维也纳文化的精神概括为它的“超民族”性,是“西方文化的一切综合”。他把这种精神归功于从古代罗马帝国时代就一直保存下来的兼容并蓄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它完全能够“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有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它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正因为如此,茨威格认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⑧
显而易见的是,在茨威格看来,维也纳的文化精神、简直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温床和摇篮;茨威格成年之后的世界主义理想、人道主义理想、和平主义理想,以及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厌恶和反感,全都可以从他的“维也纳情结”中寻找。
同时必须提及的是,出生于维也纳的茨威格,父母都是犹太人,这一点也与后来茨威格借《异端的权利》抨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密切相关。但与其他犹太人相比,茨威格内心里自幼就没有大多数犹太人所常有的那种莫名的惶惶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他非常明白自己家庭的犹太背景,但他从来没有一丁点儿犹太人的屈辱感。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时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茨威格对犹太人的处境充满亮色的看法,几乎保持到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崛起、大肆排犹之时。⑨同时茨威格也指出“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⑩茨威格一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从早年起,维护自由与独立就是最强烈的本能”。11
以上是对茨威格本人简要的介绍,但茨威格对自由问题的关注和追求,更多地放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上的。在这方面,他受到第一次震动,便是希特勒上台之后宣传的禁书和焚书。同时他与夏德施特劳斯合作的《沉默的女人》几乎完全是出于纯艺术的考虑,而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却因为茨威格是犹太人便遭禁演。这给茨威格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也是多重的,而且在当时竟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不仅惊动了全德国,也惊动了希特勒本人。茨威格深深感到,思想自由在德国已经被扼杀了,到处弥漫着法西斯叫嚣的混浊气息;他一向自以为处于政治边缘,却在一夜之间被动地受到了政治的关照,就连纯搞艺术也难逃厄运;他第一次切身体验到了身为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他那不分种族的西方犹太人的世界主义因受到冲击而近乎破灭……他在内心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迷茫。他曾写信给高尔基吐露自己的心曲。 但茨威格经过短暂的心绪低迷和彷徨之后,再次在内心里振作起来,决心与法西斯的思想专制和恐惧统治相对抗,就在这一背景下,《异端的权利》应运而生。《异端的权利》发表于1936年,当时德国纳粹分子已经全面展开排犹和迫害进步人士,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已成为世界公众瞩目的新闻。因此茨威格写的是加尔文,心里想的乃是现实的欧洲形势,尤其是现实的德国的形势。茨威格虽然是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中的“小人物”卡斯特利奥作传,但是他分明是在借此声讨黑暗的现实,影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那篇充满激情的《引言》,几乎就是一篇尖锐犀利的战斗檄文和宣言。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独裁统治,鲜为人知,茨威格把它从尘封的历史中取出来公之于众,显然不是由于好古之癖,茨威格在《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的胜利和悲剧》中已经指出,在高压之下,只能诉诸于讽刺和影射。用历史来影射现实便是茨威格当时能够采取的斗争方法。12 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他对于日内瓦在这种新教的黑色恐怖统治底下的状况所进行的具体而微的描绘,实际上是对当时,即战前德国现状的影,同时他笔下的加尔文是以现实中希特勒为原型的,因此他写作中带有主观感情色彩有失偏颇的地方。最终他出版的《异端的权利》在德国是不许出售的,同时1936年3月19日根据1933年2月28日颁发的“帝国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赖希纳出版在莱比锡库存的全部茨威格著作被没收,从这一结局也可以看书《异端的权利》对现实的影射意义。他借16世纪一段历史所表达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时代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这些思想的深刻性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既是茨威格毕生对自由、人道、道德、正义、理想、历史等问题不懈探索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被剥夺了自由之后的内心独白。
因此承认并批判加尔文的错误自然是必要的,但完全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把错误绝对化也是不对的,必须用历史的态度,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分析评价。16世纪欧洲宗教信仰自由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进步、理性是启蒙思想家的大旗,但在自由和宽容问题上,他们恰恰否定了它,自由和宽容在他们那里成了独立于历史之外,衡量一切的绝对不变的标准,加尔文自然成为它的牺牲品,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历史简单化了,以为新教就一定比罗马天主教进步。好像罗马天主教迫害镇压异端是理所当然是无可指责的,新教的这些行为则必遭谴责的。这不但是歪曲了历史,同样曲解了自由宽容进步的理念,所以处死塞尔维特既是加尔文的错误,又是那个时代的错与悲,让他一个人承受整个时代的错误,是不公正的。
注 释:
①⑥⑦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M].北京:文化生活译丛,1986.6,193.
②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③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53.
④⑤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引沙夫.教会历史(第8册).166,171.
⑧⑨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92. 16,28.
⑩阎嘉.触摸人类的心灵:茨威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9.
11 刘林海.加尔文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Idid, Cassell and Company Ltd,London,1943.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246.
12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M].高等教育出版社,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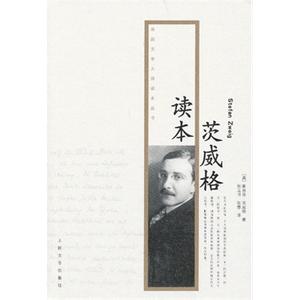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