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它的源头乃是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文明。
1946年,为中国民主奔波了大半生的哲学家张东荪在文章《中国之过去与将来》里写道:“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无济于事。”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呢?
著名学者傅国涌的新作《问史那得清如许》在呈现“活的历史”的同时,便试图探析我们的“源头”何在,挖掘、描绘了中国的“文明之托命者”。他们有胡适、傅斯年、罗隆基、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熊十力等知识分子,有张謇、陈光甫、卢作孚等商人,“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信奉低调的理想主义,脚踏实地,“朝着建造一个个健全的个体生命,从而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目标往前走”。
可惜,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历史朝另外一个方向演变了,这些“文明之托命者”则被打倒、遗弃。但“历史是上帝手中的磨子,转得很慢,磨得很细”,我们当下依旧处在历史的进程中,磨依旧在转,最后的目的地仍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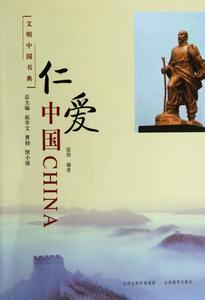
“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一切“流水”都会过去,那些帝王将相的功业、那些光彩熠熠的虚华、那些不可一世的傲慢……都会过去,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源头”恒在,且有“源头”在,便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最终会冲垮“堤坝”,滋润大地,正所谓“历史的正义可以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那些“文明之托命者”便是文明的“源头”。他们埋下的种子,迟早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傅国涌他自己何尝不是当下的“文明之托命者”之一呢,如评价家李静所言:“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便是他对中国当下与未来的“焦灼与隐痛”。
像傅国涌一样的当代“文明之托命者”还有不少,如茅于轼、贺卫方、秦晖等人。而且正如傅国涌所指出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已在稳步成长当中,如本公号提出的周濂、刘瑜、熊培云、许知远、宋石男、萧三匝、李里峰等“70后”思想者已登上历史舞台。
“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思考的问题也更为深入、更为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
相信有胡适、张东荪那些曾经的“文明之托命者”和茅于轼、傅国涌这些当今的“文明之托命者”在,我们的文明一定会得以再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1891一1962),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1962年2月24日,他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
罗隆基(1896年—1965年),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政治学博士。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右派,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中央级右派之一。1949年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28年,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他主张人权、民主、宪政,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人权 法治 民主》。1957年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反右运动开始后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也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观察》云集了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利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力量,左右着当时舆论界的风向。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并一手将南通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
抗战期间,陈光甫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最终,他与胡适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河南、山东等地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他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
他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