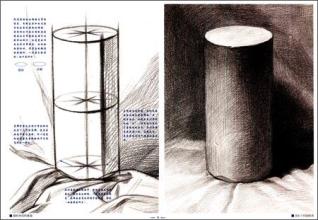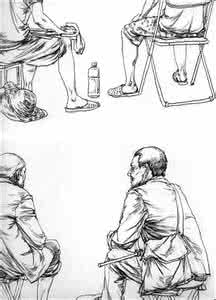
南宋笔记小说家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讲了一个故事:“一日,冲元自窗外往来。东坡问:‘何为?’冲元曰:‘绥来。’东坡曰:‘可谓奉大福以来绥。’盖冲元登科时赋句也。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
冲元是苏东坡的一个朋友。有一天,他从门外进来找苏东坡。苏东坡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冲元回答说:“很好呀,很平安。”在古语中,“绥”就是“平安”的意思。而这一句“绥来”,却让苏东坡想起了冲元登科时所作赋中的一句话,并随口念了出来:“可谓奉大福以来绥。”即“平安而来乃是上天赐予的福分”。冲元一听,立即谦恭地说:“哇!这是当年敲门的瓦砾,您老人家居然还记得!”苏东坡是大名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立刻传遍全国。于是“敲门瓦砾”一词,从此便被用来比喻借以猎取功名的工具。
到了明代,“敲门瓦砾”则正式演化成了“敲门砖”。当时的文学家田艺蘅在《留青日札・非文事》中记载:“又如《锦囊集》一书,抄录七篇,偶凑便可命中,子孙秘藏以为世宝。其未得第也,则名之曰‘撞太岁’;其既得第也,则号之曰‘敲门砖’。”
所谓的《锦囊集》,估计就是一本复习资料,俨如现在的“高考秘笈”、“试题大全”之类。当时这类书少,所以很多应考青年便视之为宝。抄录七遍之后,就觉成竹在胸。一旦没有及第,则怪自己运气不好;如果高中,则称这本“锦囊”是“敲开功名大门的砖头”。
用自己的学识和作品去敲功名和事业的大门,还是值得称道的。唐代张固的《幽闲鼓吹》中介绍,当年白居易到长安应试的时候,先去拜访著作佐郎顾况,并递上自己的作品。顾况看他年纪轻轻,穿戴朴素,又取了个“白居易”的名字,因此就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意思是讲,长安这个地方是京城,物价很高,想在这儿定居立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当顾况打开白居易的诗作,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时,不禁大为震惊,拍案叫绝,马上换口气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能写出如此绝妙的诗句,定居在京城又有何难!我前面说的话,只是和你开玩笑而已。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古人虽然把应考的文章比作“敲门砖”,但还是讲究真才实学。如果白居易当初给顾况拿的不是几十首诗,而是几十两银子,那结局又将如何?白居易所留下的,可能就不是千载美名,而是千载骂名。所以古时的“敲门砖”,只是一种谦辞和戏称。
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完全运用八股文。因此鲁迅在《准风月谈・吃教》中讲:“清朝人称八股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八比文”、“四书文”等,是中国明、清两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考生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而八股文也就专门成为“敲门砖”,除了应考,一无所用。敲过门,随即扔在一旁。
“敲门砖”一词,至今虽然仍被沿用,但已成为一个贬义词。如果谁说学习就是为了“敲门”,立刻就会引来鄙视之眼和斥责之声。如果有人把金钱、美色、权位等作为“敲门砖”,去为自己或家人谋取不正当的功名和利益,更会为人所不耻。
(摘自《绍兴日报》)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