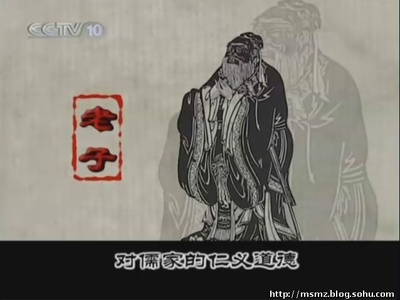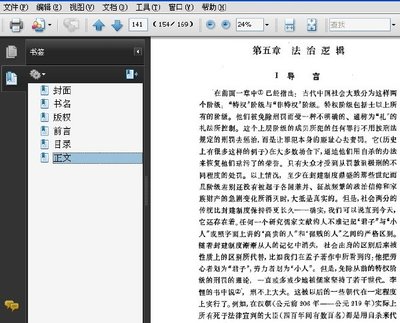金银器之所以在汉代得以大发展,与汉王朝的繁荣统一有着极大的关系。据《汉书》记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500万。可见西汉时期金银器的制造已具有相当规模。当时统治阶级拥有大量黄金,西汉皇室多以黄金赏赐臣下,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等金币投入流通领域。此外,西汉方士李少君提出的使用金银器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理论,更是对汉代金银器的制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上可略窥一二。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数量,还是品种,抑或制作工艺都远超先秦时代。
同时,鎏金工艺在汉代也颇为盛行。汉代工匠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装饰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更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逐渐发展成熟,最终摆脱了传统的青铜工艺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秦代由于年代短暂,遗留的金银器不多。汉代,由于社会长期相对稳定,金银器制作也便得到一定发展。统治者拥有大量黄金,除了制作各种装饰品、生活器皿(aIhUaU.COm)外,还铸造金饼、马蹄金。据分析,汉代出士的大量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除投入流通外,还用于皇帝赏赐诸侯王及诸侯王向皇帝进奉,或用于赎罪、买爵及较大数额的交易和军费支出等。这些金制品是集中多种工艺技术于一体的珍贵艺术品。
汉代金制品制作工艺最重要的成就是创新金粒焊缀工艺,将细如粟米的小金粒和金丝焊在器物之上组成纹饰。河北定州北陵头村汉墓出土一件累丝镶嵌金龙,采用缠绕、锤、焊接和镶嵌技法,用累丝勾勒出龙的面廓和双角,其余的额顶、双颊、颈部及腹部均用极薄的金片镂刻,全身布满粟形金粒,并以绿松石镶嵌银珠,特征毕具,历历可辨,异常精美。金丝多用于编缀玉衣,刘胜墓所出金缕玉衣是其典型。由此可见,金银器制作工艺发展到两汉,已基本从青铜器制作的传统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门类,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代的黄金铸币有两种:一种为类似圆台体,中部空、上部开口,略呈杯形的黄金铸块,通常称作“马蹄金”。另一种就是类似簸箕山一号墓出土的这种扁圆饼状的黄金铸块,称作“麟趾金”,俗称金饼。出土于徐州地区的这些金饼表明汉代金饼的尺寸和重量均不一致,为研究汉代的货币政策、钱币流通以及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国银器的出现比金器晚,约始于春秋时期。银制饰品、器物直到战国以后才普遍出现。战国时期的银制品除了前面提到的银器外,还有银牌饰、玺印、银空首布。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匈奴墓曾出土虎噬鹿银牌饰、双虎纹银牌饰、银扣饰、刺猬形银饰件,与草原游牧民族同样题材的金牌饰风格一致,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掌握了黄金提炼制作的同时,也掌握了提炼难度较高的白银制作。战国古玺中也有少量是用银制作的。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出土的容器有豆、碗、盘等,小件的有带钩、指环、铺首、车马器具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盘,即所谓“镂银盘”,到唐代已成为金银器的主要器型之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