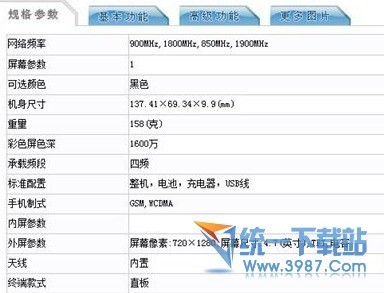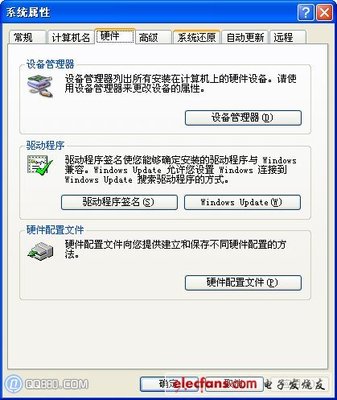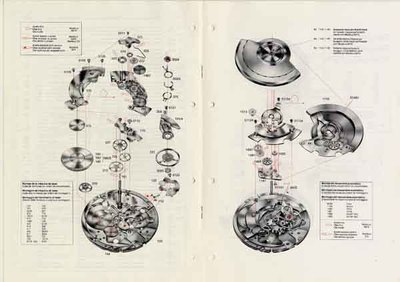我从民俗学与戏剧学家齐如山所编《北京土话》这本近似词典的书中,发现不少天津人感到熟悉的词语:
眼子、楼子(“捅了楼子”《北京土语辞典》(徐世荣编,北京出版社1990版释为“祸事”)。秧子、大头、狗食、老赶、老谣(不实之物)、夹剪(铁钳子)、嘎杂子、二尾(yi)子(气质不男不女的人)、刺儿头、挨刀的、叫街的(乞丐)、乌二鬼、窝囊废、能耐梗(好逞能之人)、糊弄局、穷人美、热火罐子、废物点心等等。
在天津,这些名词或短语,应该是极土极土的,有的只有河东水西的“老天津卫”才明白或会说。不过,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还有一些有音无字或很难找准音儿、能写出汉字的北京词语,在天津话里也存在:
哈喇(油脂类物存放多日产生的怪味)、央格(“他借钱不还。要债还得求大爷,央格他。”)、拉(lǎ)哈(“这个人办事不负责,太拉哈。”)敞开儿(儿化。如“这有十瓶啤酒了。你敞开儿喝”)、掰擦(意为剖析,如“有嘛大不了的?掰擦那个有嘛用!”)摩(mā)擦(用手舒展使平)、叻叻(lēlē。琐碎的废话,如“这个人没正形,天天光会瞎叻叻”)、拉(lá)拉(儿化。“这孩子吃冰棍,都化了,拉拉一地。”)蘑菇、杌凳,等等。
以上词语,均见于爱新觉罗·瀛生所写的《北京话里的满语词》(《京城旧俗》),即都是满族在关外时说的话。有的形、音、义都无法找到准确的汉字。天津话里出现和保留了满语词,这是由于民俗的播布性,京津这么近,尤其在清代乾隆朝,百业兴旺,天津人与北京人交流频繁,上述满语词都在当时京都流行,所以自然而然进入天津话的词汇。这从天津话里的“糟改”一词进入北京话词汇的史实(见《北京土话》),也可得到证明。再如满语中有“哩踢拉塌”一词,天津话词汇中则有“踢哩邋遢”一词,二者语音(尤其是声母)、语义都相近,从民族、人口历史考察,自然是满语在先,这就说明,天津话这种词语语源来自北京话中的满语。很显然,往往被某些文人看不起、说是粗俗的天津话(特别是其中的俚词俗语),其实与北京话同源,连语音都是原腔原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