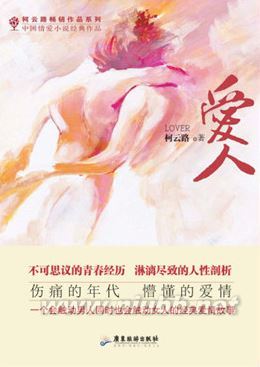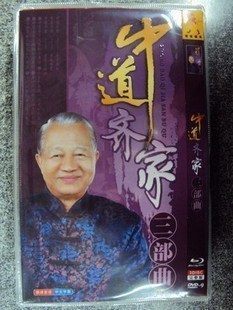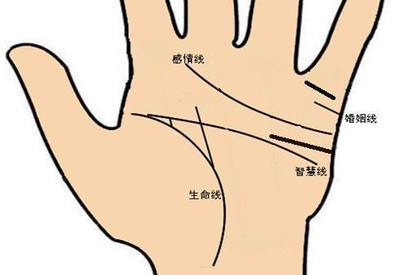婚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但就其科学含意而言,那不过就是指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一代接一代繁衍下来,正是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才得以实现的。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它也是一种历史地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现象。这正是人类的自身生产与一切动物的种的繁衍的本质区别。
谈到爱情,质言之就是精神上的两性关系。这是具有意识的男女之间在精神上对异性的追求和爱慕,并且,它总是面向婚姻,追求或憧憬着某种所谓美满的婚姻,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是婚姻在精神领域中的升华。可见,爱情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人所独具而其他一切动物所没有的。当我们说到动物的“爱情”时,那只是一种比喻,动物只有本能,并无意识,自然也谈不到爱情。
所以,婚姻和爱情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婚姻是两性关系的物质形式,爱情是两性关系的精神形式。并且,只有婚姻和爱情的统一,才是符合人性、符合人的本质的。有爱情而没有婚姻,爱情就不能在两性关系的社会物质形式上得到实现,有婚姻而没有爱情,那这种婚姻形式中的两性关系又与动物何异?不过,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并不取决于爱情,而是取决于婚姻,取决于婚姻这种社会物质形式按其自然规律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仅以人类社会中个体婚姻形态的演变,谈谈这个问题。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个体婚姻形态是对偶婚姻。对偶婚姻的特点是:(1)它并不以排他性的同居为前提;(2)这种婚姻的缔结和解除皆取决于男女双方的自愿——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另一方就不能强制对方结婚或者不离婚。当然,自愿并不等同于爱情,自愿可以是出于爱情的自愿,也可以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自愿。但无论如何,这种婚姻形态是允许爱情在其中起作用的,爱情和婚姻相统一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可是,这种婚姻形态的基础并不是爱精,它的物质前提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对偶婚姻基础上组成的对偶家庭,是一种男女双方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家庭,其中包括男女的自然分工和抚育子女等等。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对偶婚姻就被一夫一妻制婚姻所代替了。这是一种丈夫压迫妻子的婚姻。一夫一妻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男系继承权的需要。男子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传给确定无疑是自己所生的男性继承人,就要求妻子严守贞操,在把她变成家庭女奴隶的同时,也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在这种婚姻形态中根本没有爱情的位置。古希腊的男子就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爱情,而把性爱寄托在艺妓身上。我国战国时代的大将吴起,为了取得鲁国人的信任以率兵攻齐,就将自己原是齐国人的妻子杀死,毫无怜悯之意,也不为社会所非难,终于得到了兵权打了大胜仗,他与妻子当然没有爱情可言。恩格斯说过,现代性爱的第一个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这种爱就根本不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所包容。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骑士“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的爱,它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对立物,是一夫一妻制所逼出来的。如果说在对偶婚姻的条件下,婚姻和爱情还是人类两性关系上一个相对一致的统一体的话,那末在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它们就分裂为统一物的两个鲜明地互相对立的极端了。一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另一方是没有婚姻的爱情。这就是几千年文明社会婚姻和爱情的本质关系。如果说,只有存在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本质的,那么很显然,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是一个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异化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社会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
现在怎么样?现在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以男系继承权为前提的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为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社会主义时代的婚姻是一种经济上男女平等的个体婚姻。但是,以这种婚姻形态为基础,仍然要组成个体家庭。这种家庭仍然是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的单位。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所决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至少在消费领域里还要受到一系列经济因素的制约,而这些经济因素一般与爱情是无关的,有时候还会与爱情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说爱情与婚姻完全取得了一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无论婚前的恋爱问题上还是婚后的家庭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关系都常常受到某些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就使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在客观上受到一定的阻碍,这是现时代的婚姻所难以避免的。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作为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单位的职能也将消失,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将不复存在,因而婚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将最终消亡,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增长。到了那个时候,“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婚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但就其科学含意而言,那不过就是指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一代接一代繁衍下来,正是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才得以实现的。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它也是一种历史地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现象。这正是人类的自身生产与一切动物的种的繁衍的本质区别。
谈到爱情,质言之就是精神上的两性关系。这是具有意识的男女之间在精神上对异性的追求和爱慕,并且,它总是面向婚姻,追求或憧憬着某种所谓美满的婚姻,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是婚姻在精神领域中的升华。可见,爱情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人所独具而其他一切动物所没有的。当我们说到动物的“爱情”时,那只是一种比喻,动物只有本能,并无意识,自然也谈不到爱情。
所以,婚姻和爱情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婚姻是两性关系的物质形式,爱情是两性关系的精神形式。并且,只有婚姻和爱情的统一,才是符合人性、符合人的本质的。有爱情而没有婚姻,爱情就不能在两性关系的社会物质形式上得到实现,有婚姻而没有爱情,那这种婚姻形式中的两性关系又与动物何异?不过,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并不取决于爱情,而是取决于婚姻,取决于婚姻这种社会物质形式按其自然规律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仅以人类社会中个体婚姻形态的演变,谈谈这个问题。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个体婚姻形态是对偶婚姻。对偶婚姻的特点是:(1)它并不以排他性的同居为前提;(2)这种婚姻的缔结和解除皆取决于男女双方的自愿——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另一方就不能强制对方结婚或者不离婚。当然,自愿并不等同于爱情,自愿可以是出于爱情的自愿,也可以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自愿。但无论如何,这种婚姻形态是允许爱情在其中起作用的,爱情和婚姻相统一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可是,这种婚姻形态的基础并不是爱精,它的物质前提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对偶婚姻基础上组成的对偶家庭,是一种男女双方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家庭,其中包括男女的自然分工和抚育子女等等。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对偶婚姻就被一夫一妻制婚姻所代替了。这是一种丈夫压迫妻子的婚姻。一夫一妻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男系继承权的需要。男子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传给确定无疑是自己所生的男性继承人,就要求妻子严守贞操,在把她变成家庭女奴隶的同时,也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在这种婚姻形态中根本没有爱情的位置。古希腊的男子就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爱情,而把性爱寄托在艺妓身上。我国战国时代的大将吴起,为了取得鲁国人的信任以率兵攻齐,就将自己原是齐国人的妻子杀死,毫无怜悯之意,也不为社会所非难,终于得到了兵权打了大胜仗,他与妻子当然没有爱情可言。恩格斯说过,现代性爱的第一个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这种爱就根本不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所包容。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骑士“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的爱,它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对立物,是一夫一妻制所逼出来的。如果说在对偶婚姻的条件下,婚姻和爱情还是人类两性关系上一个相对一致的统一体的话,那末在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它们就分裂为统一物的两个鲜明地互相对立的极端了。一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另一方是没有婚姻的爱情。这就是几千年文明社会婚姻和爱情的本质关系。如果说,只有存在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本质的,那么很显然,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是一个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异化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社会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
现在怎么样?现在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以男系继承权为前提的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为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社会主义时代的婚姻是一种经济上男女平等的个体婚姻。但是,以这种婚姻形态为基础,仍然要组成个体家庭。这种家庭仍然是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的单位。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所决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至少在消费领域里还要受到一系列经济因素的制约,而这些经济因素一般与爱情是无关的,有时候还会与爱情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说爱情与婚姻完全取得了一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无论婚前的恋爱问题上还是婚后的家庭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关系都常常受到某些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就使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在客观上受到一定的阻碍,这是现时代的婚姻所难以避免的。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作为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单位的职能也将消失,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将不复存在,因而婚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将最终消亡,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增长。到了那个时候,“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