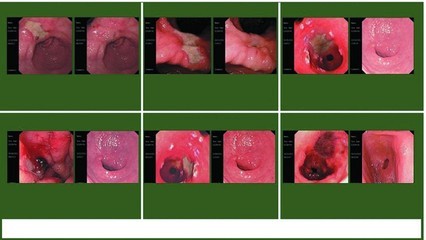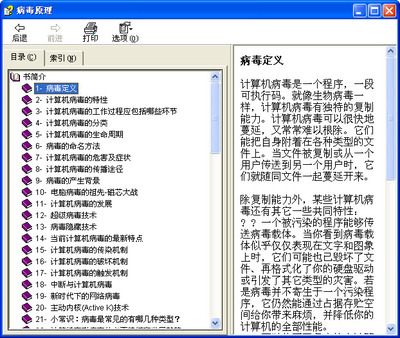1.“龙雷之火”属病理状态
首先,要深人剖析,必须了解“龙雷之火”本身的含义,不可简单跟从大流一概并论。
“龙雷之火”的说法为先哲所创,就其含义也论述众多,到如今后人仍然似懂非懂,究其原由除了大家们本身在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外,实为后世之人学习研究往往追求速效,阅读时不顾上下行文,认真领会,善犯断章取义之拙。
1.1龙雷火之的分析 现人论及“龙雷之火”往往习惯于将其分成生理状态下和病理状态下两种情况进行描述,以示“龙雷之火”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性和作用,但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实不可取,“龙雷之火”本是对机体异常反应的一种描述,何来“正常情况下”之说?
仔细端详,原因有二:
1.1.1“龙雷之火”代表的是一种非平和的自然现象
古人理解事物的方式不同现今,原始粗陋的科技条件让那时的贤者们多了一份顺应自然的东方智慧,面对种种问题他们善于取象类比,“龙雷”亦是通过实践与思考总结出的生动范例:夏季酷炎,湿热胶着之时 常可见天色骤暗,乌云浓密,忽而雷霆大作,眨眼穿梭 于云雨之间,犹如蛟龙翻腾于海面之上,故古人冠以“龙雷”,蕴有一份上升,迅速,猛烈之意。莫枚士言:“龙雷之起,正当天令炎热,赤日酷烈之时,未见天寒地冻,阴晦凛冽,而龙雷作者。”赵献可亦言:“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又问龙雷何以五、六月而启发,九、十月而归藏?盖冬时阳气在水土之下,龙雷就其火气而居于下;夏时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皆可为据。
即以肾脏内藏元阴元阳,为水火之宅,试问假若阴平阳秘,水火共济,升降平调,出人有序,又岂能出现云雨大作,湿气重浊中龙雷逆窜之势?难道人体正常生理活动可繁盛至如此暴烈?
1.1.2先哲们探讨病因病机时常提及“龙雷之火”
无数先人每提“龙雷之火”,或论病机,或论治法,皆昭示人体反常状态,否则何需探讨理法方药?而张锡纯则直言:“方书谓下焦之火于命门,名为阴分之火,又谓之龙雷之火,实肤浅之论也,下焦之火为先天之元阳,生于气海之元气。盖就其能撑持全身论,则为元气,就其能温暖全身论,则为元阳。此气海之元阳,为人生命之本源,无论阴分,阳分之火,皆于此肇基。”可明窥端详。
1.2雷龙之火如上情景,“龙雷之火”诞生于湿气弥漫,云雨遮日之时,天地间阴气重浊,然独见强光闪烁,逆天而行,可见“龙雷之火”实有阴阳错杂,虚实并见,寒中串炎之意,“龙雷”的运用更多的是对特定情况下疾病产生机制的一种形象描述,其代表的含义涉及五脏六腑的牵连变化,绝不可用正常生理状态之下的肾火,肝火或者是人体真阳等名词简单地诠释。以此结论龙雷”实为病理之征,而非正常生理现象。
2“龙雷之火"属"阴火”,治以甘温之品
2.1“阴火”与“阳火”之别
“龙雷之火”究竟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病变,自古以来医家多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阴火”与“阳火”之别。
就目前情况而言阴火”与“阳火”仍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但从历代医家论述“龙雷”过程来看,“阳火”指的是真热,而“阴火”是一种假热,假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肾阳虚极,不能潜藏而反浮越,以致虚亢奋,而见阴盛格阳的阴火证;二是指脾气虚甚,以致血液亏虚,气无所附,虚阳亢奋,而见脾虚发热的阴火证。
这其中,朱丹溪、唐宗海、俞根初等认为是阴虚之火;张景岳、李用粹及明清时代大部分医家则认为是阳虚之火。究其缘由,“龙雷”之说由来已久,流传后世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大家经过实践感悟后的理解诠释,难免产生分歧,众说纷纭。
2.2从起源到分歧的产生
据先人考证,“龙火”一词起于王氏《黄帝内经》,如《二火辩妄》曰:“子和,丹溪之徒以龙雷火释相火,其言实原于王太仆按。”,按《至真要大论》中“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句王冰注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烘,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褥湿而焰,迂木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光扑灭。”可谓龙火的最早出处。
从王冰的论述来看,“龙火”的治法应隶属于“反治”范畴,再结合“阴火”与“阳火”的病理特征可知,王冰在注释《素问》时认为“龙火”属“阴火”。
唐代王氏之后,医家普遍少有提及“龙火”,自宋陈无铎曲意逢迎,释君火在于心肾,相火隶于五行,金刘完素进一步分论“君相之火”,金张子和直接称“相火者,犹龙火也。”之后,随着元朱丹溪掺入“雷火”一说,“龙雷之火”开始为后世继承与发扬。
朱丹溪认为:“其所以便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丹溪常发“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论,他认为,火热上炎皆因肝肾相火妄动,而“龙雷之火”出于肝肾之气,故 临床上重用补养真阴之法以制约龙雷之火。
唐氏、俞氏所论“肝火为龙雷之火”亦与丹溪大同小异。
从丹溪等的学术观点可以看出,他治疗“龙雷之火”时采用的是“正治”法,这与王氏《素问》的观点刚好相反,分歧在此产生。
2.3支持“阴火”论者众
既已丹溪之医法受之于先哲,竟反其道而行,不免发人思考其中流传变化的过程,孰是孰非似乎难以辩解,但仔细探索丹溪之后各大医家的理论著作可以发现,追随逢迎丹溪者少,支持赞同王氏者多。
下面列举较有代表性的几例:
明赵献可在《医贯相火龙雷论篇》中言:“人火者,所谓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焰,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得湿则热,遇水则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勿穷方止矣。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炎光扑灭。古书泻火之法,意概如此”。
清喻昌在《医门法律》阴病论篇中言:“昌每见病者,阴邪横发,上干清道,必显畏寒腹痛,下利上呕,自汗林立,肉润筋惕等症,即忙把住关门,行真武坐镇之法,不使龙雷升腾霄汉。”
清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论两腿冰冷症治时言:“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气散漫,则阴邪立起,浮肿如冰之症即生。古人以阳气喻龙,阴血喻水,水之泛滥,与水之归壑,其权操之龙也。龙升则水升,龙降则水降,此二气互根之妙,亦盈虚消长之机关……”。
不仅医界诸子争鸣,药学典籍里也不乏代表性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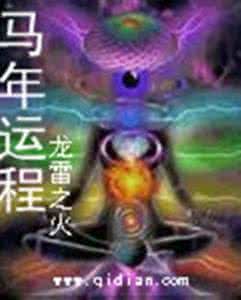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火部第六卷中言:“天之阴火二:龙火也,雷火也(龙口有火光,霹雳之火,神火也)……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诸阳火遇草而焰,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故人之善反于身者,上体于天而下验于物,则君火相火、正治从治之理,思过半矣”。
清陈士铎在《本草新编》卷四的肉桂篇中言:“此肉桂之功用也,今人亦知用之,然而肉桂之妙,不止如斯。其妙全在引龙雷之火,下安肾脏。……夫肾中之火既旺,而后龙雷之火沸腾,不补水以制火,反补火以助火,无乃不可乎。譬犹春夏之间,地下寒,而龙雷出于天;秋冬之间,地下热,而龙雷藏于地,人身何独不然。下焦热,而上焦自寒;下焦寒,而上焦自热,此必然之理也。我欲使上焦之热,变为清凉,必当使下焦之寒,重为温暖。用肉桂以大热其命门,则肾内之阴寒自散,以火拈火,而龙雷收藏于顷刻,有不知其然而然之神”。
以上诸家皆主张使用桂附等善走不守,温中驱寒,引火归元之药味,同时辅以龟板、牛膝等滋阴潜阳,立法严谨,用意明确,即反热动浮越之表象,以助火收关之力令元阳下伏归位,使阴阳平调,降“龙雷之火”串升欲涅之势。
同时,亦有医者认为不可一味投以温热之品,而应以固脾益气,敛血收藏为要,主要针对的是脾虚发热的 “阴火”证,虽有不同,但理法相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李东垣、陈念祖所论:
金李东垣在《脾胃论》中阐述“阴火升腾”、“气虚发热”的机理,他认为“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是从另一角度论述了脾胃气虚、肾间阴火上乘土位而炽盛的病理变化,脾胃气虚,谷气下流,湿浊流于下焦肝肾,肝肾中之火,为木中之火、水中之火,乃龙雷之火,其性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今龙雷之火为湿所扰,必升腾上乘土位而阴火炽盛。
清陈念祖在《医学从众录》血症篇龙雷之火论中言:“龙雷之火,潜伏阴中,方其未动,不知其为火也,及其一发,暴不可御。以故载血而上溢。盖龙雷之性,必阴云四合,然后遂其蒸腾之势,若天清日朗,则退藏不动矣,故凡凉血清火之药,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于阴火,未有不转助其虐者也。吾为大开其局,则以健脾中之阳气为一义。健脾之阳,一举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如天清日朗,而龙雷伏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而胸中窒塞之阴气,则如太空不留丝翳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而饮食运化精微,复其已竭之血也。况乎地气必先蒸土为湿,然后上升为云。若土燥而不湿,地气于中隔绝矣,天气不常乎。古方治龙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归元之法,然施之于暴血之症,可暂不可常。盖已亏之血,不能制其桿,而未生之血,恐不可滋之扰耳”。
由上可知,无论是阴盛隔阳,虚阳浮越,还是脾气虚衰,血亏生热,都体现了明清之后医家们对于“龙雷之火”病机的一种较为明确的论断和统一的认识。
2.4对比分析,“阴火”论更贴近中医本质
那么,从前后对比来看,丹溪等人所著在疾病病机阐述和治法方药上都没有错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精辟卓著,见解独到,对后世临床施治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其与“阴火”派医家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于“龙雷之火”的解释只停留在了纯粹的字面分析,而忘却了追溯本源,失去了对“龙雷之火”取象类比的理解,而这恰恰是一种中医最传统的认知方式。从丹溪提出“龙雷”二字的过程可知,他的“龙雷”是拼凑而成的, “龙火”在传到丹溪这里时本身已经受到了误解,丹溪再将本来具有单独意义的“雷火”与之和称,形成了 “龙雷之火”,他的“龙雷”二字实属并列称呼,分别代表肾和肝之相火,其实际含义已经和最初的“龙火”有 所偏离,而“阴火”派医家们虽巳惯于使用“龙雷之火” 一词,但实与《素问》之“龙火”同类,只是说法稍改而已,这里的“龙雷”是一个整体的称呼,显然不同于丹溪等,他们更注重“龙雷”作为一种具象化的事物所能 代表的一类与自然之象同气相求的变化过程,将医理还原于原始时期对生活的观察和归纳,这样的方式,显然更符合中医认知疾病的理论
然更符合中医认知疾病的理论系统,也更契合“龙雷之火”病变实质。
所以,丹溪之法虽救人无数,贵为医学真理,但能否冠以“龙雷之火”尚需斟酌,而“阴火”论对于“龙雷之火”阳从阴生,阴不敛阳,虚阳上扰,阴阳错杂之象诠释,更符合“龙雷之火”那种“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的形象,故“龙雷之火”实为“阴火”其义甚明。
3跟从老师诊辨治实例
3.1四肢冰冷
患者,黄某,男,62岁,2009年6月19曰就诊。近3年来下肢冰冷,脸部发热,穿长裤,鞋株包裏严实仍觉下肢发冷,失眠,每年春夏时节尤甚,伴脘腹胀闷,小便清,大便秘结。舌红苔白械右脉弦滑,左脉细弱。
处方:熟附子片15g(先煎),天麻10g,珍珠母30g (先煎),灵磁石45g,川牛膝10g,酸参仁15g,石菖蒲 20g,砂仁10g,龟板5g,炙甘草5g,吴茱萸3g,肉桂1包 (冲服),黄连2g。服用4剂。
按:本例患者病程较长,病机复杂,缠绵不愈,脏腑气血多有亏虚,观其症、脉、舌象可知为阴寒内盛,虚阳上扰,元神不安,拟潜阳丹合天麻钩藤饮加减。潜阳丹出自郑钦安《医理真传》,郑氏认为“砂仁辛温,能宣中 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板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曰潜阳。”方中用阳丹,旨在温肾纳气,引火归
3.2牙龈肿痛
刘某,女,43岁,2009年7月28曰就诊。主诉牙 龈肿痛伴少量出血持续一月有余。之前到他处治疗, 医生多给予凉血止血之方,但肿痛仍不止,就诊时见神 靡体倦,懒于语言,四肢厥冷,舌苔淡白,脉微细。处方:熟地黄12g,当归15g,肉桂3g,熟附子片15g(先 煎),淮牛膝10g,泽泻6g,甘草3g。服用4剂。
按:本例患者曾接受多次治疗,辗转之后仍不见效,可见仅以常规凉血止血之法无法抓住疾病根源,患 者就诊时一派上热下寒,虚实夹杂之象,故试从阴阳升 降平衡入手,拟以阴盛格阳之证,治宜温肾助阳,51火 归元,方用镇阴煎加减。镇阴煎出自张景岳《景岳全书》,张氏认为镇阴煎可“治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则真 阳失守,血随而溢,以致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嚴 冷,危在顷刻。”此时虽无甚危笃,但仍可使用。
3.3总结
老师常与笔者谈论其自我感受:“龙雷之火”犹“亢龙有悔”,龙本于水中潜游,如若水势泛滥,龙无力于波涛汹涌中安身,势必上窜而逃,龙虽绚烂但孤越无依,故可见龙头不昂反坠,恰似“亢龙有悔”,以此类比病人病症,十分形象,临证诊治切记辨清病变实质,引火归元尚需兼顾元阴元阳,不可一意孤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