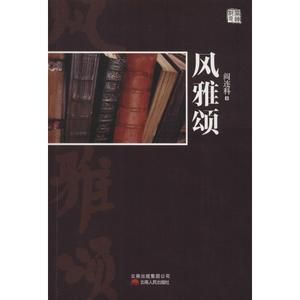“神舟”六号发射之前,本刊对航天英雄杨利伟以及三个梯队的航天员分别进行了独家专访。
采访时间:2005年9月26日晚上8点
采访地点:北京航天城
采访对象:杨利伟
祖国,我为你骄傲
得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要创办《航天员》杂志,航天英雄杨利伟十分高兴,并在百忙中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对他的专访。
《航天员》:“神舟”六号飞行任务一公布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谁会执行“神舟”六号的飞行任务也成了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您在媒体上已经披露,将不执行此次飞行任务,这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杨利伟: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向全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在大家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的,在此我代表航天员大队向关心和热爱祖国航天事业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神舟”六号飞船在技术上比“神舟”五号更加完善,飞行任务也更加深入。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我有过一次太空飞行的经历,所以执行“神舟”六号的任务会更加有经验。其实,这次我没有被安排执行飞行任务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因为工作需要,我目前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有所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在训练方面的投入。另外,国家同期培养的十多位航天员,他们各方面都很优秀,如此巨大的资源不应该浪费,要让他们也能在执行飞行任务的过程中得到锻炼,满足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其实,经过完整的训练,所有的航天员不管在技术上还是能力上,都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我非常高兴我的战友们能够再次为祖国和人民争光,我为他们骄傲。
《航天员》:我们知道,您现在担任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工作非常忙,您还能坚持正常的航天员训练吗?平时的具体工作都包括哪些?以后是否还会执行航天任务?
杨利伟:从进入航天员大队那一天起,训练工作就一直伴随着我。现在,我从一名任务的执行者变成了一名工作管理者,虽然角色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是我仍然和我的战友们一起进行常规训练。我想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参加训练。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和航天员大队的管理。以后,中国的航天事业一定会有更多的突破性进展,作为一名职业航天员,我会根据任务的需要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努力争取再次执行任务。
《航天员》:以您的飞行经验来看,您认为执行这次任务的两名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利伟:我觉得对航天员最大的挑战还是身体的适应问题。虽然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出现不适,但是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在双舱中活动,这在我国航天史上还是头一次。尽管航天员在地面上接受了逼真的模拟训练,但与真正进入太空所要面临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飞船设备、航天员生理和心理都要经受重大的考验。
《航天员》:专家设计了大量的专用设备对航天员进行训练,尽可能地让他们适应太空环境,您刚才说模拟训练与真正进入太空有区别,这些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杨利伟:举个例子来说吧,大家可能都知道,人一进入太空就会处于失重状态。在地面上,长时间的失重环境很难模拟,我们一般用失重飞机对航天员进行失重训练,但由于失重飞机训练的价格昂贵,而且创造出的失重时间很短,所以只能用来进行失重体验。在平时的训练中,航天员一般躺在特制的可以调节倾斜角度的床上,头低脚高,模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血液和体液的头向转移。不过,这种模拟训练也还只是对失重产生的部分效应的模拟,与真正的失重情况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失重的影响,进入太空后,不少航天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运动病,在地面进行失重模拟训练的时候这是很难筛查出来的。
《航天员》:心理承受力是衡量一名航天员的重要标准,您能否谈谈心理因素在执行航天任务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杨利伟: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心理稳定对航天飞行来说十分重要。航天飞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包含很多未知的因素。在太空中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心理承受能力如何很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航天员只有冷静应变、沉着处理,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化险为夷。“神舟”六号飞船上有两名航天员,表面看起来,他们的心理状态会比一个航天员独处时好,但是航天员之间的配合和心理相容性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正是我们航天员训练的“重头戏”。
《航天员》:据说我国将选拔女航天员,请问现在有没有选出来?她们什么时候能执行航天飞行任务?
杨利伟:女航天员的选拔在美国、俄罗斯已有先例,这既是对女性的尊重,也是对她们能力的肯定。这方面的选拔工作,我国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选拔的标准也在制定过程中。根据我国的航天计划,在“神舟”六号任务成功之后,我们将会陆续培养女航天员。她们在进入太空之前,至少需要2~4年的学习和训练。
《航天员》:选拔女航天员有些什么样的标准?
杨利伟: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不管男航天员还是女航天员,大家面临的环境和考验都是一样的,因此选拔的要求也大同小异,但我们会专门针对女性的特点来制定一些特殊的标准。
《航天员》:男航天员和女航天员执行太空任务的能力方面有什么差别吗?
杨利伟:执行太空任务对男、女航天员的能力要求没有太大的差异,任务性质也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如果需要出舱执行任务的话,这就对女航天员的身体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出舱执行任务时,航天员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让男航天员协助进行。
《航天员》:作为《航天员》杂志的名誉主编,您想对我们读者说些什么吗?
杨利伟:首先祝贺我们《航天员》杂志的成功发行,同时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该杂志的名誉主编。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读者奉献一本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丰富多彩的刊物,同时,作为一本科普刊物,我希望《航天员》能起到科学普及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航天员和航天事业,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进而热爱航天事业并参与进来,为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国家和民族的腾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采访时间:2005年9月26日下午
采访地点: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模拟器大楼
采访对象:费俊龙、聂海胜
与神六航天员面对面
《航天员》:你们以前都是空军飞行员,后来是怎样加入航天员队伍的?
费俊龙:所有航天员的选拔经历都差不多。先是档案筛选,身高、体重、飞行时间等基本条件符合要求的人员被挑选出来,然后由他们自主报名参选。之后还要经过层层选拔,包括临床选拔和特因耐力选拔等。我是1996年知道选拔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哈密,训练处长给我打电话,说选拔预备航天员,问是否报名。我条件符合,立刻就报了名,后来很顺利地通过了各种测试,成为了一名航天员。
聂海胜:我的选拔经历和费俊龙基本一样。不过我是到疗养院体检时才知道这是在选拔航天员,直接就参加了选拔。
《航天员》: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乘组是如何选拔出来的?
费俊龙:神六乘组的选拔标准是公正、客观、公平、透明。针对“神舟”六号的飞行任务,专家制定了科学、严格的选拔标准,不同的考试科目有不同的权重。整个选拔过程大体经过了初选、复选和定选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非常详细的实施方案。初选时,所有人的分数都全部清零、“重新洗牌”,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这对所有的人都很公平,而且大家在选拔中做到了竞而不争。
聂海胜:由于大家训练得都非常好,找个小毛病都很困难。这样,在考核过程中,只能通过小的地方来区分大家,在外人看来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大概是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选出了三个飞行乘组。
《航天员》:乘组的人员搭配都考虑了哪些因素?
费俊龙:分组时考虑的综合因素非常多,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自身角度来讲,喜欢和谁一组,首选人选是谁;二是专家和教员进行综合考虑,确定乘组人员的搭配。选拔出来的梯队基本都是外向活泼型与内向沉稳型结合,心理相容性非常好。
《航天员》:“神舟”六号任务的飞行训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费俊龙:其实,“神舟”六号飞行计划一出台,我们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训练了。不过,有针对性的训练是从2005年春节前开始的。
《航天员》:可以看出你们两位配合非常默契,是怎么练出来的?
聂海胜:毕竟大家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有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磨合训练,相容性非常好。为了配合好,不光是训练时两人一起交流,训练前要协同准备,特别是对看法的交流很重要,白天没时间进行我们就晚上来。针对故障情况下的分工,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怎么衔接,两个人要多次演练。
《航天员》:能不能介绍一下“神舟”六号的心理训练情况?
费俊龙:心理训练主要有:表象训练、相容性训练和放松训练。根据任务的需要,过过电影,回忆一遍,加深记忆,效果很好,因为不能总在模拟器训练,这种训练就是表象训练。通过放松训练,可以训练你在大的环境下,在紧张的情况下,能很快地放松下来。比如,闭一口气,坚持5秒钟左右,很快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一些小技巧。
《航天员》:您认为进入太空后最大挑战是什么?
费俊龙:最大的挑战是尽快适应太空生活。由于失重引起的身体上的改变和不适应,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航天员》:空间运动病就是进入太空后的一种不适应症,平时进行了哪些针对性训练?有什么预防措施?
聂海胜:主要有前庭功能训练(转椅),每周都要进行多次,还有体育锻炼,比如秋千什么的,体训馆后面有许多设备。每个人发生运动病的概率不一样,有没有运动病,只有上天才知道。到太空中要以预防为主,可以预服抗运动病的药物,我们在地面都服用过,主要是耐药性试验,看有无不良反应。此外,在太空要减少头部运动,因为头越动,运动病的症状越强。如果实在难受的话,可以打针。我们的太空药箱里专门准备了针剂,症状特别严重时,就可以注射。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专门训练,练习进行相互注射。
《航天员》:这次飞行都准备了哪些航天食品?在太空吃饭需要进行训练吗?
费俊龙:通过计算能量热量,给航天员配备了丰富的航天食品,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食品,如中国的月饼,小块的,不产生残渣。饮水袋是单向阀门的,防止水外泄。食品有复水菜、八宝饭、调味品、巧克力、风冻果干以及硬、软罐头等,还专门配备了加热设备。一般来讲,上天后人的口味会发生变化,地面上再好吃,到天上都不好说了。一般航天员在天上会比较喜欢辛辣的味道,因此特别准备了辣酱等调味品。
聂海胜:地面吃饭很容易,10分钟搞定。天上由于环境不同,所有的东西都在飞,吃饭就不容易了。首先吃饭不能掉渣,要控制自己的身体行为和使用的工具。饮水也是一样,太空中液体的东西,一旦散出去就不容易收回了,特别是如果水飞到电路上,引起短路,会直接威胁飞行安全。因此在地面上必须要进行专门训练。
《航天员》:假如你们在太空中生病了怎么办?
费俊龙:飞船上有药箱,轨道舱里有大药箱,返回舱里有小药箱,它们都装着各种各样的药品。普通的感冒、肠胃不适、发热等,药箱里都有相应的治疗药物,但使用时要听地面医生的,用药必须经地面医生批准。
《航天员》:航天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你们是怎样看待这个职业所面临的风险?
费俊龙:这项事业肯定有一定风险,但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停止,包括国外探索宇宙,“发现”号也一样。“发现”号重返太空显示人类探索太空没有因为风险而中止。从加入航天员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向国旗、向祖国和人民宣誓,为祖国载人航天事业奉献一切。
聂海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胆子比较大,把那些东西看得比较淡。
《航天员》:《航天员》杂志是一个刚刚创刊的科普期刊,你们能对我们的广大读者说些什么吗?
费俊龙:感谢你们创办了这个刊物,从一个角度把航天员和为航天事业的辛勤工作的人报道出来,让祖国和人民了解他们,感谢你们。
我们航天员乘组感谢中国载人航天的千军万马、后方各行各业的人,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
感谢时代,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乘祖国的神六,或今后更多的飞船去遨游太空、探索太空。这也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它必将凝聚全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
记者手记
结束对三个航天员梯队的采访,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信念,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2005年10月17日早上4时33分,当头顶的那抹亮光长长地划过天际时,群山高歌,大地欢腾。潮涌而来的鲜花和掌声,宣告着费俊龙、聂海胜此次太空征程的完美结束。在中国人探索未知世界的路途上,他们迈出的步伐令世人瞩目!感谢英雄,感谢时代。
面对记者的提问,每一名航天员都显得那么从容、洒脱。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将航天员所有的精彩对白一一展现出来,只摘录其中一些精彩片段,与大家一同分享。
刘伯明:自从加加林首次进入宇宙空间,人类便增添了一种勇敢的职业-航天员。作为一名航天员,不但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超强的生理、心理素质,过硬的综合素质,而且要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险、勇于献身。载人航天事业如今已走向成熟,但任何先进的装备都无法将风险系数降到零,我们航天员要有同异常情况顽强拼搏的精神,有战胜困难的信心,有完成任务的决心,真正做到勇者无惧。
景海鹏:我加入三个梯队的其中之一,最大的感受是永不放弃。“神舟”五号选拔的时候我没有入选,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永不放弃,总有一天我有机会执行航天任务。此外,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非常关键,考试和大型训练前,耳边常常会响起同事朴素的话语:“好好整、好好考。”那时心理感觉非常好。
翟志刚:哪个训练都不好过。难度最大、最考验人的意志、最能消耗人的储备能量的就是离心机、低压缺氧、下体负压、模拟器等训练。离心机训练要求人体肌肉的对抗性、紧张度好,体质好,这个训练就好弄。进行模拟器训练,人不光要捂着航天服操作模拟器,还要思考问题,做出正确判断。模拟器训练耗精力,也耗体力,3个小时肯定出不来。心血管调节功能不强的,低压缺氧训练肯定做不下来。
吴 杰:作为航天员,我对咱们的飞船、火箭和设备是绝对相信的。科技人员对质量抓得相当严格,而且要进行质量认证,加上有“神舟”五号等飞船的基础,我们感觉非常放心。进入飞船后,我不会考虑安全性和可靠性到底有多少,只会想怎样按照训练的要求去做、能不能把平时训练的最好水平拿出来。即使出现异常情况,我们也能灵活应对,所以我们信心很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