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是诗歌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它的传统源远流长,它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把所要叙写之事物借来比方另一事物的表达方式。它们之间是明确的借代,是一比一的关系,如余薇野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它只有一句
不是虹,走人脸!
它精采极了,诗人将生活中那些善于伪装,不时变换脸谱的伪君子比作天上的虹是太新颖了,它的深刻性也由此而生。叶嘉莹认为比喻是“由心及物”它是作者先有内心感受,然后再用一个外物的形象来表现。兴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比,它是“由物及心”。叶嘉莹举例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是因为我们听到了关关的雎鸠鸟的叫声,想到那河边的沙洲上一对鸟这么快乐、美好的生活,我们人类岂不应该也有这样快乐、美好的生活吗?所以‘窃宛淑女’就‘君子好逑’了。这是很自然的由外物引起的联想。这个我们叫做‘兴’。西方现象学所注意的,也就是你的意念跟外在的现象的外物之间交接的关系。我们讲的兴,也就是一种交接的关系,是由外在的外物引起我们内心的感动.是由于先看到物象而引起我们内心的感动,是由物及心的感动。①比和兴虽有先后之分,但都是打比方。在新诗中用“兴”也是很普遍的,如雪迪《我的家》表现的是一个美满家庭中的和谐夫妻生活,开头一句“我的家在午后一个温暖的日子结满葡萄。”就是一种“兴”的方式,诗人第二节说“窗子的玻璃上趴满蜜蜂,花朵在一个个开放”也同样是一种由物及心。姜强国的《大马群》看上去似赋:
黄昏的风,轻揉着马头琴的皮弦/奏出了牧归曲的前奏/大马群,铺天盖地的大马群/在涌动,在长嘶,在奔腾……/骤雨般急促的节奏/在牧人的心房里强烈地共鸣着/草原又一次发出粗犷的回声
它实际上是由物及心的“兴”,先有嘶鸣着、奔腾着的大马群铺天盖地而来,然后才有牧人心房的急促的跳动。
比喻的目的既是为了传达作者真切的感受,又是为了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出于此目的,诗人不甘心用一个比喻,而连用几个喻体来比喻一个本体,这就是博喻。
艾青的《给乌兰诺娃》用了六个比喻,何其芳的《欢乐》却用了十三个比喻:
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象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象一声芦笛?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或者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欢乐是怎样来的?是什么地方?萤火一样散自蔷薇的花瓣上?它来时脚下响不响着铃声?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我的忧郁? 周振甫认为这种博喻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大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②不管是比喻,还是博喻必须在新、奇、特上下功夫,要完全避免重复、因袭的老调重说。在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礁记》中有这样一个博喻典型例句:
投到你做官,直等到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眨眼,北斗打呵欠。直等到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刺靴,蚁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买饼料。
投到你做官,直等得炕点头,人摆尾,老鼠跌脚笑,骆驼架儿上,麻雀抱鹅蛋,木伴哥生娃娃,那其间你还不得做官哩。
连用了十五个比喻既奇特又新颖,这不能不说它是剧作家的匠心创造。瑞恰兹在《想象》一文中就认为比喻中那些常见的说明性或图解性应该尽量避免,他最欣赏的是诗歌中“把不相干的、彼此本来不联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排比与组合,“这些东西在读者头脑内就建立起关系,因而形响他的态度和走向。”虽然它表现为反常的、不合逻辑的,但“通过这种方法,更多的不同因素可以组织到经验的结构中去。”新、奇、特也由此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本体意义上认识比喻的新、奇、特,它只能是正确的废话,这在爱情诗中特别明显。在表现爱情时,仅为形同的比喻极易落入肤浅的窠臼,而新、奇、特的比喻因具有本体意义,它被大大地升华了,罗兰·巳尔特说:
他恋爱了:他到处凭空创造意义,使他震颤的也是意义;他落入了意义的熔炉了。对恋人来说,每一次碰撞都提出了回应的问题:皮肤被要求给予回答。(手的紧握--大量的信息资料--手心的轻微弹动,一动不动的膝盖,双臂似乎自然而然地伸向椅背,伴侣的头渐渐靠在上面,这是微妙隐藏的极乐世界:一场欢乐,不是感官的,而走意义的。)
——转引自卡勒尔著《罗兰·巴尔特》
巴尔特的分析确是精采绝伦的,从热恋情境中的恋人们的特殊表现中,我们当悟出优秀爱信诗中必有的品位。试看早期现代派诗人罗莫辰的《短章为s作》:
我无声无息地呼喊你/在我手掌上/泅泳着你的目光/你的名字/微微转动在我沉默的呼唤中/正如蜜蜂在它的房中/如你的手臂/以前本我手臂中转动。
热恋者的两情脉脉全通过比喻给出色表现出来。有创造性的诗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比喻的方式提高它的品位。且看余光中的《双人床》:
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流弹/象一把呼啸的萤火/在你的,我的头顶窜过/窜过我的胡须和你的头发/让政变和革命在四周呐喊/至少爱情在我们的一边/至少破晓前我们很安全/当一切都不再可靠/靠在你弹性的斜坡上/今夜会山崩或地震/最多跌进你低低的盆地/让旗和铜号在高原上举起/至少有六尺的韵律是我们/至少日出前你完全走我的/仍滑腻,仍柔软,仍可以烫热/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让夜和死亡在黑的边境/发动第一千次围城/惟我们循螺纹急降/天国之下/卷入你四肢美丽的旋涡
全诗虽写了做爱,但并不是诲淫,而是从一个侧面强调了爱的完整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主张在爱情描写中,应该有必要的和健康自然的性生理、性心理描写,否则就不可能真实动人。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说:真正的爱情是“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作为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是“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待征。”③余光中的《双人床》写的就是心灵的契合和精神因素的提纯,因而它“始终是两位一体--在同一份爱中既有甜美的心神交融,又有激烈、自豪的肉体满足。这样我们就升华为一朵玫瑰。我们甚至超过了爱,爱被拥有了,又被超越了。我们是两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我们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宝石般的独特存在。”(劳伦斯:《爱》)它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英国小说家毛姆在长篇小说《刀锋》中的一段精采议论:“如果爱情不是激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激情不是由于得到满足而增长,而是愈不顺利愈强烈。”“激情是能毁人的,激情如果不再有毁灭人的能力,它也就灭亡了。”
离开了诗中的新、奇、特的比喻,这首诗中的意蕴也就不复存在了。需要指出的,片面地追求新奇特的比喻,只能造成谬喻(Catachresis)的滥用。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比喻实质上也是一种经验的表达。但如果他的经验纯属于个人,不包括任何人的一种经验在内,只是一种零度语言的表达,那这种比时只能是一种情感的黑洞。
从更广义上说,拟情化也是一种比喻,它指的是将自己最心爱的人和事物比作情人的一种特殊的比方,也正因此,它很容易被淹没在广大的比喻的海洋里面而被忽视,所以有特别拈出来的必要。“五四”时期的郭沫若的《炉中媒》就将当时的中国比作自己的情人: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我的思量。/我为我的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要知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更有甚者,是闻一多的《也许(葬歌)》: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当人们读这样的诗时,无不被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缠绵悱恻的感情所感动,这不是一首典型的悼亡诗吗,是悼念死去的妻子,还是有过海盟山盟的情人呢?其实这是诗人悼念夭折的爱女的葬歌,这首诗的姊妹篇还有《忘掉她》。就有人把它作为情诗理解:“这首诗像纤美的按摩女的手指。如果一个人死了心爱的人,在他(她)的坟前,把这首诗斟字酌句的念两遍,你会静静地流泪,而不会嚎啕。这首诗可谱上曲,做为通用的葬歌。”对处于传统思维定势的读者可能对闻一多这首诗或《忘掉她》大惑不解,怎么能以对待情人的感情表现对爱女的怀念呢?然而这并不是闻一多的首创,卢梭在《忏悔录》中述及他对养母华伦夫人的感激之情时就说:“她对我来说,胜似姐姐,胜似母亲,胜似朋友,甚至胜似情人。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是我的一个情人。总之,我太爱她了,不能别有所图,这在我思想里是最清楚的。”《也许》中的“反常”表现是“合道”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足以表达出他对失去爱女的拳拳之心,它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叶嘉莹在谈到中国古代诗歌中为什么喜爱用男女之间的爱情表达美好感情时说:“这也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西方也是如此的。《圣经》上象《雅歌》的诗篇,完全写的是美女和爱情,而他所说的是什么?是一种宗教上的信仰。象西方的英国的诗人John Donne所写的很多非常热烈的爱情的诗歌,都是宗教的信仰的诗歌。正因为爱情是人类最本能的最真挚的一份感情,所以才富有广义的象征的意味。”④闻一多的《也许》、《忘掉她》在发表的当时不啻是一阵春风,也可谓惊世骇俗,但有趣的是,在今天己经为年轻的诗人接受了。如一九九○年一月号《东京文学》上的一首表现春种秋收的诗中说:
季节在秋天/出嫁/季节蒙红头巾/季节骑小灰驴/在山道上得儿得儿跑/野菊为季节喧响金黄的铙钹/喇叭为季节吹嘹亮的铜号
在诗人看,季节就是他心爱的新嫁娘,他钟爱的小媳妇。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自画像》中,为表达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就说:
我不老的母爱/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条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他呷玛阿妞
诗人将对母亲的爱比作“永恒的情人”,也是一种拟情化。在当代诗人中,它几乎无所不能。如奚邦科的《插秧》也是这一手法的变奏:
在我江南春之水绢上/生花的妙笔是闪光的手指/秧苗单恋的现象/春之气息深入/秧之气息浅出/灵秀的季节最繁盛的欲望/在指间得到最时宜的开放/季候之外个总有一些什么/被手指干净地表演/正如这些老资格的/棵行之间的距离/正如这一方老式的水土/在各人自插门前秧的时代/依然于我迷茫的眼中/缠绕的手指一一生花
在诗人看来,插秧者对秧苗是情有独钟:“一一生花”的“缠绕的手指”完全是沉入 爱河中的青年男女缠绵悱恻的写照。将这种拟情化推到极致的,是有些诗人将丈夫和妻子视为永恒的情人,是以看待情人的心态观照他们。前者如林子的长篇组诗《给他》,后者如黄永玉的《献给妻子们》。诗人说:
不是好女儿,/哪来的好情人?不是好情人,哪来的好妻子?/不是好妻子,哪来的好母亲?
情人与妻子是有区别的,但两者如能做到水乳交融,成为一体,那无疑是情爱的最高表现。
①④《唐宋词十七讲》第437页,38页,岳麓出版社1989年版。
②周振甫:《诗词例话》第23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③转引自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情描写的一些论述》,《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后记:“时尚胡闹” 与诗意的丧失
——第三代诗潮的得与失回顾
“第三代”诗是“朦胧”诗后的一批青年诗人实验性诗潮的泛指,它已定格成为历史了;然而在它的鼎盛时期的1986—1988却是风靡全国的“时尚”。
“时尚”日益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从70年来的跑图书馆,交谊舞,喇叭裤,80年代的校园歌曲,迪斯科,托福,下海,摇滚,到90年代的炒股,刷卡,时装表演,上网,它几乎成了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青年人,“时尚”成了引导他们不断向前的滚滚潮流,可见“时尚”是一个好东西。
“时尚”最能反映在时装的日新月异的嬗变中,它总是以新、奇、异、怪的面目呈现在女模特的时装表演中,但在我们看,不管它如何变化,服装的最基本功能:一是实用,二是美化,它的以人为本功能是不可变的,即使有着爆炸效应的三点式比基尼泳装也是如此。然而在这股潮流中总有一些趋时者不遗余力地大搞“稀奇竞赛”(Rarity game),如将古典建筑叠加在服装上的木乃伊化,各种玩具型的卡通化,造型狰狞怪诞的魔鬼化,似乎愈奇愈好。它已远离了服装应以人为本的法则。可见“时尚”也不一定是好东西。英文fashion可译为时尚,主要指的就是服装试样变化的潮流。
服装变化上的时尚与诗歌上的时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观赏对象和艺术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活动的体现出来的“力的式样”在性质上趋于对应时,也就有了共鸣,他们称之为“异质同构”。作为一个大背景,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实为一种潮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重新审视它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要肯定的,第三代诗潮的涌现并非偶然,它是继朦胧诗后的又一次精神的解放。如果说朦胧诗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诗的审美性质,显示了肯定自我的价值观。诗人将是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我引入诗中”⑴,那么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向纵深,他们继续轰击原有新诗的形成的意识形态硬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与之相适应是追求灌注生命意识的语感、语调、语势,由诗的语言“陌生化”而转向日常化的原生态。它的独特贡献就是对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形成假崇高、假神圣、假喜悦、假悲哀的消解。在人类生活中,崇高、神圣、喜悦、悲哀都是必不可少的伦理感情,可是一旦掺了假就如同变味变质食品。更为可怕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常在打着崇高而神圣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强迫大多数人作出喜悦和悲哀的虚假表演,它鲜明地反映在为实践检验是错了的各项政治活动中的人们表现,大到如“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摇旗呐喊;小到像除四害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一旦被钦定,均在神圣和崇高的旗号不是被唾骂被打击,就是陷入灭顶之灾。诸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胡风、巴金、老舍、艾青、丁玲等,以及被科学家判为益鸟的麻雀在短短的8个月中竞被消灭了19.6亿只!那些看来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人面对被批判者有几份真实的感情可言,明言人一看便知,因为被迫才不得不如此表演。对此,第三代诗人深恶痛绝,尤其对那些制造的虚假表演的“导演式的人物”,他们常常被罩上神圣的光辉。诗人雨田说:“看见了吗?他不分春夏秋冬/以他存在的方式挥起手臂/过去的岁月/象一个真实的春天/针芒的斗争无比/有嘴的人不能说真话/有嘴的人/说出鬼话/真理被谎言刺伤后/此时你是否仍在转眼不改脸色/注视着南来北往的汽车和行人”。(《另一座城市的塑像》)伟人毕竟有伟人的“质”,但用造神运动方式的创造出来的崇拜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它源于一种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中,首先是默祷,在默祷中,你把这个人的神圣想象得无限崇高,把自己看得无限渺小。以净化灵魂的方式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块一无所有的“空地”,由造出来的神占领取代,由此,第三代诗人就; 热衷于在他们诗中以非崇高、非神圣的方式、将伟人平民化,还原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如于坚的《贝多芬纪年》《罗家生》,柯平的《陈子昂登上幽州台》、《车至剡溪下游突然想起李白》。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宙斯,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和普通人一样,照样“失恋”,“感冒”,有着他们同样的苦恼,生活平平常常。如诗人说:“十八世纪某月某日某地一职员病休在家/某地以剧院客满/贝多芬双耳全聋/十八世纪某月某日/好天气/供应烤面包/一个男子和老婆上床睡觉/路德维奇·凡·贝多芬逝世”。伟人之所以愈来愈不真实,是人们给他附加的意义太多了。由此第三代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关注他们由于所处生存状态的喜怒哀乐。代表诗作如于坚的《罗家生》。诗人笔下的罗家生实在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位工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但因为太平凡了,谁也不注意他,可是当他出现在诗人笔下,诗人以不动声色再现他的不幸时,人们才感到震惊。多少年来,我们的诗坛是否太多地关注伟人而对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视而不见。诗人的这种“近距离”表现方式拉近了艺术与观念,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它无疑是新诗的一大进步,然而过犹不及。在消解了传统价值与精英的同时,也为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委琐者、骗子、痞子张目,价值的虚无必然使伟人、常人处于同一个平面,由于是削平深度,便形成了文学平面。正如一位诗评家的指出的上述主张“曾鼓动和引导了许多涉世未深的诗歌初习者对‘朦胧’诗所拥有的现实批判精神的轻率遗弃。大胆引进关于个人的题材,袒露自己的压抑、不幸、欲望和野心。历史现实中的行为和事件,伦理的诫条和神秘宏大的情景不是纷纷退隐,就是一无例外地受到嘲弄、短暂、琐屑、卑微的行为和场景,乃至粗俗的嘴脸和不雅的谈吐,纷纷出演主角。”⑵
第三代诗人同样重视诗歌语言,他们的名言便是“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虽然认为诗是一种语言游戏,但却不是一种为玩而玩的游戏,而是诗人介入社会的一种特殊游戏方式,它应是严肃的、认真的,它常伴随着苦难。他在《棕皮日记.1966》一文中就说:“如果游戏在汉语中往往被理解为不负责任、戏弄等等,那么我可以为‘游戏'加上一些限制词。严肃的、伤筋费神的创造性的等等……西绪福斯的劳动可以看成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不是命中注定的,谁愿意去玩啊!”然而,由于长期来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阐释权,诗人是无法进行如于坚所认为的那样语言游戏,语言成了凝固的板块。对此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文革中广为传播的流行语“一句顶万句,句句是真理”。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取得了上述话语垄断权后,他的话语就必是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它可以指鹿为马。语言本身是思想交流、生活的工具,可此时语言却成了少数人愚弄大多数的魔方与陷阱,对此,非非主义诗人何小竹深有感触。他写出了历来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不少人为突然飞来的横祸击倒的场景: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人就会记得/一个动词会叫人死/他们隔山打石,痛击你的/脑袋和灵魂。/你翻开语录,寻找武器/你可以在白天抵挡,却不敢保证/在梦中不会走漏风声/动词们成纵队排列。不是请客吃饭/那样温文尔雅。/有人谴词造句/有人突然在名词中消失/“唉”的一声,想为虚词……
文革中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赫鲁晓夫”系指内定了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打倒他,全国8亿人民被裹进了一场空前的风暴,其结果是刘少奇死了,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10年之后却证明了这关键词是不存在“伪问题”。何小竹所说的“一个动词叫人死”不是千真万确的吗!
大学问家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何小竹与季羡林感受是同样的。
语言学家徐友渔更是从理论高度指出:“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当今世界上许多武装冲突,分离运动,都有语言方面的根源。这似印证了《圣经·旧约》第八章中的一则寓言。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头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要看世人所建成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
这则寓言深刻地告诉了人们,如今世界上还存在隔绝,如同聋子对话,语言隔绝之所以能形成,就是耶和华这样的人垄断了语言的阐释权。“人类的得救,一是包括拆语言的墙,填平语言的鸿沟。”⑶非非主义理论家们有感于此,他们在《非非主义宣言》中明确宣告:“我们要摒弃感觉活动中的语义障碍。因为它使诗人与世界按语义方式隔绝。”并指出“要捣毁语言的板结性,在非运算地使用语言时,最大限度地解放语言。”⑷然而他们的创作与主张却是一个悖论,那就是要反对现存的语言规范就不得不打破它另造新的语言,然而诗人与读者在解读时还不得不依靠原有的语义加以阐释,否则就给人感到不知所云,前卫画家徐冰的《析世鉴》,乍看画面是一个个整齐的方块汉字,但却是从任何汉字字典找不到的汉字,只是一连串没有所指的能指,一种纯粹的符号。如果仍在绘画中,因诉诸视觉,《析世鉴》上的“伪汉字”还可起到装饰作用,那么非非主义诗人们的一些诗作就不堪率读了。诗并不是纯语言,在它后面必须体现我们现实中的问题。“艺术一出现‘纯’就意味着问题的消失,而艺术没有问题,也就失去了永恒的活力”⑸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枚举,仅从以上例征,就不难看出新生代诗人们的主张和实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如此,但因是看到传统诗歌中的“问题”而发,在大多数诗人和读者还处于浑然不觉状态时,这些诗人们的超前意识却表现出他们的先锋精神。“先锋之为先锋就因为它超前,与众不同,有点奇形怪状之意——如果先锋一上来就被公众认同,如果先锋一上来就与大众阅读拉平,如果先锋一上来就与传统接轨,只有连续,没有断裂,那还谈上什么先锋呢?”。⑹而“时尚”之所以称之为“时尚”,同样是因为具有先锋特征。英语trends也可译为“时尚”,但它与另一可译为时尚的英语fashion有着质的不同。前者体现为一种自觉了的大众走向,一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追求的潮流。著名的文学史家林庚教授就认为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应强调精神文明。“精神方面的影响主要靠艺术的熏染”,“都说中国是儒家的学说占主要地位,这也没有错,但对于人的精神影响,主要的还是诗教”。⑺诗教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应是回答什么是诗,诗人何为?
什么是诗?它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但又有别于散文语言。由于诗歌是从音乐中分化出来,这就决定了诗歌语言必须依靠音调、音韵和节奏等音乐方面的因素产生效果;作为艺术的一种,它又应有着社会交往功能。如美国文艺理论家埃德曼所言:“更确切地说,诗歌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在诗歌艺术中语文这种媒介处于最引人注意的前哨位置,无论是诗人或是听众,读者都不会忘记诗歌运用的语言。正如桑塔亚纳所说,诗人是锻造文字的金匠,当诗人被文字的声音对于感官的效果说感染时,他的读者也会受到感染。”⑻
明确了什么是诗,再看诗人何为?我们不妨看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皮萨列夫说:“诗人——如果不是伟大的思想斗士,大胆无畏,无可指的‘精神斗士’,像亨利希·海涅所说的那样,便是渺小的寄生虫。”
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己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的喉舌。”
高尔基说:“不要把诗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从以上论述看,他们一致地认为诗人应为社会、人生而创作,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感知他们生存状态中的喜怒哀乐,为促进人类社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即是超越了对物质追求的终极关怀,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一个有着健全人格的人,必须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20世纪已过去了,人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惊叹不已,但人类几千年来的彼此争斗都留下的教训也触目惊心。据历史学家粗略估计,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995年世界上就发生过4500次战争,死亡人数70亿,为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不惜发展残杀技能:刑具、武器、谋略;可见人类的敌人为人类自身。当代最著名的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惨淡阴暗的未来图景。这似乎过于悲观了,但理论的悲观比盲目的狂热好得多。而不是给人们分发进入虚幻天国的入场券。德国哲学家蒂利希就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存在的烦恼。一个尽管竭力想逃避烦恼,但除非他有勇气把烦恼当作人生于世不可避免的处境的一部分接受下来,他就免不了受它袭扰。只有接受烦恼,他才会有生存的勇气。”⑼
当我们以什么是诗、诗人何为的价值判断对照第三代诗潮,就可以看出某些诗人创作追求的实为后一种“时尚”(fashion),也就是在服装变化中因追求猎奇而形成的时兴、风尚、风气导致“胡闹”,它的泡沫状态最终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冈布里奇正是从这个角度谈起文艺发展中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当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因循守旧与墨守陈规受到冲击是必然的,然而却有些“别具用心”的人为了引人注目而玩弄一种“时尚胡闹(follies of fashion)”,他就是以服装变化中的猎奇为例加以说明的:“在一个时期,又可能是胸肩的大胆袒露、发型的高度和裙衬的宽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竞争已把时尚变成了一种声名狼藉、愚昧玩劣的‘过分行为’。”“但是偶尔这种竞赛会变得流行起来,并且达到全体参与的临界规模。不管我们是剃发,还是系领带;是喝茶,还是滑雪,我们都加入了‘跟着头领跑’的竞赛”。⑽在中国,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某些“新潮艺术家”的所谓“创新”和“反传统”,实为一场“时尚胡闹”。无独有偶,这种“时尚胡闹”在第三代诗潮诗人中也有充分表演,这里仅举数例:
先说杨炼,他的早期朦胧诗为人称道,然而他的后期的诗作却为年轻的第三代诗潮诗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是他的文化寻根诗,如《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诗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作者说:“《自在者说》十六首,为以《易经》为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一部,《与死亡对称》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二部分。”诗人以诗的形式阐释古老的《易经》文化底蕴,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读者面对的却是这样的诗句:
传播鼠疫的手,猝然掰碎身体里的一座汞矿
第一天的红色在舌头上蜕为蝗虫
——《自在者说·天·》
影子佝偻的太阴历已绕过毒箭
溜过来 读 病与年轮
——《与死亡对称·地·第一》
读后的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读者之所以有如此感受,并不是因为诗中有太多的西方意象和典故,而是通篇都是割裂的词,而词却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人们都知道,寻找意义永远是阅读的目的,即使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它也是在意义的引导下进入角色。这样的文化寻根诗多少像时装中那种将古代建筑、如紫禁城加在服饰上的木乃伊化的表演。
比之杨炼,在语言试验上走得更远的是钟鸣的诗作。他的诗意象奇特而流畅如大珠小珠,但同样不为读者接受,这是为什么?如《裸国》十六节中的片断:
“风吹过草原,我的两眼茫茫。血,在碑额上停止无用的奔流。羊群在最后一线烛光中遭到女巫灼烈的语言放逐。光明无畏黑暗者最初的光明,树巅上神秘的叶子在头顶消失,牙在阴影里恢复,石麒麟和玉蟾蜍。优美的乱伦,人类的俗气,得到完美的恢复,而灵魂,荡秋千的影戏,moving picture,则变成傀儡。”
当读者面对上述诗句时,同样会一片茫然。
其情形,如同当年朱自清在评论李金发诗所说的那样,他的诗单个儿的词语都可以懂,然而全在一起却不知所云。如同一粒粒珍珠,必须有一串儿安然无恙地将它串起才成为项链,李金发的诗缺少的却是这串儿。如从语言学角度看,它只是没有所指的一连串的能指滑动。是巴尔特所认为“能指完全独立于所指,而无拘无束地和文本打交道,追求反应的一贯性和有效性而不是客观性和真理性。”⑾由于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就导致语言意义的丧失。“在这时里,语词的双重功能被剥离去了一重,它的所指符层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词语的能指符层面。文本变得至高无上,而作为支撑文本的人类现实生存经验反而变得空渺和无迹可循。词,仅仅是词,它不再指代什么”。⑿阅读本应是得鱼忘签,但结果却是得签而忘鱼。这种语言游戏方式显然是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种卡通式的时装表演,只能在舞台上“胡闹”,他与于坚所说的“语言游戏”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些诗人都以先锋自居,并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它的至命处恰是因为没有思想内涵,而逃避社会责任失去了感觉,成了没心没肺的舞台上骚首弄姿的时装模特。至于主观意象派诗作实在是等而下之。吴非的
修着/在/久以/的/个是故事的/这你发生//替时/肤色/在村//被你走中/过你/留/下着的/一层/树
读者不禁要问,这也是诗吗?诗人孟浪说:“坦率地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不喜欢这类制作。但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它有助于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也就是说,从什么是诗的反面看出它不是诗。”⒀作者也说:“它是我边缘意识的错乱反映”。⒁其实这样的语句连精神病人的错乱呓语也说不上。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话并不是没有规则可循,他们遵循的是“旧逻辑”。即“相似即同一”的规则。正常的逻辑“A像B,却不是B”,而前逻辑则是“A像B,A就是B”将两者完全等同是荒唐的,但仍是有迹可循。保罗·克劳瑟在批叛某些先锋派艺术所谓独创性时说:“的确,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却创造出一种独创性和胡闹(original nonsense)。”⒂早在近千年前金代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批评了这种哗众取宠的现象:“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诗歌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存在。英国诗人邓恩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在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们受到损失,因此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必须为有意义而活着,何况肩负着诗教的诗人。以“人在生活中游戏,诗人在文字中游戏”的态度进行写作,并将它视为“排泄”,⒃这正是杜伏海纳所告诫的:
作品自身的语言不要象手淫那样从身上获得满足,作品多少参照世界,即使为了否定世界或者把世界作为想象的一个背景。⒄
在时装表演中,为取得一时哄效应的时尚可以朝秦墓楚,但作为社会中一员的诗人对意义的追求却是永恒的,而不应是以“胡闹”打发日子的“空心人”,如汤因比所说的“内心无产者”。
新诗技巧二十讲(后记)
后记:“时尚胡闹” 与诗意的丧失
——第三代诗潮的得与失回顾
“第三代”诗是“朦胧”诗后的一批青年诗人实验性诗潮的泛指,它已定格成为历史了;然而在它的鼎盛时期的1986—1988却是风靡全国的“时尚”。
“时尚”日益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从70年来的跑图书馆,交谊舞,喇叭裤,80年代的校园歌曲,迪斯科,托福,下海,摇滚,到90年代的炒股,刷卡,时装表演,上网,它几乎成了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青年人,“时尚”成了引导他们不断向前的滚滚潮流,可见“时尚”是一个好东西。
“时尚”最能反映在时装的日新月异的嬗变中,它总是以新、奇、异、怪的面目呈现在女模特的时装表演中,但在我们看,不管它如何变化,服装的最基本功能:一是实用,二是美化,它的以人为本功能是不可变的,即使有着爆炸效应的三点式比基尼泳装也是如此。然而在这股潮流中总有一些趋时者不遗余力地大搞“稀奇竞赛”(Rarity game),如将古典建筑叠加在服装上的木乃伊化,各种玩具型的卡通化,造型狰狞怪诞的魔鬼化,似乎愈奇愈好。它已远离了服装应以人为本的法则。可见“时尚”也不一定是好东西。英文fashion可译为时尚,主要指的就是服装试样变化的潮流。
服装变化上的时尚与诗歌上的时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观赏对象和艺术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活动的体现出来的“力的式样”在性质上趋于对应时,也就有了共鸣,他们称之为“异质同构”。作为一个大背景,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实为一种潮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重新审视它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要肯定的,第三代诗潮的涌现并非偶然,它是继朦胧诗后的又一次精神的解放。如果说朦胧诗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诗的审美性质,显示了肯定自我的价值观。诗人将是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我引入诗中”⑴,那么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向纵深,他们继续轰击原有新诗的形成的意识形态硬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与之相适应是追求灌注生命意识的语感、语调、语势,由诗的语言“陌生化”而转向日常化的原生态。它的独特贡献就是对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形成假崇高、假神圣、假喜悦、假悲哀的消解。在人类生活中,崇高、神圣、喜悦、悲哀都是必不可少的伦理感情,可是一旦掺了假就如同变味变质食品。更为可怕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常在打着崇高而神圣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强迫大多数人作出喜悦和悲哀的虚假表演,它鲜明地反映在为实践检验是错了的各项政治活动中的人们表现,大到如“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摇旗呐喊;小到像除四害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一旦被钦定,均在神圣和崇高的旗号不是被唾骂被打击,就是陷入灭顶之灾。诸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胡风、巴金、老舍、艾青、丁玲等,以及被科学家判为益鸟的麻雀在短短的8个月中竞被消灭了19.6亿只!那些看来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人面对被批判者有几份真实的感情可言,明言人一看便知,因为被迫才不得不如此表演。对此,第三代诗人深恶痛绝,尤其对那些制造的虚假表演的“导演式的人物”,他们常常被罩上神圣的光辉。诗人雨田说:“看见了吗?他不分春夏秋冬/以他存在的方式挥起手臂/过去的岁月/象一个真实的春天/针芒的斗争无比/有嘴的人不能说真话/有嘴的人/说出鬼话/真理被谎言刺伤后/此时你是否仍在转眼不改脸色/注视着南来北往的汽车和行人”。(《另一座城市的塑像》)伟人毕竟有伟人的“质”,但用造神运动方式的创造出来的崇拜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它源于一种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中,首先是默祷,在默祷中,你把这个人的神圣想象得无限崇高,把自己看得无限渺小。以净化灵魂的方式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块一无所有的“空地”,由造出来的神占领取代,由此,第三代诗人就; 热衷于在他们诗中以非崇高、非神圣的方式、将伟人平民化,还原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如于坚的《贝多芬纪年》《罗家生》,柯平的《陈子昂登上幽州台》、《车至剡溪下游突然想起李白》。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宙斯,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和普通人一样,照样“失恋”,“感冒”,有着他们同样的苦恼,生活平平常常。如诗人说:“十八世纪某月某日某地一职员病休在家/某地以剧院客满/贝多芬双耳全聋/十八世纪某月某日/好天气/供应烤面包/一个男子和老婆上床睡觉/路德维奇·凡·贝多芬逝世”。伟人之所以愈来愈不真实,是人们给他附加的意义太多了。由此第三代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关注他们由于所处生存状态的喜怒哀乐。代表诗作如于坚的《罗家生》。诗人笔下的罗家生实在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位工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但因为太平凡了,谁也不注意他,可是当他出现在诗人笔下,诗人以不动声色再现他的不幸时,人们才感到震惊。多少年来,我们的诗坛是否太多地关注伟人而对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视而不见。诗人的这种“近距离”表现方式拉近了艺术与观念,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它无疑是新诗的一大进步,然而过犹不及。在消解了传统价值与精英的同时,也为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委琐者、骗子、痞子张目,价值的虚无必然使伟人、常人处于同一个平面,由于是削平深度,便形成了文学平面。正如一位诗评家的指出的上述主张“曾鼓动和引导了许多涉世未深的诗歌初习者对‘朦胧’诗所拥有的现实批判精神的轻率遗弃。大胆引进关于个人的题材,袒露自己的压抑、不幸、欲望和野心。历史现实中的行为和事件,伦理的诫条和神秘宏大的情景不是纷纷退隐,就是一无例外地受到嘲弄、短暂、琐屑、卑微的行为和场景,乃至粗俗的嘴脸和不雅的谈吐,纷纷出演主角。”⑵
第三代诗人同样重视诗歌语言,他们的名言便是“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虽然认为诗是一种语言游戏,但却不是一种为玩而玩的游戏,而是诗人介入社会的一种特殊游戏方式,它应是严肃的、认真的,它常伴随着苦难。他在《棕皮日记.1966》一文中就说:“如果游戏在汉语中往往被理解为不负责任、戏弄等等,那么我可以为‘游戏'加上一些限制词。严肃的、伤筋费神的创造性的等等……西绪福斯的劳动可以看成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不是命中注定的,谁愿意去玩啊!”然而,由于长期来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阐释权,诗人是无法进行如于坚所认为的那样语言游戏,语言成了凝固的板块。对此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文革中广为传播的流行语“一句顶万句,句句是真理”。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取得了上述话语垄断权后,他的话语就必是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它可以指鹿为马。语言本身是思想交流、生活的工具,可此时语言却成了少数人愚弄大多数的魔方与陷阱,对此,非非主义诗人何小竹深有感触。他写出了历来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不少人为突然飞来的横祸击倒的场景: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人就会记得/一个动词会叫人死/他们隔山打石,痛击你的/脑袋和灵魂。/你翻开语录,寻找武器/你可以在白天抵挡,却不敢保证/在梦中不会走漏风声/动词们成纵队排列。不是请客吃饭/那样温文尔雅。/有人谴词造句/有人突然在名词中消失/“唉”的一声,想为虚词……
文革中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赫鲁晓夫”系指内定了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打倒他,全国8亿人民被裹进了一场空前的风暴,其结果是刘少奇死了,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10年之后却证明了这关键词是不存在“伪问题”。何小竹所说的“一个动词叫人死”不是千真万确的吗!
大学问家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何小竹与季羡林感受是同样的。
语言学家徐友渔更是从理论高度指出:“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当今世界上许多武装冲突,分离运动,都有语言方面的根源。这似印证了《圣经·旧约》第八章中的一则寓言。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头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要看世人所建成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
这则寓言深刻地告诉了人们,如今世界上还存在隔绝,如同聋子对话,语言隔绝之所以能形成,就是耶和华这样的人垄断了语言的阐释权。“人类的得救,一是包括拆语言的墙,填平语言的鸿沟。”⑶非非主义理论家们有感于此,他们在《非非主义宣言》中明确宣告:“我们要摒弃感觉活动中的语义障碍。因为它使诗人与世界按语义方式隔绝。”并指出“要捣毁语言的板结性,在非运算地使用语言时,最大限度地解放语言。”⑷然而他们的创作与主张却是一个悖论,那就是要反对现存的语言规范就不得不打破它另造新的语言,然而诗人与读者在解读时还不得不依靠原有的语义加以阐释,否则就给人感到不知所云,前卫画家徐冰的《析世鉴》,乍看画面是一个个整齐的方块汉字,但却是从任何汉字字典找不到的汉字,只是一连串没有所指的能指,一种纯粹的符号。如果仍在绘画中,因诉诸视觉,《析世鉴》上的“伪汉字”还可起到装饰作用,那么非非主义诗人们的一些诗作就不堪率读了。诗并不是纯语言,在它后面必须体现我们现实中的问题。“艺术一出现‘纯’就意味着问题的消失,而艺术没有问题,也就失去了永恒的活力”⑸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枚举,仅从以上例征,就不难看出新生代诗人们的主张和实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如此,但因是看到传统诗歌中的“问题”而发,在大多数诗人和读者还处于浑然不觉状态时,这些诗人们的超前意识却表现出他们的先锋精神。“先锋之为先锋就因为它超前,与众不同,有点奇形怪状之意——如果先锋一上来就被公众认同,如果先锋一上来就与大众阅读拉平,如果先锋一上来就与传统接轨,只有连续,没有断裂,那还谈上什么先锋呢?”。⑹而“时尚”之所以称之为“时尚”,同样是因为具有先锋特征。英语trends也可译为“时尚”,但它与另一可译为时尚的英语fashion有着质的不同。前者体现为一种自觉了的大众走向,一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追求的潮流。著名的文学史家林庚教授就认为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应强调精神文明。“精神方面的影响主要靠艺术的熏染”,“都说中国是儒家的学说占主要地位,这也没有错,但对于人的精神影响,主要的还是诗教”。⑺诗教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应是回答什么是诗,诗人何为?
什么是诗?它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但又有别于散文语言。由于诗歌是从音乐中分化出来,这就决定了诗歌语言必须依靠音调、音韵和节奏等音乐方面的因素产生效果;作为艺术的一种,它又应有着社会交往功能。如美国文艺理论家埃德曼所言:“更确切地说,诗歌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在诗歌艺术中语文这种媒介处于最引人注意的前哨位置,无论是诗人或是听众,读者都不会忘记诗歌运用的语言。正如桑塔亚纳所说,诗人是锻造文字的金匠,当诗人被文字的声音对于感官的效果说感染时,他的读者也会受到感染。”⑻
明确了什么是诗,再看诗人何为?我们不妨看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皮萨列夫说:“诗人——如果不是伟大的思想斗士,大胆无畏,无可指的‘精神斗士’,像亨利希·海涅所说的那样,便是渺小的寄生虫。”
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己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的喉舌。”
高尔基说:“不要把诗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从以上论述看,他们一致地认为诗人应为社会、人生而创作,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感知他们生存状态中的喜怒哀乐,为促进人类社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即是超越了对物质追求的终极关怀,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一个有着健全人格的人,必须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20世纪已过去了,人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惊叹不已,但人类几千年来的彼此争斗都留下的教训也触目惊心。据历史学家粗略估计,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995年世界上就发生过4500次战争,死亡人数70亿,为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不惜发展残杀技能:刑具、武器、谋略;可见人类的敌人为人类自身。当代最著名的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惨淡阴暗的未来图景。这似乎过于悲观了,但理论的悲观比盲目的狂热好得多。而不是给人们分发进入虚幻天国的入场券。德国哲学家蒂利希就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存在的烦恼。一个尽管竭力想逃避烦恼,但除非他有勇气把烦恼当作人生于世不可避免的处境的一部分接受下来,他就免不了受它袭扰。只有接受烦恼,他才会有生存的勇气。”⑼
当我们以什么是诗、诗人何为的价值判断对照第三代诗潮,就可以看出某些诗人创作追求的实为后一种“时尚”(fashion),也就是在服装变化中因追求猎奇而形成的时兴、风尚、风气导致“胡闹”,它的泡沫状态最终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冈布里奇正是从这个角度谈起文艺发展中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当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因循守旧与墨守陈规受到冲击是必然的,然而却有些“别具用心”的人为了引人注目而玩弄一种“时尚胡闹(follies of fashion)”,他就是以服装变化中的猎奇为例加以说明的:“在一个时期,又可能是胸肩的大胆袒露、发型的高度和裙衬的宽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竞争已把时尚变成了一种声名狼藉、愚昧玩劣的‘过分行为’。”“但是偶尔这种竞赛会变得流行起来,并且达到全体参与的临界规模。不管我们是剃发,还是系领带;是喝茶,还是滑雪,我们都加入了‘跟着头领跑’的竞赛”。⑽在中国,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某些“新潮艺术家”的所谓“创新”和“反传统”,实为一场“时尚胡闹”。无独有偶,这种“时尚胡闹”在第三代诗潮诗人中也有充分表演,这里仅举数例:
先说杨炼,他的早期朦胧诗为人称道,然而他的后期的诗作却为年轻的第三代诗潮诗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是他的文化寻根诗,如《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诗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作者说:“《自在者说》十六首,为以《易经》为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一部,《与死亡对称》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二部分。”诗人以诗的形式阐释古老的《易经》文化底蕴,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读者面对的却是这样的诗句:
传播鼠疫的手,猝然掰碎身体里的一座汞矿
第一天的红色在舌头上蜕为蝗虫
——《自在者说·天·》
影子佝偻的太阴历已绕过毒箭
溜过来 读 病与年轮
——《与死亡对称·地·第一》
读后的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读者之所以有如此感受,并不是因为诗中有太多的西方意象和典故,而是通篇都是割裂的词,而词却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人们都知道,寻找意义永远是阅读的目的,即使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它也是在意义的引导下进入角色。这样的文化寻根诗多少像时装中那种将古代建筑、如紫禁城加在服饰上的木乃伊化的表演。
比之杨炼,在语言试验上走得更远的是钟鸣的诗作。他的诗意象奇特而流畅如大珠小珠,但同样不为读者接受,这是为什么?如《裸国》十六节中的片断:
“风吹过草原,我的两眼茫茫。血,在碑额上停止无用的奔流。羊群在最后一线烛光中遭到女巫灼烈的语言放逐。光明无畏黑暗者最初的光明,树巅上神秘的叶子在头顶消失,牙在阴影里恢复,石麒麟和玉蟾蜍。优美的乱伦,人类的俗气,得到完美的恢复,而灵魂,荡秋千的影戏,moving picture,则变成傀儡。”
当读者面对上述诗句时,同样会一片茫然。
其情形,如同当年朱自清在评论李金发诗所说的那样,他的诗单个儿的词语都可以懂,然而全在一起却不知所云。如同一粒粒珍珠,必须有一串儿安然无恙地将它串起才成为项链,李金发的诗缺少的却是这串儿。如从语言学角度看,它只是没有所指的一连串的能指滑动。是巴尔特所认为“能指完全独立于所指,而无拘无束地和文本打交道,追求反应的一贯性和有效性而不是客观性和真理性。”⑾由于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就导致语言意义的丧失。“在这时里,语词的双重功能被剥离去了一重,它的所指符层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词语的能指符层面。文本变得至高无上,而作为支撑文本的人类现实生存经验反而变得空渺和无迹可循。词,仅仅是词,它不再指代什么”。⑿阅读本应是得鱼忘签,但结果却是得签而忘鱼。这种语言游戏方式显然是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种卡通式的时装表演,只能在舞台上“胡闹”,他与于坚所说的“语言游戏”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些诗人都以先锋自居,并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它的至命处恰是因为没有思想内涵,而逃避社会责任失去了感觉,成了没心没肺的舞台上骚首弄姿的时装模特。至于主观意象派诗作实在是等而下之。吴非的
修着/在/久以/的/个是故事的/这你发生//替时/肤色/在村//被你走中/过你/留/下着的/一层/树
读者不禁要问,这也是诗吗?诗人孟浪说:“坦率地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不喜欢这类制作。但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它有助于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也就是说,从什么是诗的反面看出它不是诗。”⒀作者也说:“它是我边缘意识的错乱反映”。⒁其实这样的语句连精神病人的错乱呓语也说不上。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话并不是没有规则可循,他们遵循的是“旧逻辑”。即“相似即同一”的规则。正常的逻辑“A像B,却不是B”,而前逻辑则是“A像B,A就是B”将两者完全等同是荒唐的,但仍是有迹可循。保罗·克劳瑟在批叛某些先锋派艺术所谓独创性时说:“的确,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却创造出一种独创性和胡闹(original nonsense)。”⒂早在近千年前金代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批评了这种哗众取宠的现象:“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诗歌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存在。英国诗人邓恩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在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们受到损失,因此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必须为有意义而活着,何况肩负着诗教的诗人。以“人在生活中游戏,诗人在文字中游戏”的态度进行写作,并将它视为“排泄”,⒃这正是杜伏海纳所告诫的:
作品自身的语言不要象手淫那样从身上获得满足,作品多少参照世界,即使为了否定世界或者把世界作为想象的一个背景。⒄
在时装表演中,为取得一时哄效应的时尚可以朝秦墓楚,但作为社会中一员的诗人对意义的追求却是永恒的,而不应是以“胡闹”打发日子的“空心人”,如汤因比所说的“内心无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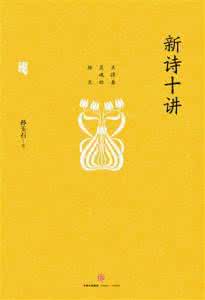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