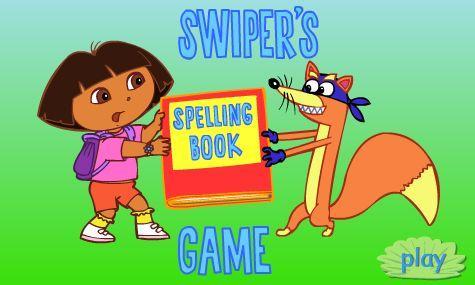山里的风
看不见你的微笑,
摸不到你的脸颊。
闻不到你的芬芳,
寻不见你的踪迹。
只听见你的呼吸,
山风一样的自由。
朝阳无力地穿过薄薄的雾气,散发峨眉山的佛光。萧萧的落叶在凉风地呵护下,尽情地飞舞,静静地安眠。不知何处飘来的鸟唱在山林里时起时落,增添几分静谧。清晨的山村如同熟睡的婴儿,贪婪地呼吸着上帝的恩赐。
山里人称这村庄为石桥村,顾名思义村中有一座石桥。
据老一辈介绍,这座石桥历史悠久,故事丰满。大概清朝年间,本村的一位穷书生,数次名落孙山,受尽他人无情的讥讽,依旧奋发图强,每天大清早到河滩读书,晚上挑灯伏案。日复一日,山里的风吹转四月的风车,静静流淌的河水带来四季的变化。他坐的那块大石头早已被磨地光滑溜圆,这让其它粗糙的石块羞愧难当。穷书生的十年寒窗剑终于拨开清晨的云雾,迎来百合花的春天。
他成了这个山村的第一位秀才,也许是仅有的一位。山村里的乡民筹资为他修建一座山庙,他成了庙中的文曲星,全村乡人顶礼膜拜。不知谁突发异想,在穷书生的圆石旁修建了一座石桥,从此这个不足百人的野山村更名换姓,成了如今的石桥村。
石桥现已残垣断壁,斑驳衰老,力不从心地刻着从古至今的点点滴滴,倾诉着沧海桑田。
岁月的变更,脱落昔日的辉煌。香火的延续,石桥村平静地繁衍。石桥村的户户人家,住得比较分散,除了春节生死,很少聚在一起。毕竟山路不好走,翻山越岭才能见一见曾经的面孔,聊一聊现在的故事。
山里的房子大都是石块垒盖而成,有的还糊上泥土,添加几片青瓦,铺上几束毛草。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挂满外墙,一串串金黄的玉米堆满小院。平日的山村静得像半山腰的夕阳,慢节奏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难得的生机也不过是些鸡叫狗吠,虫唱蝉鸣。
山里的风吹起日出的炊烟。皎洁无比的蔚蓝天,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串联在空中,犹如成群结队的妙龄女郎,个个身着妩媚的沙滩裙,披着柔软的白纱巾。喘着热气的红日,围着狭长明亮的云带,不安分地斜挂着,要把树梢点燃,还向河滩倾泻它那橘红的光辉。
山里的风吹灭日落的灯火。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了下去,深红变成绯红,绯红变成浅红,浅红变成橘黄,橘黄变成淡灰。最后,当这一切的绚烂彻底地消失时,天是那么的高,那么的远,顿时露出肃穆的神色。翠菊似的月亮犹抱琵琶半遮面,露出娇羞的脸。月光在河面上闪烁跳跃,如同乐曲中轻盈的拨弦,泻在地面上则迷茫空灵,似水墨画中不均匀的笔触。数不清的星星欢乐地眨着眼,像树林中飞舞的萤火虫。
新鲜香甜的山风再次路过石桥,像是大地发出幸福的叹息。
一声声啼哭打破山村昔日的宁静,男娃儿的诞生让老刘家喜气洋洋。老刘家虽然有一个11岁的女娃,可生男娃的梦想在山里人的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在遥远而贫穷的山村,千年的封建思想并没有被吹得烟消云散,依然紧紧地咬定山里人的神经元:女娃儿是泼出去的水,男娃儿才能防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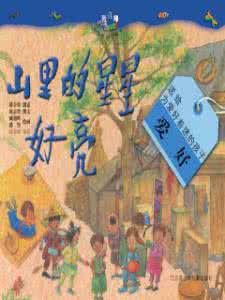
4月2日全村总动员,庆祝小刘的降临。老刘大半辈子的愁眉终于得以解开,露出“今生无憾”的狂笑。小小的男娃,寄托整个家庭的希望呀!
按照乡俗,娃儿出生12天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喜宴——“十二晌”,也叫“小满月”。据前辈说,娃儿到了十二天,母亲因生产而打开的骨缝已经合上,已经过了月子里最重要的一关。按照习俗,这一天要给产妇吃饺子,寓意捏骨缝。
“十二晌”是欢迎小生命诞生的一场隆重庆典。这一天,男女双方的众多亲戚,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不论道路远近,带着礼物簇拥而来,贺喜道福。大户人家有的在数百人之上,平常人家也有数十人。
老刘前面忙着请人垒烟囱,架大灶,后面急着找人租桌子,借板凳。没多时,大棚搭好,音乐四起。小院里油气缭绕,大锅炖肉菜,小锅炸油条,大桌堆馍馍,小灶出酒菜,桌子板凳整齐排列,碗筷酒具擦洗锃亮。
在众多礼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外婆的:首先是六双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虎头鞋。虎为百兽之王,穿虎头鞋,据说可以祛病辟邪,保佑娃儿长命百岁。鞋上除了必有的虎头、虎眉、虎目外,还有莲花头、牡丹头、南瓜头、、、、、、有歌曰:一对牡丹一对莲,养的娃儿中状元;一对石榴一对瓜,娃儿活到八十八。其次便是给娃儿做的迷糊鞋。其它鞋是鞋底鞋帮分开做,然后缝在一起,可迷糊鞋必须要帮和底连在一起。鞋底再缀几缕彩缨,意思是:孩子刚刚来到人世,穿上此鞋可以在阳间迷路,忘记去阴间的路,能够扎下家根儿。
这一天也是娃儿出生后第一次穿衣服的日子。穿什么衣服也有讲究:姑姑的袄,姨姨的裤,妗子的花鞋,度起意无非是“红红火火过日子,清清白白长成人”。头上再戴一顶由花手绢、小毛巾扎成的“官”帽,盼望长大成人做大官,发大财,能够扬眉吐气。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后,揭起保鲜膜,一盘盘饭菜冒着腾腾的热气。瓜子、糖果刚到桌面就被娃儿抢得精光,只留下光亮的盘子。席中的老人必先相互推辞一番,才拆开渡江烟,一根根地散给众人。
酒至半晌,老知来到席间,热闹的大棚一下安静了许多。“粗茶淡饭,不成敬意,大家吃好喝好!”,老知鞠完躬后,老刘和史云也跟着鞠躬。大家坐下后,继续推杯换盏。
可“坐桌席”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吃顿饭,里面也有许多规矩。比如上鱼时,鱼头一定要对准德高望重的老者,以示敬意。如果席间没有足够的位置,娃儿就“挂拐”,站在大人身旁,想吃什么就叫大人夹在碗里,但绝对不能哭。
娃儿们由于先前吃得急,很少能够吃到席末。有了足够的地方,大人们索性站起来,右脚放在板凳上,一边吆喝一边划拳,直到深夜。
热闹过后,山风温顺了些许,如同住在谷口等待山花开放的女郎。
悠悠的白云匆匆地渐行渐远,静静的生活依旧慢慢地舒展开来。山村里的娃儿就像一阵风,自由地飘荡,欢快地成长。山里的毛竹刻下他们歪歪斜斜的字样,河滩的两岸传来鱼跳的声响,田里的陇上留下一串串小脚丫、、、、、、这些都是娃儿们的杰作!
18岁那年,姐姐刘月就要嫁人了。这是山村的习俗,女娃要早嫁,男娃早立家。那天鞭炮声合着唢呐声响彻整个山村,为阴冷的石桥徒增了几分喜庆。
牛bb文章网欢迎您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