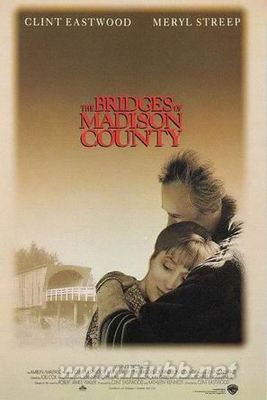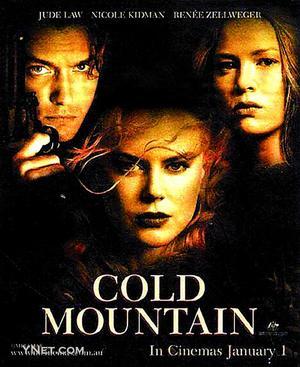中国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浪潮代表作,由此产生了“第五代影人”之说。陈凯歌、张艺谋成为其代表人物。影片的影像冲击力,颠覆了此前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方式。
1939年冬天,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为收集民歌来到陕北,正好赶上一家人娶亲,目睹了陕北女孩子的命运。他借住在翠巧家里。但他不知道翠巧就是他在延安听说的会唱民歌的“人尖尖”。翠巧也面临着订好的“娃娃亲”,她爹说:“定钱一半发送了你娘,一半凑数给你兄弟定了婆姨。”又是一场婚姻悲剧。由于顾青在这一家人当中宣传了延安的女子得到解放,以及“用镰刀、斧头、老钁头,砍开大路让工农走”的思想,翠巧在顾青走的那一天,在半路上等他,要求跟他一起去延安,但是顾青说,“等领导批准”了,就来接他。翠巧的四月的时候如期嫁人,她等不到顾大哥来接她,在夜里独自撑船东渡黄河寻找八路军,结果被浪涛卷走。影片结束在黄土地上农民求雨的浩大声势中,翠巧的弟弟憨憨看见顾青,逆人流艰难向他跑来。
人文思考的深度与艺术表达的强度是《黄土地》震撼人心的主要原因所在。此前,中国电影的道德关注与社会评判是电影的主要支撑,正误好坏的认知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黄土地》将创作者的关怀扩展到沉默无语的黄土沟壑和终年劳作的百姓、高悬冷酷的天际与仰首叩拜孜孜以盼的臣民、周而复始无爱无恨的仪式婚约与隐约驿动的个人情感。千百年来的土地规则富含哲理,却沉重地桎梏着人的心灵跃动,八路军公家的新生活带来了冲破传统的希望,却没有按照电影叙事的惯例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顾青擦身而过,放弃了拯救女孩子翠巧,翠巧的希冀与怨恨如同黄土地上的所有民生一样,只有寄托在沟谷中久久难以散去的“信天游”中,令人心碎。这正如影片中顾青问翠巧爹的话:“陕北的民歌千千万万,怎能记下?”翠巧爹说:“日子艰难了,自然就记下了。”这既说明了民歌是陕北人唯一的心灵寄托,也说明了艺术和一切创造的真谛。不可抗拒的传统、无形的土地上规矩、人的悠久生存状态,成为没有决断的宏阔展示对象。天人合一的关系思辨,生命哲学的形象思考,文化探寻的注目眼光,成为《黄土地》难以分离的主要内涵。关注这片土地上人的无声命运是影片厚重感的主要体现。
影像语言的自觉把握把是《黄土地》另一艺术价值。传统中国电影对影像本体的自觉程度远不如对社会内容来得重视,声画语言自身的造型因素与独立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挖掘。第五代电影人的重要功绩就是为归还电影本体的价值做出重大贡献。本片的影像语言凸显出独立的意义。包括注重色彩的表意作用的开创性,构图对内涵意义的突现,影像表现的文化意味的寄托等等。注重色彩的表意作用这一开创性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大片黄土地的色块,婚礼铺排的红色和乡民黑色的组合,构成创作者所要表现的文化内涵。构图上对正在主角黄土地与人的关系处理为土地占据巨大空间,人只是天际线上的渺小存在。画面已经显示了内涵。影像表现的文化意味无处不在,尤其是婚礼、祈雨、腰鼓的段落饱满扎实令人震撼。祈雨的仪式化场面表现人与天的旧有关系,安塞腰鼓展示勃发的生命力量,预示着人与土地关系的变迁,和全片稳重的镜头语言形成差异的动感镜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内在跃动感,与憨憨逆着人流向顾青跑去的镜头一起,呈现出突破厚重寻求顽强生机的希望。
这部电影的主体是现实主义的,里面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不是英雄,也不是列士,前半部分拍了他们的生活虽是艰苦,但平平淡淡,而不是轰轰烈烈,甚至刻意积蓄隐忍,不讲大道理只说小事情。但是到了后面部分那个延安的大腰鼓表演,那里却拍的场面宏大震撼人心极其浪漫,有一种非常震撼人心的美,包括还有求雨那一段都是。这两段大场面中的浪漫主义的美感对导演陈凯歌的影响应该说非常之深,对本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更是明摆着的不用说。

《黄土地》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也是陈凯歌对中华民族力量的反省和思考,这部电影正如片中的陕北民歌信天游一样,既流淌着苍凉雄浑的艺术血液,又承载着厚重深远的文化使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