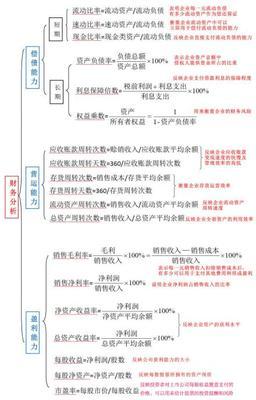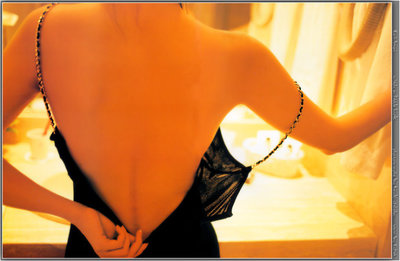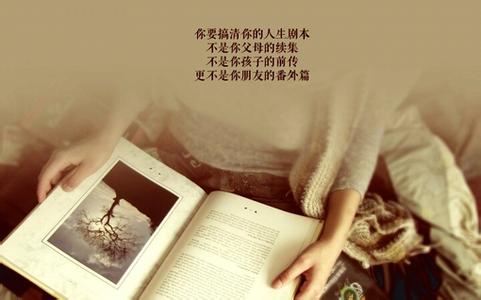北角,位于香港岛的最北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避走香港的上海人见这里人口较疏,落脚在此。一时间,北角有了“小上海”的称号。
六十年代开始,富裕的上海人陆续搬迁到新开发的半山、太古城一带,福建移民涌入,北角又成了“小福建”。
不过,如今在这里依然能找到不少上海的痕迹。比如,打着“上海”名头的老式理发店,以及乡音难改的老上海人。
▼
此地做头发,大家好讲讲上海言话呀
“哒哒哒哒哒哒……”红绿灯发出急促的提示音,快得跟摇拨浪鼓一样。在香港过马路,仿佛有双无形的手在后面推着,不敢放慢了脚步。
也不是什么节假日,可在繁华的闹市区,常常产生摩肩接踵的场面。9月里日头还有些毒,在街头随着人流疾疾往前走,周遭听到的都是广东话,这让外省来的人很容易产生异乡感。
走到北角渣华道、糖水道,沿街竖了块牌子:“上海侨冠男女发屋”。推门进去,喧嚣被隔在门外,节奏放慢下来,好像时钟也跟着往回拨了几圈。狭长的店面向里延伸,镜子里映出头发花白的师傅和头发花白的客人。那是一股熟悉而又日渐遥远的气息,使人联想到如今在上海也已为数不多的老式理发店。
沙发上放着供客人等候时消遣的报纸,这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了
坐在当中的阿姨之前一直不大响,此刻跟高师傅闲聊起来,说的竟是上海话。她不笑的时候面孔有点凶相,不过只消用上海话跟她打个招呼,脸上的线条马上柔和下来。
“侬特地从上海过来啊?”她大感兴趣。问起她来香港多久了,她说:“三十年唻。阿拉先生先出来,我就跟着出来了。”
刚来香港的时候她住在北角,在侨冠做头发很多年了。“大家好讲讲上海言话呀,我就认牢这个师傅了。”她说,“这爿店老字号唻,北角上海人多数到这里来。”
现在,她已从北角搬到了观塘。“这里是香港岛,观塘在九龙,就是浦东、浦西的区别。”她这样解释说。每到要烫头发,她还是习惯回这里来。
“阿拉做熟客比较多。”高师傅也把语言频道转换成了上海话,又指指旁边的阿婆说,“这位阿姨过两日要到上海去了。她年年去,待几个号头(几个月)再回来。。”
“我有辰光一年去个两趟。”阿婆慢悠悠地道,“阿拉在青浦买了别墅,静安区也有房子。别墅我不大待,路远不过,多数住在静安。我觉得现在上海跟香港差不多了。”
“现在变化老大的。”阿姨也接口说,“我觉得上海开销大过香港了。这方面好像深圳比较好点。”到底是会过日子的上海人,马上比较起了几个城市的物价水平。
▼
香港人所讲的“上海”,是一个统称
“侬在上海待过伐?”阿婆问高师傅。
“待了两三年转去了。阿拉舅舅、舅妈住在提篮桥杨树浦路。埃个辰光(那时)没粮票,侬吃啥呀?伊拉自家都没吃,我后头回扬州乡下去了。”他说。

仔细听的话,高师傅的上海话里带有扬州口音。事实上,香港的“上海理发店”多数是由扬州人开的。他解释说:“香港人所讲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上海’是一个统称,江苏人、浙江人,伊拉都讲是'上海人’。”
高德田算是子承父业,父亲早年是在上海出师的。“上海老早剃头店都是阿拉同乡人开的嘛。”他说,“爸爸年轻辰光在金门饭店下头的华安(理发)做。那个剃头店的门是旋转的,有红头阿三开门,在上海算特级的了。”
1949年,高德田的父母跟着南下的上海人一起来到香港,把4岁的他留给扬州乡下的爷爷奶奶照顾。“人家请伊拉来的。埃个辰光不要通行证,直接就过来了。”他说。
由于内地人大量涌入香港,1951年,香港放弃了实行超过100年的自由往返政策,首次设立了边界,规定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等到高德田要来香港时,就没这么容易了。
“我10岁超过的辰光,爸爸写信转去(回去),叫我申请出来。没噶容易批下来,申请了几年。”他回忆说。申请批准的时候,高德田14岁了。1959年,他由奶奶带着,从上海乘火车到广州,凭入港证买票到深圳,再由罗湖进入香港。
收音机里一直在播放广东话的电台节目,就像是店里的背景音
和许多早年来香港的人一样,他用“蹩脚”来形容当时的香港。“比上海推般(差)多唻,没高楼大厦,都是三四层高的唐楼。中环、湾仔、铜锣湾都是后来填海发展的。香港老早小来兮的,人也没噶多。”
“埃个辰光,上海繁华过香港。”他总结说,接着又话锋一转,“不过解放以后上海就推般了。到一九五几年要粮票,就更加尴尬了。侬要买好的东西,没的。衣裳嘛,清一色蓝布衣裳。香港是一九七几年开始逐步逐步繁华。”
来到香港,他先进学校读书。“读了一腔,读不进哎。广东言话不懂,ABC也不懂,哪能读法子?字也不识,内地是简写的,香港是繁体的,看也看不懂。”当时,父亲已经在英皇道上开出了一家上海理发店,他索性到店里做起了学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上海理发店最兴旺的时期。上海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时髦”,打扮饮食无一不走在香港潮流的前沿。上海理发师傅给香港带来了“平头装”“蛋挞头”“飞机头”等经典发型,加上剪发手法特别,服务周到,格外受欢迎。当时理发店只要挂出“上海”两个字,收费就要贵不少。
星期二是侨冠店休的日子。师傅们都休息了,只有高德田仍在店里,留了个年纪比他还大的洗头工帮忙。
“做这行就是没保障。”他说,“不像国内有退休金,香港没的。阿拉没有退休年龄,有得做就有得拿,做到不能做为止。”这天他穿的是蓝色工作服。每逢周二他理男发,老客人也都知道店里的这个惯例。
此刻高德田给一位老伯理好头发,开始给他刮脸。“修面,修胡子,阿拉店里厢跟上海传统剃头店一式一样。”他说。
男宾部的陈设有许多有趣的“机关”。就拿理发椅来说吧,据说比这家店的年龄还大,用了四十多年,当年是从日本进口的,一把椅子要一万多。“真皮的,还可以按摩。”高德田拨了一下椅背后面的小开关,椅子震动起来。他又扯了扯椅子旁边挂着的一根带子,在上面磨了磨剃刀。原来这椅子还自带磨刀功能。
透过理发店的玻璃门往外看,渣华道上人来人往。北角在香港岛的最北端,二战前人口并不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避走香港的上海人见这里人口较疏,落脚在此。一时间,北角有了“小上海”的称号。此地人口日渐密集,曾一度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六十年代开始,富裕的上海人陆续搬迁到新开发的半山、太古城一带,福建移民涌入,北角又成了“小福建”。不过,在北角至今仍可找到众多上海餐馆,像侨冠这样较具规模的上海理发店也还幸存几家。
-End-
写稿子:韩小妮
拍照片:韩小妮
画图片:顾汀汀
长按二维码并识别可关注本号
本号所有文图均为原创
如有转载需要请与后台联系
谢谢支持与理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