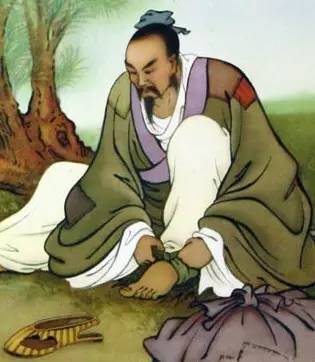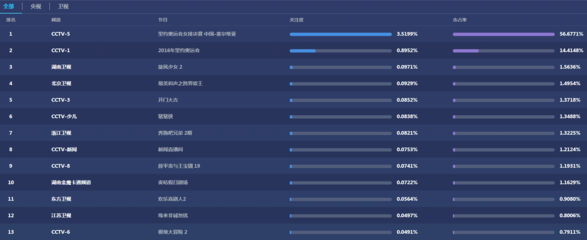来源: 《国文天地》2016年第7、8期
經學文獻投稿郵箱
jxwx12@yeah.net
作者简介
张伟,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感谢作者授权经学文献转载)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全8种)
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之中,经学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经学的这种独尊地位集中在古典目录中有集中体现:首先,在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的综合性目录中,经学类书籍都居于首位;其次,历代图书目录都著录了数量众多的经注、经说著作,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丛书综录》即著录古代经学著作7646部。除此之外,经学自汉代以来还被纳入国家政教体系之中,对古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初,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王朝的覆灭,以经学为核心的政教体系也趋于瓦解。经学走下了神坛,步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自清末皮锡瑞撰《经学历史》以来,有关经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经学通史著作,如刘师培著《经学教科书》、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许道勋等著《中国经学史》、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又有经学断代史著作,如章权才著《两汉经学史》、焦桂美著《南北朝经学史》、章权才著《宋明经学史》、吴雁南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等,还有以经籍介绍为中心的经学史著作,如周予同著《群经概论》、范文澜著《群经概论》、杨伯峻等著《经书浅谈》、董治安主编《经部要籍概述》等。此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儒学史、教育史等相关学科的著作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经学史的内容。以上著作共同推动着20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为经学研究的深入和经学知识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迄今为止,在数量众多的经学史著作中鲜有能全面超越晚清皮锡瑞所撰《经学历史》者,大部分经学史著作在叙述框架方面还基本延续着皮锡瑞所构建的经学发展框架,在史料依据方面还基本以正史儒林传、《五经正义》、古典目录中的经部书籍提要等为主要资料,在体裁结构方面则多采用章节体形式。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以《经学历史》、《经学教科书》等清末民初的经学史著作作为最好的经学入门书籍。
∆郑杰文教授
如何在中国经学史研究上取得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进展呢?针对当前经学史研究方面的不足,我们在撰写经学史时,一方面要拓展经学史研究所凭借的资料,另一方面则是改变单纯的章节体叙事模式。只有将自己的研究立足于扎实且广泛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取得学术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只有运用更具包容性的叙述体裁,才能更全面地展示经学发展的生动图景。郑杰文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经学编年》)一书便是顺应这一学术研究趋势、满足这一学术研究需要的著作。
《经学编年》一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叙述了自西周至清末三千多年间经学发展的情况,总结了中国古代经学发展演变的轨迹与规律,最重要的是本书从编写体裁、研究方法、学术思想三方面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
一、编年体经学史的拓荒之作
编年一体,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甚早。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便已相当普遍,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作为成书于春秋时期的鲁国史书《春秋》。除《春秋》外,流传至今日的先秦编年体史书尚有西晋时期于战国魏王墓中出土之《纪年》残本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后者更是以其丰富的史料记载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成为先秦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秦汉以后,编年体史书仍长盛不衰。唐刘知幾于《史通》中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列为史书编写所采用的两种主要体裁,并详论编年体史书之优劣。
∆刘知幾《史通》
在刘知幾看来,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既没有重大遗漏,也不必重复记述;但是,编年体史书也有自己的缺点,即偏重于记载与政治变迁、军事外交等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却忽略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刘知幾此言可谓切中肯綮,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如《左传》、《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确实只偏重于记载政治史、军事史,而于学术史、文化史很少措意。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与编年体史书的时间性太强而学术文化活动往往不具备明确的时间因素这对矛盾有关。
20世纪以来,在西方特别是日本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章节体著作成为学术著作的主要体裁。章节体著作凭借其细致、明晰的分章划节将历史演进的线索清晰勾勒出来,便于读者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寻得历史演进的规律与线索。但是,在对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章划节的背后,势必隐藏着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存在又导致你不得不舍弃一部分历史事实以更好地适应章节安排的需要。因此,章节体著作的弊端——导致了历史叙述的单一化与历史事实的不完整性——也在撰写过程中暴露无遗。
有鉴于章节体著作的不足,当代学者也并未放弃包括编年体在内的传统史书撰写体裁。一部分学者立足于我国自古以来丰富的文献记载,对其中与学术文化活动有关的记载详加考辨,确定或大致确定了某些学术活动发生的年代。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诞生了数部编年体学术史,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汝霖撰作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梅新林等主编的《中国学术编年》以及姚名达撰作的《中国目录学年表》、陆侃如撰作的《中古文学系年》、杨翼骧等编著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刘跃进撰作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等。以上编年史涉及到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多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古典学术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却没有一部反映中国古典核心学术——经学发展变迁的经学编年史,郑杰文先生主编的《经学编年》的出版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经学编年》一书将西周至清末的中国经学史分为八个历史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在每个历史时期下面,又根据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分为若干个历史阶段,如将先秦经学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与中国经学史有关的事件。与以往编年史著作不同的是,此书在每条经学史事件的叙述之后皆有“文献”、“考论”、“相关论著举目”三部分,“文献”部分主要是列举经学史事件的相关文献记载;“考论”部分或阐述将此事件系于此年之下的理由,或对经学史事件的原委详加考证,使读者获得对此事件深入的了解;“相关论著举目”则开列学术界尤其是近几年学术界与此事件或此问题有关的论著目录,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指示门径。关于这种编排体例的优点,下文将有详述,此不赘言。
∆《春秋公羊传注疏》
和以往的章节体经学史著作相比,以编年体形式撰写经学史著作可以将经学史事件置于具体年代之下,确定其时间坐标,从时间角度对其进行把握与理解;此外,还可以在撰写过程中解决一些在经学史上有时间争议的问题,推动经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春秋公羊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是《春秋公羊》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但该书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作者年代不能确定的著作。关于作者徐彦的生活年代,共有两说:一说徐彦是北朝人,一说徐彦是唐人。持徐彦为北朝人的学者所举证据主要有:(1)徐疏所引书有一百多种,最晚的是南朝宋庾蔚之的《礼记略解》;(2)徐疏中注音之处多用汉儒所习用之直音法,甚少用反切注音;(3)徐疏所引群经之注具有北朝经学特点。持徐彦为唐人说的学者的证据主要有两点:(1)《春秋公羊疏》在两《唐志》中未曾著录,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北宋王尧臣等人所撰之《崇文总目》,但《崇文总目》仍未指出此书作者是谁,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始指出此书作者是徐彦;(2)唐代韩愈在《答殷侍御书》中曾说“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若《春秋公羊传注疏》出于南北朝时期,韩愈不应说除何休《公羊解诂》外“不见他书”。在这个问题上,《隋唐五代经学学术编年》的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将《春秋公羊传注疏》的写作时代定位至唐德宗贞元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并从中唐以后经学发展的总体视角来看待此书的撰作,将其作为中晚唐经学沿袭前期经学统一进程的代表作品,认为它是一部集汉唐以来《春秋公羊》学之大成的注疏之作。虽然关于《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撰作年代迄无定论,但《经学编年》一书所作出的新的探索与提供的新的研究角度仍然为此书撰作年代的断定做出了贡献。
《经学编年》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辨,将中国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典籍系于每年之下,在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现中国经学史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以详尽的考辨论证和详实的参考文献目录满足了对经学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经学编年》不仅填补了中国经学史编年的空白,也为新的中国经学史的撰作奠定了基础。
二、以文献为根本的典范之作
重视文献考据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优良传统。先秦时期,孔子即有关于“文献不足”之慨叹。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图书的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文本校勘的学术风气;而由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兴起之后,文本校勘和文字训诂更是成为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治学方法,并产生了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运用此法治学的经学大师。汉代以后,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继续发展。即便是在义理之学大盛的宋明时期,训诂考据之学也在学术界产生着持续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便极为重视训诂考据,力戒空谈、穿凿之弊病,以训诂考据为工具阐发道学义理,其曾言:“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字字句句对注解子细辨认语意,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解得两遍是两遍工夫。工夫熟时,义理自然贯通,不用问人。”其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考据之学的典范作品。正是因为朱熹对训诂考证极为重视,并以此为工具去阐发义理,才取得了其他理学家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并推动训诂考据之学在宋代迈上一个新台阶。至清代,训诂考据之学承前代发展之余绪,在学术界成披靡之势。清代学者在阐释经典时遵循“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学术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综合运用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来校理古籍,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称“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清代考证学在经学、史学、子学、小学、金石学等领域全面开花,达到了中国传统考据之学的顶峰。
∆《中国哲学史大纲》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学术方法的传入,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学也发生了新变。在传播西方学术方法并与中国传统文献考据方法相结合方面贡献最突出的学者当推胡适。1918年,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详细介绍了其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胡适所倡导的这一方法分为四个步骤:“述学”、“明变”、“求因”、“评判”。“述学”是指搜集、审定史料;“明变”是“把各家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求因”是“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评判”则是“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效果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而在以上四个步骤中,以“述学”最为关键,只有运用校勘、训诂等方法,将文献史料整理好,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好后三步工作,并写出一部系统、完善的哲学史著作来。胡适此论,虽为中国哲学史的撰作而发,但实际上可以为一切研究中国古代学问者所取资、借鉴,其中所强调的以文献考辨为本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精神尤其值得提倡。
如上所述,今日流行的章节体著作易于导致历史叙述的单一化与历史事实的不完整。而且章节体著作的撰写者还会在思想观念的左右下轻视乃至忽视部分文献史料,以至于在某些章节体著作中,文献史料仅仅被当作填充在撰作者事先拟好的章节中以助成其结论的工具,完整的文献史料被任意切割,失去了自身所应具有的价值与地位。相反,编年体学术史著作类似于传统史书编写过程中的资料长编,完全是以文献为本体来撰写的。其内容的组织与编排,一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每个条目的撰写都有文献资料作为支撑。《经学编年》作为第一部编年体中国经学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且《经学编年》一书的编排体例也颇值得称道。
《经学编年》的每一个条目之下都分为四部分:内容概要、文献、考论、相关论著举目。如此书记载周平王三十一年,卫庄姜夫人失位,作《绿衣》、《日月》、《终风》诗自伤。在“文献”部分,全文摘录了《绿衣》、《终风》二诗及《日月》诗之首章。在“考论”部分,对这三首诗的内容进行了立足于文献的考辨,先后征引毛传、郑笺、孔疏、朱熹《诗集传》、魏源《诗古微》、闻一多《风诗类钞》、陈子展《诗三百篇解题》、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等古今文献,得出了是三诗之内容皆为卫庄姜伤己之作的结论。在“相关论著举目”部分,则以目录的形式列举了与此一事件有关的论著,计有:高晓成:《〈诗经·终风〉篇诗旨集评与新探》,《攀枝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窦强:《〈邶风·绿衣〉创作时间考》,《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10期;姜荣:《试析〈诗经·邶风·绿衣〉之“绿衣”》,《汉字文化》,2006年第3期;方孝坤:《〈终风〉新解》,《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陈子展:《诗三百篇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人鉴:《关于“日居月诸”一语的训释问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刘大白:《白屋说诗》,作家出版社,1958年;闻一多:《风诗类钞》,中华书局,1957年等八种论著,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此问题者指示了门径。《经学编年》一书对其他经学史问题的论述也都如此条所示,在全面、系统地搜集、排比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扎实考辨,从而使此书既能按照时间顺序充分占有资料,又能在资料考辨的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经学史结论。
除了编排体例上体现出以文献为根本之外,《经学编年》一书还在具体内容的选取方面对文献史料给予了“特殊关照”。在先秦经学部分,该书详细记载了《礼记》、《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文献对先秦经书的征引情况,从而为我们了解西汉刘向、刘歆校理图书之前的文献流传情况提供了文本依据。而《先秦经学学术编年》对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关注以及《秦汉经学学术编年》对两汉谶纬文献的收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学史研究者的文献视野,为经学史研究突破陈陈相因的旧框架和书写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提供了文献支撑。
三、经学学术研究的创新之作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经学编年》除了在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拥有以上优点外,更重要的则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一部学术著作只有具备创新性,才会在学术界受到欢迎与重视,并成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经学编年》所具有的诸多创新之处正可以使其成为中国经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先秦时期,华夏大地上散布着数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集团。关于这些文化集团,前代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作了初步划分。除了从民族角度进行划分以外,从文化形态角度可以将先秦华夏大地的文化划分为两大系统:神守文化与社稷守文化。产生于先秦时期并迅速播散的六经文献也受到这两大文化系统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流传特点。神守文化与社稷守文化对先秦六经流传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时人对六经的征引上。神守文化重视祭祀,思维方式倾向于浪漫奇想,故在征引六经时,多将其看作助成自己观点的工具;山川守文化产生于农业部族,重视人际关系,思维方式比较保守,在征引六经时,往往将其看作古人遗训或历史事实。《先秦经学学术编年》在著录经学事件和经学人物之外,还对先秦诸子文献征引六经的情况予以关注,据统计,此书著录《礼记》文献征引62条、《墨子》文献征引22条、《孟子》文献征引15条、《荀子》文献征引76条、《吕氏春秋》文献征引19条,此外《庄子》、《管子》等书对文献征引的情况也得到了反映。这些内容为后来者研究先秦诸子对待六经文献的态度提供了资料,便于研究的开展,而通过研究先秦诸子对待六经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先秦诸子的文化起源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汉人将先秦诸子划分为“九流十家”的传统模式,建构一个新的、更接近于先秦学术实际情况的诸子学术体系。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学便成为了国家政教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在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状况。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发展过程必然充分体现国家政教的需求。西汉前期,《春秋公羊》学盛行,但自西汉中期之后,《春秋穀梁》学开始崛起。对于这一变化,《秦汉经学学术编年》的作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公羊春秋》学说的兴盛与武帝时期中央皇权渐渐加强而至于强盛的历史趋势相对应。至昭宣时期,《公羊春秋》所主张的王朝更替理论,已不合乎统治集团的利益,《公羊》学者所主张的‘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更是直接威胁到西汉王朝的存续,因此昭帝时立《穀梁春秋》博士,被认为亦有削弱《公羊学》的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学盛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孝经》类著作除“疑非古本”的《古文孝经》与题为“郑氏注”的《孝经》外,其余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对于这种现象,《魏晋南北朝经学学术编年》的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十分频繁,士人的正统观念较为淡薄,这使得儒家学说的权威性难以实现。不管是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还是宋、齐、梁、陈的更替,都是以篡位的方式取得政权。这使得统治者很难以‘忠君’思想巩固政权,只能提倡‘孝’,曲折地通过孝道达到忠君的目的。晋武帝之恢复三年之丧,晋穆帝、晋孝武帝、昭明太子、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讲《孝经》,梁武帝撰《孝经义疏》,无不对儒家之‘孝’推崇备至” 。以上无论是对西汉中期以后《穀梁》学兴起原因的分析,还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学兴盛原因的论述,都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经学“学随术变”的特点,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经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政教体系也有大有裨益。

∆顾炎武
明代经学自顾炎武以来便屡遭诟病,顾氏谓明代经学“无非盗窃”。至清代乾嘉时期,明代经学更是受到了乾嘉考据学家的批评。无论是顾炎武,还是乾嘉考据学家,他们批评明代经学的矛头所指都是明代经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病。这种鄙夷明代经学的学术风气沿袭至清末,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中直斥明代为“经学积衰时代”。民国以来,明代学术虽然逐渐为人所重视,但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是以王守仁“心学”为代表的明代哲学思想,学术界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仍停留在清末的水平上。明代经学的实际状况果真如此吗?在对明代经学史料进行详细爬梳的过程中,《明代经学学术编年》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代经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往学者所批评的那种空疏学风,但并非不重视传统的经学典籍,尤其是在以“心学”名世的王守仁身上,以文献为依归的特点体现的更突出。据《明代经学学术编年》,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即在与徐爱论学时提倡“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的为学风气;正德十三年王守仁“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故重刻古本《大学》,虽然王守仁重刻古本《大学》是为了反对朱熹的格物论,不是纯粹的文献整理活动,但其中也反映了他对经学文本的尊重和从文献出发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为学特点。此外,王守仁还对古本《大学》中的核心概念予以重新诠释,如将《大学》中的“在亲民”之“亲”直接训释为“亲”,而非像朱熹那样训释为“新”。通过对王守仁一生经学活动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王守仁倡导的“心学”并非纯粹出于思辨性活动,恰恰相反,王守仁之所以能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其立足于文献考辨并辅之以文字训诂的结果。
除了以上三点,《经学编年》一书还有诸多学术创新之处,如对宋代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对宋代经学中群经与“四书”关系的新见解等,限于篇幅,无法详述。总之,这是一部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取得诸多突破的创新之作。
四、余论
从先秦时期的“萌芽”状态到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从宋代的“义理之学”到清代的“考据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经学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对于中华文化特质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心理的锻造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系统、完整地回顾中国经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经学的学术方法,无疑对于当今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学编年》一书正是适应这一学术需要,在编写体裁、研究方法、学术思想三方面都为经学史的书写与研究确立了范式的杰出作品。
当然,作为一部内容跨度达三千余年、且成于众手的大型著作,《经学编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中国经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学问,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港台地区及海外汉学界对中国经学史也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经学编年》在引述前人观点及开列参考文献时对海外及港台的研究成果关注不足。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是因为存在语言文化、学术交流的障碍,但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关注海外汉学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内在要求,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方法加以批判吸收也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次,作为一部成于众手的大型学术著作,《经学编年》在卷帙多寡上也存在问题,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是《明代经学学术编年》的字数高达118万字,而《清代经学学术编年》仅62万字,显然与明、清两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
瑕不掩瑜,《经学编年》在对三千余年经学发展史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必将为具有创新性的“中国经学史”的撰写提供条件。而其所开创的编年体例、文献意识与学术创新性,也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本期排版:小高
排版受限本文删除原文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