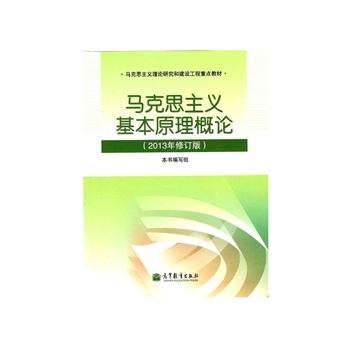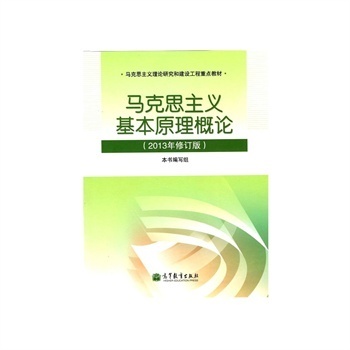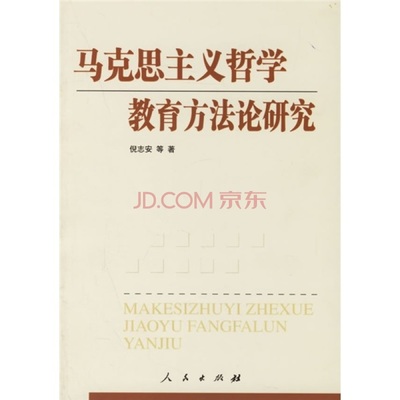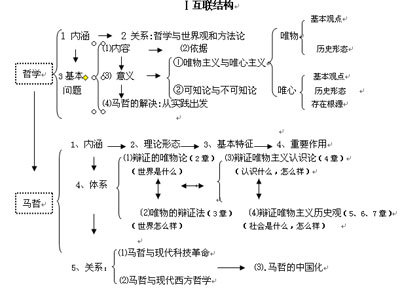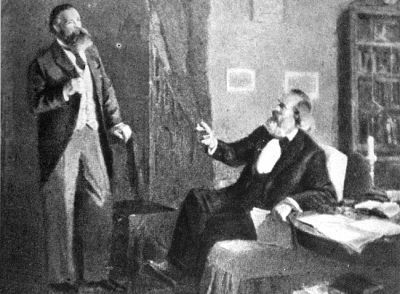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理论原则上是冲突的。
1、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生产力早已突破了民族地区界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工已经变得十分狭窄了,不足以继续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社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必然要依靠国际分工的发展,由民族国家内的分工,发展到各民族、各地区的国际化分工协作。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将这种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驱动下,世界市场被深入地开拓了,全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竞争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在对剩余价值无限追求的驱动下不断地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开拓市场。资产阶级要这样做的详细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论述得很清晰,在此摘录一一段:
“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章)这种强制的竞争规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会是一种民族的、地域的、个别的情况,而必然且已经是一种世界生产方式,并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三,要彻底推翻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就必须要在全世界——或者世界绝大部分角落推翻资本主义,否则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这个问题做出过清楚的回答: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所以,《共产党宣言》才要大声疾呼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团结协作,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另一个经典著作中,同样谈到了“地域性共产主义”的问题: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就连反共大师、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论述,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已给整个世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根据这种唯物史观的逻辑,社会主义不可能是民族的,它只能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他所能设想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全人类和全世界。对他而言,必须对全世界的经济进行统一的管理。(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187-188页)米塞斯接着还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列举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出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要解决这些困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胜利。
2、民族主义光从字面上看,就是和国际主义相对立的。界定一个民族的标准虽然很多,但从来都是一个地域标准(“国族”——例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或者是一种种族—血缘标准,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血统(例如犹太复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等)。民族主义采用的标准是同阶级标准对立的,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是一个地域或一个种族的各阶级的集合体,例如说犹太民族,必然既包括犹太工人,也包括犹太资本家和犹太小业主。
在民族主义下,犹太人是一个共同体,其他民族是另外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教导一名犹太工人,会强调他们同犹太资本家是“留着相同的血,讲着同样的语言”等等,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则会更强调犹太工人和其他各民族工人的相同地位,教导犹太工人对犹太资本家的反抗意识。因此,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
从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上看,它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相伴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解释下,现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正是资产阶级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分散状态,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它们的民族主义是在反侵略中形成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例如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等等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只能依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成为世界霸主的路径实现,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样——消灭民族。以下是长时间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的经典论述段落摘录: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资产阶级是主角。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目标。对于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而言,一个民族处于压迫地位,民族主义者会反对民族压迫,追去民族独立;此后,按照民族主义,民族还要实现自己的强大,不管是用“民族伟大复兴”或者其他什么词句(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变成剥削性的民族才有可能)。总之,民族主义不仅不是要实现一种普世的社会制度,反而是要实现人类中一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同化”它们,把其他“落后愚昧的民族”都变成同族呀!我只能说,这个思想已经离纳粹法西斯主义没多远了。
3、尽管如此,民族主义——主要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上总是有联合的趋势。这似乎和上面说的矛盾,但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原因如下:
无论是哪种民族主义,它是否能够实现,都会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而一个民族,无论以什么标准划分,其大多数成员必然是以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劳动人民。而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马克思时代的德国,还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还没有失去其革命性;在历史上,恰恰是压迫民族-帝国主义,是阻止被压迫民族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而帝国主义在这时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在这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主体、利益诉求、斗争方式、主要敌人,总体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两者可以结合的现实基础。而实际上,很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论述的最为透彻明白: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马克思在当时也主张许多民族主义的目标,例如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废除区域内的关税,建立民族国家等等,肯定(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进步意义:
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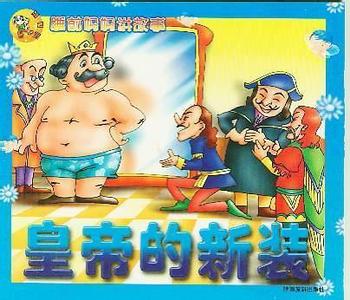
而当民族取得了政治独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并且开始意图成为压迫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裂痕也就随之扩大了。因为这时,民族主义者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其他与其竞争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意图反抗它剥削的民族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会和这种民族主义结合,而是坚决地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就和列宁反对一战各参战国的“爱国主义”那样,并坚决宣传、践行国际主义。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同时,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特别讲到时刻认清楚民族主义的本质,决不能在理论上模糊,甚至给事实上的民族运动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所以,题主还没做出这个关键的选择——到底是成为一个披着红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选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判断当前中国的性质和世界的性质,从而得出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