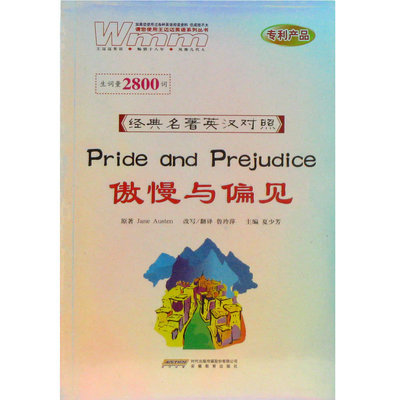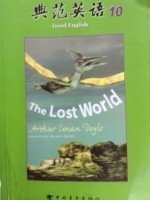《世界名著远大前程》,是(英)狄更斯编著,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远大前程简介_世界名著远大前程 -基本信息:
书名:远大前程(附光盘)

作者: (英)狄更斯著,胡泽刚译
出 版 社:南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1 字数: 427000 版次: 2 页数: 423 印刷时间: 2003-1-1 开本: 32开 印次: 1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7806602054 包装: 精装所属分类:图书>>小说>>世界名著>>欧洲
远大前程简介_世界名著远大前程 -内容简介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故事讲述了一个出身卑微、有着艰苦童年的年轻人匹普的成长经历。匹普从小跟姐姐、姐夫生活。他在郝薇香小姐家遇到了高傲、美貌的艾丝黛拉并爱上了她,但艾丝黛拉却对他傲慢无礼。后来匹普受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资助,到伦敦学做绅士。然而,匹普逐渐看透了这些以社会地位的晋升和财富为标准的浅薄价值观。他发现他的秘密资助人并不是他之前以为的郝薇香小姐,而是他曾经帮过一把的逃犯。同时,他还发现自己深爱着的、以为属于上流社会的艾丝黛拉原来是这名逃犯和一个女仆的女儿。郝薇香小姐是个苦命的女人,她的生活中只有恨,没有爱,从她的经历以及粗鄙无情的朱穆尔身上,匹普看到了隐藏在高级阶层光鲜生活背后人性的缺失。多年的飘荡之后,匹普最终回到了家乡,他从逃犯马格韦契和自己可怜的姐夫乔身上体会到了人真正的内在价值以及什么才是优秀的绅士风范。匹普终于明白:他曾经看不起的逃犯给予他的关怀以及乔对他的无私疼爱才是真正值得他珍惜的。随书赠送“孤星血泪”电影VCD光盘2张。
远大前程简介_世界名著远大前程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英国小说家。由于出身贫寒,从小没有在学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12岁便开始在工厂工作。19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盛行,这为英国大城市带来了繁荣,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阴暗面:童工泛滥,工人阶级的生活极度困苦。狄更斯亲身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公平,他开始通过自学创作小说,同时坚信只有学习才能使他脱离贫困。狄更斯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工人阶级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因而他的作品很受欢迎。狄更斯还通过诙谐的描写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和社会矛盾。狄更斯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等。1870年6月9日,查尔斯・狄更斯去世。他安息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与英国其他伟大的作家葬在一起。尽管人们常批评狄更斯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过于多愁善感,但狄更斯仍与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样备受尊重,究其原因就是狄更斯创造的人物不仅被赋予了人性和幽默,同时还体现出人类真正的乐观和生命力。
远大前程简介_世界名著远大前程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远大前程简介_世界名著远大前程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我父亲姓匹瑞普,我自己的教名叫做菲利普。童年时我那小舌头怎么也无法把这姓和名念清楚,含含糊糊地就念成了简短的匹普。于是我就管自己叫匹普,别人也就渐渐跟着这样叫我了。
我说我父亲姓匹瑞普是有根据的,他的墓碑和我姐姐都可以为此打保票。我姐姐是乔・戈杰瑞太太,她丈夫是铁匠。由于我既没有见过亲生父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肖像(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离拍照这玩意儿还远着呢),我对他们长相的最初印象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墓碑胡乱揣测出来的。父亲墓碑上的字体使我产生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认定他是个皮肤黝黑的矮胖子,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而墓碑上“及夫人乔治安娜”那几个弯七拐八的字体,又使我得出一个孩子气的结论,认为母亲脸上一定长着雀斑,而且还体弱多病。父母的坟墓旁还整整齐齐地排着五块约一英尺半长的菱形小石碑,那就是我五个兄弟的墓碑(在人世间谋求生存的斗争中,他们早早地停止了努力)。见了这些石碑,我从此就坚信,我这五个兄弟来到人间时一定都是仰面朝天、双手插在裤袋里的,而且一辈子也没把他们的手拿出来过。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片沼泽地,附近有一条河,顺河蜿蜒而下到海不过二十英里。我第一次对世间万物之间的来龙去脉产生刻骨铭心的印象是在一个难忘的下午。记得那是临近傍晚的时分,我终于弄明白:那荨麻丛生的凄凉之地原是教堂公墓,本教区的已故居民菲利・匹瑞普及其妻子乔治安娜都已经死了、埋了;他们的婴儿亚历山大、巴瑟罗缪、阿伯拉罕、托比亚斯和罗杰也都死了、埋了。墓地对面那一大片黑压压的荒野之地就是沼泽地,沼泽地上堤坝纵横,土墩、水闸横七竖八,还有疏疏落落的牛群在吃草。沼泽地再过去的那条铅灰色线条就是河流,远处那阵阵狂风呼啸而来的地方就是大海,而被这一切吓得浑身发抖、哭哭啼啼的小东西就是匹普。
“别嚷嚷!”靠近教堂门廊一边的墓地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来,大声喝道,“不许动!你这个小鬼!否则我就掐断你的脖子!”
这个人真可怕!只见他穿着一身灰色粗布衣服,腿上拴着一副大铁镣,头上没有戴帽子,只裹着一块破布,一双鞋子破烂不堪。这个人在水里泡过,被泥浆呛过,两条腿被石头绊得一瘸一拐,身上被碎石片划出一条条伤痕,还被荨麻戳得疼痛难挨,被荆棘扯得皮开肉裂。他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浑身发抖,又是瞪眼又是咆哮。他一把抓住我的下巴,满口的牙齿直打战。
“噢!别掐断我的脖子,先生。”我吓得一个劲儿地求饶,“求您千万别这样,先生!”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道,“快说!”
“我叫匹普,先生!”
“再说一遍。”那人瞪了我一眼,说道,“说清楚些!”
“匹普,匹普,先生。”
“你住在哪儿?”那人说道,“指给我看!”
我指着河边平地上我们住的那个村庄,那里离教堂大约有一英里多路,周围是一大片桤树和秃顶树。
那人看了我一眼,然后便把我头朝地摁在地上,并把我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其实,除了一块面包,我口袋里什么都没有。等到教堂恢复了本来面目――那人手脚快、劲头猛,刚才一下子就把整座教堂在我面前翻了个身,我看到教堂的塔尖跑到了我的脚下――言归正传,等到教堂恢复了本来面目,他便把我抱到一块高高的墓碑上。我坐在上面直打哆嗦,而他却拿起那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吃完面包,舔了舔嘴唇,说道:“你这小混蛋的脸蛋儿长得倒挺胖的啊!”
就我的年龄来说,我当时并不高,体质也不结实,可我脸蛋儿的确长得胖乎乎的。
“我要是吃不了你的脸蛋儿那才怪哩!”那人又晃了一下脑袋,吓唬我说,“我要是不想吃它才怪呢!”
我一面苦苦哀求他千万别吃我的脸蛋,一面紧紧抓住屁股下的那块墓碑――一则怕从上面摔下来,二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
“嘿!”那人说道,“你妈在哪儿?”
“就在那儿,先生!”我说道。
他吃了一惊,拔脚就跑,可跑了没几步又站住了,回过头来看了看。
“就在那儿,先生!”我胆战心惊地向他解释道,“您瞧‘及其妻子乔治安娜’那几个字,那就是我妈。”
“噢!”他这才跑了回来,说道,“这么说你爸爸也跟你妈妈葬在一块儿罗?”
“是的,先生。”我说道,“他也葬在那儿,‘本教区的已故居民’。”
“哈!”他哼了一声,想了想后又说道,“那么你跟谁在一起过呢?我是说,假如我发善心饶你一命,你跟谁在一起生活呢?不过,我还没有打定主意是不是要饶你这条小命。”
“跟我姐姐乔・戈杰瑞太太一起生活,先生。她就是铁匠乔・戈杰瑞的太太,先生。”
“哦?铁匠?”说着他就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腿。
他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腿,一会儿又看看我,沉着脸来回看了几遍,然后走到我坐的墓碑前,抓住我的两个肩膀,把我的身子尽量向后按下去,一双眼睛凶巴巴地盯住了我的双眼,而我的双眼却只有无可奈何地仰视着他的份儿。
“你听着!”他说道,“目前的问题是,要不要让你活命。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锉刀吗?”
“知道,先生。”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吃的?”
“知道,先生。”
他问一句,就把我的身子再往后按一下,好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走投无路、危在旦夕。
“去替我弄把锉刀来。”他又把我往后按了一下,“再替我弄点儿吃的来。”他又把我往后一按,“你把这两样东西都给我拿来。”他再次把我往后一按,“否则,我就要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吃。”他又一次把我往后一按。
我被吓坏了,顿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双手不由得紧紧抓住了他。我说:“先生,请您行行好,让我直起身子来,免得恶心呕吐,而且我还可以听得更清楚些。”
这时,他猛地一松手,让我一个倒栽葱滚下地来,我直觉得整个教堂一跃而起,跳得比屋顶上的风信鸡还要高。过了一会儿,他抓住我的两条胳膊,把我放在墓碑上重新坐好,继续说些吓人的话:
“明天一大早,你就给我把锉刀和吃的送来,送到那边古炮台前交给我。要是你能办到,而且不走漏一点儿风声,也不露出半点儿形迹,不让人知道你看到过我这么个人或看到过任何人,我就饶你一命。要是你办不到,或者不依我的话去做,哪怕走漏了一丁点儿风声,当心我挖出你的心肝来烤熟了吃。你不要以为我是光杆一个人,我还有个小伙子躲在身边哩。跟他相比,我简直慈悲得像天使。我在这儿和你说的话,那小伙子听得清清楚楚。他还有一套独特的法术,专会捉小孩子,挖小孩子的心啦,挖小孩子的肝啦。哪个小孩子也休想躲得过那个小伙子。哪怕你锁好房门,暖暖和和地睡在床上,钻进被子里,用被子蒙住头,自以为安安稳稳,可那个小伙子也会悄悄地爬到你床上,扒开你的胸膛。这会儿我费了好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拦住了他,不让他来伤害你。不让他碰你的心肝还真不容易呢。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我一定会替他弄把锉刀来,而且只要能找到什么残羹剩饭,好歹都给他带来,而且明天一大早一定去炮台那里见他。
“你得起誓:如果做不到,天打雷劈!”那人说道。
我照着他的话起了誓,他这才把我抱下来。
“你听着,”他接下去又说,“别忘了你答应做的事,也别忘了那个小伙子。你回家去吧!”
“晚……晚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得了吧!”他边说边扫了一眼周围那寒冷、潮湿的沼泽地,“我真恨不得能变个青蛙。要不然,变条泥鳅也好!”
说到这里,他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搂着瑟瑟发抖的身子(仿佛他怕身子会散架似的),一瘸一拐地向低矮的教堂围墙走去。看他在那一大片荨麻丛生、荆蔓萦绕的坟墩里躲躲闪闪地拣着道儿走,我那幼稚的心灵还以为他是在躲避那些死人从坟墓里悄悄伸出来的手,怕他们揪住他的脚踝,把他拖进去呢。
他走到低矮的教堂围墙前,翻了过去,然后又转过脸来看了看我。看他翻墙的姿势,你会觉得他的两条腿已经冻僵、冻麻木了似的。我一等他再次转过脸去,就急忙撒开两条腿飞快地往家里跑去。过了一会儿,我回头一看,只见那人正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在那一块块大石头之间拣着道儿向河边走去,他的两条胳膊仍然紧紧地抱着身子。那些大石头搁在沼泽地上是准备下大雨或是发大水的时候当垫脚石用的。
我停下来目送着他的背影。这时的沼泽地已只是一条长长的、黑黑的地平线,那条河流也成了另一条地平线,只是不及第一条宽,也不及第一条黑,而天空似乎成了一大条用血红色长条和浓黑色长条交织起来的带子。我隐隐约约只能看到河边有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直直地矗立在那儿:其中一个是为水手们指点航向的灯塔――这玩意儿近看时就像个散了箍的桶被撑在木杆上,难看极了;另外一个就是绞刑架,上面还悬着几根铁链,曾用来拴过一个海盗。只见那人正一瘸一拐地朝着绞刑架走去,那情形仿佛是那个海盗复活了,刚刚下了绞刑架,现在又回去重新吊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害怕起来,再看到地里的牛也都仰起头来盯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得怀疑这些牲口的想法是否也和我的一样。我四下搜寻那个可怕的小伙子,可是连个影子也没看到。这一下我又害怕了,赶紧一刻不停地往家跑去。
第二章
我的姐姐,也就是乔・戈杰瑞太太,要比我大二十多岁。她喜欢标榜自己,左右邻居们也对她赞不绝口,因为我是由她“一手”带大的。我那时候弄不懂这“一手”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她那只手生来又粗又笨,老喜欢“啪”的一下落到她丈夫和我的身上,于是我便以为乔・戈杰瑞和我大概都是她“一手”打大的。
我姐姐长得并不好看,我总觉得乔・戈杰瑞之所以娶她,一定也是她“一手”造成的。乔倒是个皮肤白皙的男子,光滑的脸蛋两旁留着淡黄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珠淡得似乎和眼白快要融成一体,难以分辨。他脾气柔顺、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待人随和,带有几分傻气,是个可爱的家伙。他是那种力气很大,可很怕老婆的人。
至于我的姐姐乔太太,头发和眼睛都生得乌黑,皮肤却特别红,我有时禁不住怀疑,也许她洗澡擦的并不是肥皂,而是肉豆蔻。她个头很高,骨骼宽大,一条粗布围裙几乎成天不离身,挽两个活结系在背后。胸口围着一块十分坚实的胸兜,上面别满了大大小小的针。她就这样成天围裙不离身,一则显示自己治家的功绩,二则当做责骂乔的资本。不过我倒是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系围裙,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一旦系上后成天不解下来。
乔的打铁间就在我们家的隔壁。我们家住的是一所木头房子,那时我们村里的住宅十之八九都是木头房子。那天当我从教堂公墓赶到家的时候,打铁间已经打烊了,乔正独自一人坐在厨房里。乔和我是一对同样挨苦受气的难兄难弟,彼此推心置腹。我拨开门闩探头朝里面一看,只见他正坐在门对面的壁炉边。他一看见我,便赶紧悄悄告诉我:
“匹普,乔太太出去找你找了十多次啦。刚才她又出去了,二十次也有啦。”
“是吗?”
“是的,匹普。”乔说道:“更糟糕的是,她还随身带了那根抓痒棍呢。”
一听到这令人沮丧的消息,急得我一个劲地扭着背心上仅剩的那一颗纽扣,垂头丧气地瞧着炉火。所谓“抓痒棍”,其实是一根缠着蜡线的棍子,在我身上横抓竖搔,早就给磨得十分光滑了。
乔说:“她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于是就拿起抓痒棍,暴跳如雷,冲了出去。我一点也没有夸张。”乔边说边慢悠悠地拿起拨火棍,捅了捅底部炉格中的火灰,眼睛看着炉火,又补上一句:“她的确是暴跳如雷地冲了出去,匹普。”
“乔,她出去很久了吗?”我一向把乔也看做一个孩子,在家中的地位和我一样。只是年纪比我大些而已。
“嗯,”乔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道:“匹普,她最后一次暴跳如雷似的冲出去,大概有五分钟了。她回来了!伙计,快躲到门后面去,用大毛巾遮一遮。”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我姐姐,也就是乔太太,猛的一下将门推开,发觉有个什么东西挡在门后,立刻怀疑其中有名堂,便拿起抓痒棍进一步探查起来。一看是我,她便一把将我拎起来扔到乔跟前。他们夫妇俩经常把我当飞镖,一个扔一个接――乔总是乐意把我接住。他现在就接住我,将我放到了炉子前,并悄悄地用他那条大腿护着我。
“你这个小畜生到哪里去了?”乔太太跺着脚骂道:“老实告诉我你干什么去了?惹我生气,惹我着急,让我惦记,把我累得精疲力竭。快告诉我,否则我就要把你从角落里揪出来,管你是五十个匹普,还是他是五百个戈杰瑞,也休想招架得住!”
“我只不过到教堂墓地去了一下。”我坐在矮凳上边哭边蹭着身子。
“教堂墓地!”我姐姐说道,“要不是我,你早就进了坟墓,一辈子就待在那里啦。你知道是谁把你一手带大的吗?”
“是你。”我说道。
“我倒要问问你,我干吗要把你拉扯大呢?”姐姐咆哮道。
我抽抽噎噎地说:“不知道。”
姐姐说道:“不知道?我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你不知道我可知道!老实说,自从你生下来后,我这条围裙就没有离过身。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嫁给了一个铁匠,一个戈杰瑞这样的铁匠,偏偏还要给你当妈!”
我闷闷不乐地看着炉火,根本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因为我一心只想着沼泽地上那个戴着脚镣的逃犯,那个神出鬼没的小伙子,锉刀、食物以及自己立下的可怕的誓言――我得从我这个栖身之处为逃犯偷锉刀,偷吃的。炉子里的炭火似乎存心和我过不去,竟然把这一切统统映现在我的眼前。
乔太太“哼哼”冷笑了一声,把抓痒棍放回原处,说道:“教堂墓地!你们俩说墓地倒是说到了点子上!”其实,我们俩当中有一个根本没提到过墓地。“你们俩总有一个要不了多久就会把我逼进坟墓的,唉,那时候,没有了我,看你们这对活……活宝怎么办!”
趁她去张罗茶具的当口,乔偷偷瞥了一眼躲在他大腿后的我,仿佛心里在暗自思忖,万一这种不祥的预言成了事实,我们俩究竟会成为怎样的一对活宝。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摸着自己右边亚麻色的鬓发和胡须,蓝色的眼睛盯着乔太太的一举一动。他不顺心的时候总是这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