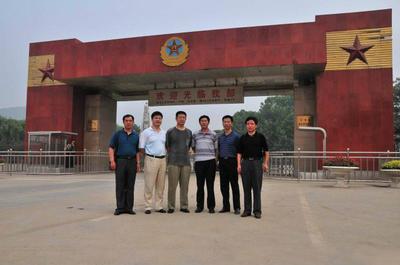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年,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1952年,中国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是美国以中国的赔款在中国创办的教会高等学校。校址在北京海淀。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历史沿革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以中国的赔款在中国创办的教会高等学校。校址在北京海淀。
1919年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次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并入。成立初期未分学系,仅设本科和预科。
1929年,设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音乐、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家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系。
1934年设研究院,下分文、理、法3个研究所。美国人J.L.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迁校成都。
1946年迁回北平(今北京)。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燕京之父
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由他起步
传教士草创名校,司徒雷登迎难受命担任第一任校长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司徒雷登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2)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3)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学校筹建
燕京大学 校园
晚清,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后来他们终于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到司徒雷登头上。
1919年1月司徒雷登来到北京,但围绕校名的争吵延续了好几个月,最后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并结合该校特点设立女部。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清淑春园的所在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设计师亨利・墨菲总体规划,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司徒雷登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校园环境
燕京大学由于建校资金来自不同的赞助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1926年6月5日燕大迁入新址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因病去世,而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于是司徒雷登将这临湖轩时常作为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的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了匾额。园内最重要的景点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大家争执不休,还是钱穆有主意,索性称其为"未名湖"。 校园最初的基址是清朝三山五园的附属园林,包括漱春园、弘雅园(墨尔根园)(漱春园和弘雅园为明朝勺园的一部分),1921年自军阀陈树藩手中买入。后又陆续从载沣等人手中购入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1949年后,原由徐世昌家族租用的镜春园、鸣鹤园并入燕京大学园区)。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正门位于校园西边,坐东西向东,以玉泉山玉峰塔为对景,门内为东西轴线。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安佑宫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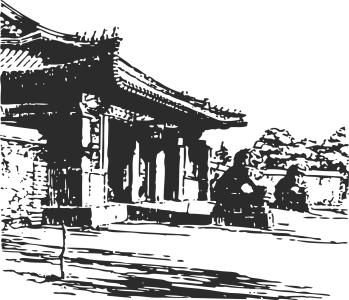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办学思想
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却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中国教员的比例由建校初期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刘廷芳、洪业、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冰心、冯友兰、陆志韦等等。为了使燕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司徒雷登还让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29年燕大在中国注册,自此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所以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是“教务长”。 司徒雷登的这些“改革”,不断受到教会的质疑。但他觉得信仰问题不是靠强迫能解决的,他试图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类似组织课外活动的团体)活动吸引更多的人。的确有许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开始信奉基督教,但是团契的另一个作用是,发展到后来居然大多变成了进步学生的组织。如最有名的"生活创造社",就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了。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司徒雷登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遭残酷镇压,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历经战火
坚守沦陷区
1947年 的燕京大学 校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已改任教务长的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国出差,突然接到学校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并纷纷参加请愿。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对立严重。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教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缓缓说道:"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学生都去了,我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由于燕大没有与北大、清华等一起南迁,司徒雷登曾经受到许多燕大师生的指责。但事后证明,燕大留在北平,不仅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许多学生毕业后正是通过燕大的 "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冰心后来回忆道,她和吴文藻曾经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车将两个要去大后方的学生在夜里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封闭了学校,数十名师生被捕。12月9日,正在天津的司徒雷登也遭逮捕,被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这年10月,燕大复校,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三年多后,终于再次敲响。
为抗战输送人才
燕京大学燕大教授夏仁德是美国费城人,1923年8月来中国,任教于燕大心理学系,在燕大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多年来,他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从1940年起,根据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领衔主持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则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主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逃奔大后方的燕京学子所在多有,逃奔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也不少见。侯仁之回忆,当他策划第一批学生南下时,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向他建议,也应该送一批学生去根据地。并说根据地就在山西,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侯仁之表示赞同,两人就一起去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无保留地支持,并要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和侯仁之共同负责此事。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京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挑选了3批共10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筹措抗战物资
林迈可向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的学员们解答问题
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对抗战中国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战争物资的输送。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林迈可刚从牛津毕业一年,他与白求恩同船赴华,奉派前往燕大,帮助实施牛津试行的新式教学制度――导师制,到燕大后,林迈可住进临湖轩司徒雷登寓所。他选收了8名导师制学生,其中惟一的女生李效黎,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来华途中,林迈可与白求恩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重逢。林迈可很快兑现了这个诺言,于1938年夏首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欢聚。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根据地战争物资的短缺。于是频繁往返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设法为根据地代购战争物资。
这年秋季开学后,林迈可花费很多业余时间,为根据地装配无线电收音机。有一次还拿出一沓进口化学药品的订单,请不知情的李效黎译成中文。这沓订单数量极大,让李效黎好生奇怪。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匆忙撤出平津,决定把来不及搬运的整整6个皮箱的军用器材赠给平津附近的八路军,但一直无法运出。这个任务也落到林迈可夫妇头上。
他们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到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上。
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2日,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过6天。当晚,林迈可在燕园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应变措施。他预计日美战争已不可避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敌后根据地交情颇厚的林迈可主持会议,说服外籍教师撤往敌后根据地。但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后林迈可向司徒雷登汇报,司徒雷登总结了燕大毕业生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15人前往。他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敌后根据地急需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敌后根据地。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林迈可到延安后,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设计制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用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英语,不断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战场的捷报。
刺刀下演说
陆志韦
燕京大学有两个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个是夏仁德,另一个就是陆志韦。
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头一次到陆志韦家做客,两人一见如故。次年,陆志韦即举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
陆志韦只答应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4年。直到“七七事变”,燕大出于生存需要升起了星条旗,司徒雷登亲自出任校长,陆志韦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属于决策层,燕大无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贝公楼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只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控制着我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这股势力一日不消灭,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
台下依旧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顿,他又说:“看到最近在校内发表的冯先生的遗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新诗爱好者,我和他原应结识为朋友。不幸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使我今生再也无缘和他相识,谈论新诗了。”
说到这里,他喉头哽塞,热泪长流。人群中的饮泣,随之爆发成一片嚎啕大哭! 在场的日本军方代表殊为不快,拂袖而去。
燕园日不落
反抗是坚忍的,报复也是凶残的。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宪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之后,师生们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当天下午,日本宪兵两人一组,各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备好的黑名单,逐楼逐室地照单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学生。
亲历者陈嘉祥回忆当时场景:忽然外面一阵皮靴声近,到门口停下。门猛地被推开,一前一后,闯进两个鬼子。前面的凶狠地扫我们一眼,看着手里名单,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陈嘉祥有?”我说:“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挥:“走!”后面的鬼子立刻把枪口对着我的脊背(陈嘉祥:《一二八蒙难记》,见燕京大学校友纪念特刊《燕园友谊》)。
同时被捕的,还有蓝铁年、沈聿温、李慰祖、程述尧、李欧、姚克荫、刘子健、张树柏、朱良漪、孙以亮等10名燕大学生,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刘豁轩、赵承信、林嘉通等7名燕大教授。数日后,燕大教授洪业、邓之诚,总务长蔡一谔、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农科教师沈寿铨,以及周学章、萧正谊全部被捕。来不及撤离的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燕大外籍教师,则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
总共30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敌后根据地的寥寥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
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学被迫暂告中止。燕园被改成日军的伤兵疗养院。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已于前一天应天津校友会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关在一起。
这是燕京大学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学的骄傲――因为,锒铛入狱的30多个燕京师生,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大学校训
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和几位老师,在建校后不久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于是将《圣经》中的两句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与“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结合在一起,燕京大学的校训诞生了。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走向世界
次世界级联姻: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与哈佛的合作,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7)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在他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燕京大学_燕京大学 -文化传承
当年的燕京大门如今换成了北大的招牌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入燕大的校址,两校实行合并。燕京大学就此终结,学校被分拆,文、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国内外普遍认为同时迁入燕园(燕京大学校址)的北京大学才是燕京大学传承的正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