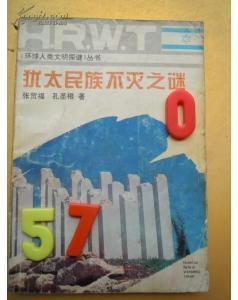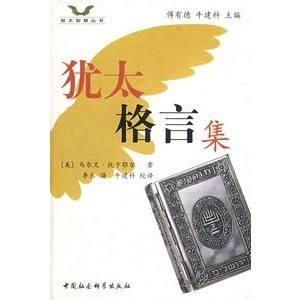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希伯来语:???????/Tsiyonut,阿拉伯语:??????????/al-Sahyūnī,英语:Zionism),也称“犹太圣会主义”,中国大陆官方习惯(择其用意)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在犹太复国运动发展初期,锡安主义是世俗化的,也是一定程度上对19世纪时在欧洲的以天主教徒为首的社会中十分猖獗的反犹主义的一种回应。从1世纪开始,犹太人遭受来自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原因是犹太人被认为对耶稣受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居住在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犹太人则得以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在经过一连串的进展和挫折,以及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摧毁了欧洲的犹太族群后,锡安主义的民粹运动于1948年(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前后)达到了高潮。
犹太复国主义_犹太复国主义 -基本概况
历史原起因
犹太复国主义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这种运动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曾存在着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两个犹太人国家,分别于公元前8世纪和前6世纪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流落到世界各地。
以色列建国
犹太复国主义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例如宗教锡安主义、修正锡安主义和劳工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虽然旧约的历史远超过现代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这名词亦会用作形容有千年历史的旧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本条目是用以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目标作出描述,而非对以色列历史或以巴冲突的析述。如想了解种种反对锡安主义的运动,可参见反犹主义。
回归故里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曾存在着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两个犹太人国家,分别于公元前8世纪和前6世纪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流落到世界各地。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L.平斯克尔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同时,在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T.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他领导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会上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贝尔福宣言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建立
犹太人返回祖辈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为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自从古代的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及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犹太人就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虽然在HellenisticAge许多犹太人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如同MosesHess在他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是犹太裔奥地利人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个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他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ZO),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锡安主义"这个字根源于"锡安"(Hebrew:????,Tziyyon),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这是奥地利犹太出版商NathanBirnbaum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对犹太民族主义所创的词。
主张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是非宗教性质的,开始是作为对19世纪末叶在欧洲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回击。它是犹太人对在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反击。
以色列
1947年英国宣布了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然后在同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了内战。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了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了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了以色列国防军。在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了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了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回归法令,给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导致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而且这个变化看起来是永久的。
196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采用了以下的准则:
犹太人的团结与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犹太人从所有国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区,
在“预言的正义与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国的富强,
通过犹太、希伯莱与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和强化犹太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而保存犹太人的身份,和在所有地区对犹太人权的保护。
巴勒斯坦
1918年奥图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制,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说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国际间犹太人对锡安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_犹太复国主义 -美国

基督教基础
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L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1967年7月)、50%∶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年9月22―2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乃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而美国主流社会竟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美国行政当局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精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现在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锡安主义组织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犹太复国主义_犹太复国主义 -反锡安主义
美国反锡安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反锡安主义(一译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个敏感词。如果名人与这个词连在一起,铁定是个大新闻。
梅吉森7月28日因醉酒开车,被警察截停检查,不知怎的扯上战争和犹太人,梅吉森口无遮拦,说什么战争都是犹太人开始的,他说犹太人应为战争负责。梅吉森随后向犹太人社区道歉,表示那是酒后乱性所致,当不得真。
一般而言,酒后驾车要认真对待,酒后失言则不必当真,不过要是这两件事都出在名人梅吉森身上,结果就不太一样。梅吉森酒醉驾车,被警察拦下检查,演成报纸头版新闻,一时间梅吉森被视为反锡安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然接下来的媒体中所出现的新闻,就是名人们就梅吉森的酒后醉话如何选边站的报道,新闻记者不断追著娱乐界名人们要他们表态。例如8月7日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一组表示理解梅吉森的娱乐界名人,认为他并非是反锡安主义者,只是有酗酒的坏习惯,应该原谅他,支持他,另一组娱乐界名人,则认为吉森可耻,更绝的是,他们中有的发誓绝不再与他合作,有的发誓再也不看他的电影。有趣的是,还有人是列在未决定之下,大概还在权衡该如何表态吧。
吉森
吉森是娱乐界名人,闹得娱乐界纷纷表态也合情合理,但由于他曾拍过电影基督受难记,并受到美国福音教会的一致推崇,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议题让教会如此团结一致。因此媒体也不放过教会的名人,一个个名牧师,也要发表个人看法。福音派教会对待吉森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用一句话概括,“福音派痛恨吉森的罪,但拥抱他的受难记”。酒醉驾车和口无遮拦,当然不可能得到教会牧师认同,但如果说吉森有反锡安主义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可能体现在他的电影作品中,那么就涉及到对基督受难记的评价了。而这当中就涉及到了教会的立场。因此大多数被媒体访问到的牧师,都十分小心,避免否定基督受难记。
基督受难记还未上映时,就受到犹太社区的责疑,认为是一部宣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电影。因为电影渲染了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细节,并借用圣经中的话,让犹太人表白,“让流耶稣的血归到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后代”。这让犹太社区感到会掀起反犹太主义思想来。
电影的影响
基督受难记最后上映时,把这句话删除,并在电影结束时,以字幕方式陈述,有多少犹太人在二战中死去。电影上映后的事实证明,基督受难记并未引发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爱家协会主席道生牧师的态度是:吉森的言行是伤害性的和不幸的,但与基督受难记毫无关联,基督受难记是本世纪最好的电影。超大型教会新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全美福音联合会的主席特.赫格德认为此事值得关注,但还看不出有重新评价基督受难记的必要,他此举基本上划定了福音派教会的立场底线:即不赞成吉森的言行,但那是个偶发的不幸事件,与他的作品无涉。这是比较公事公办的态度。
不过还是有不少牧师更体现出宽容和慈爱,他们会为吉森辩护两句。同样也是全美十大教会之一,会友有两万人的社区教会的一位同工就指出,人喝醉了酒就会说些违背他本意的话,当不得真,再说他不在现场,又没听见梅吉森说话,因此无法去论断。
犹太复国主义_犹太复国主义 -发展历史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L.平斯克尔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同时,在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T.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他领导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会上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民族,不应与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途径不是消除产生反犹太主义的阶级根源,而是与非犹太人分离,单独建立一个国家。只要取得宗主国与其他大国的支持和有钱的犹太人的资助,不断向一确定]地区移民,即可实现这一目标,而无须征得殖民地区居民(巴勒斯坦人)的同意。
然而事实上,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是犹太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过,可是这不是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因为当一个民族拥有一块土地超过50年,他就拥有了这块土地,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千年,犹太人的主体已经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已经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了。
十九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此时该地区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人向该地区移民加速,此时主要是来自东欧,尤其是苏联的移民。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所以说,阿拉伯人有权利反对该决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明显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绝建国。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犹太复国主义_犹太复国主义 -评价
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在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建国后又屡次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就像当年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而且越演越烈,终于酿成了民族矛盾。而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两个民族都视同一个城市为宗教圣地,从而冲突就有了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决也变得更加困难。犹太人的建国和驱逐可以看作为几千年来怨恨的释放,虽然可以理解,但犹太人表现出来的过分强硬和蛮横却为本来可以更好解决的问题留下了祸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