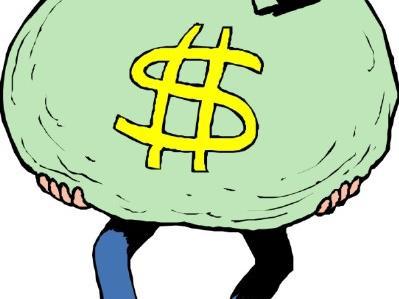关于学术论文的问题我不想赘言(我自己写论文也同样十分头疼),我只想从一个半吊子写作者的角度,谈一谈一般意义上的写作的问题。
“中国学生写作几乎是天赋技能”,说实话,当看到这句话时,我几乎有点生气——原因是,我所重视的,也是唯一还算擅长的事情:写作,竟然受到了如此的轻视。在我的理解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写作这种事情,还需要学习么?”
对于每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我建议各位去读一读王小波的《我的师承》。在文章的开头,他用戏谑的口吻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
现在,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初中生都轻车熟路的随笔小说”,究竟是好的文字呢,还是“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
不能创造出称得上好的作品,这样的能力究竟配不配被称为“天赋”?
在很多人看来,写作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只要你不是文盲,又能够握笔或者打字,人人都可以轻松地写作,随手几下就是一篇锦绣文章——这简直要让各位文坛大家们羞愧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或是剪掉了自己所有外出的衣服紧闭房门两个月、或是每天喝掉八杯咖啡、或是因为自己的听众睡着而烧掉已经完成的稿件,这样呕心沥血了一辈子的事业,一群数量庞大的“有天赋”的“中国学生”轻描淡写地就完成了。

恕我直言,这样的写作,不过是毛姆口中的“形式的戏剧”:“只是出于年轻时的精力旺盛,并不比儿童在沙子上建造城堡更有意义。”
毛姆将其总结为“年轻人的本能”,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将其错误地定义为“天赋”——并且有些人很有可能在沙子上建造城堡都做不到,只能建造出奇形怪状的不明物体,或者干脆是一个沙堆,他们依然将其称之为“天赋”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分不清好坏。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简直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我想说的是,让我感到有些生气的,不是这个观点明显的错误,而是背后的态度——或许换个例子更加容易理解:“你们学计算机的,不就是会修电脑吗?”
我们费尽心力的东西,被以一种近乎轻蔑的方式进行解读,这才是我不舒服的原因。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半吊子写作者,我的目标仅仅是能讲好一个故事,但我的每一篇稿件都是尽心尽力的。在不知道从何下笔时烦躁地走来走去,花了半天写好的内容又全部推翻重写,找到好的切入点之后几乎笑出声来,这些我都经历过。
写到今天,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匮乏和无知,越清楚自己的东西和真正的“好文字”差了不知道多远,下笔的时候也越来越慎重:要选取什么样的角度?传达什么样的情绪?哪里应该着重下笔?这样写究竟会不会好看?能不能呈现我希望表达的东西?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经常会感觉到无力:在这条路上,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而真正的高手们,我可能殚精竭力也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这种想法似乎非常不合时宜。在一个“人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的时代,每个人都喊哑了嗓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有可能带来注视、名声、利益,数不胜数的好处,我们关心的是声音都够被多少人听到,至于究竟说了什么内容,则被越来越少的人关心——毕竟,它很快就会被淹没在喧嚣的海洋里。
对此我不置可否。时代的趋势本就无法逆转,这样的做法也不该被评判是非。我承认我也写过很多垃圾文字,甚至写过的每一篇都是失败的范例,但我希望的是,作为写作者能够拥有自知,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在狂欢中愈发膨胀,在五彩斑斓中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我从来不认同写作的种种光芒万丈的崇高意义,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眼高手低。但即便仅仅是引人一笑的文字,我也努力地希望它能够好看一点,更精彩一点,至少让人在回味的时候还能笑一下,而不是想到一堆毫无意义的垃圾。
能够做到优秀的人少之又少,但至少不要把生产“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的能力,称之为“天赋”。
最后,放上一个我很喜欢的寓言故事,改编自《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看到一棵歪脖子的病树。他心中可怜,便把歪脖子树移栽到一个瓦盆里好生照料。
一日,病树对郭橐驼说:“恩人好心救我,我心中十分感激,但是这种在这破瓦盆里是在没面子,劳烦恩人给我换个好看些的花盆,也算光彩些。”
郭橐驼听后,默默把歪脖子树移到彩绘花盆里。
几月后,病树又说:“我久居屋檐下无人注意,这花盆现在又有些嫌小了,容不下我伸展手脚,把我移到院子里去吧,这样,路过的行人也能看到我!”
郭橐驼并不多话,又将歪脖子树移到院子里。
又过几月,病树不耐烦地嚷嚷道:“这院落破败不堪,我怎能待在这样的地方!你这老头,还不快把我移到泰山顶上去,让千万人都在我脚下仰望我!”
郭橐驼听罢,将树连根拔起,跋涉数天来到泰山之巅。远处,众山俯首,云海苍茫。
此时,郭橐驼才微微一笑,对病树说道:
“天地越大,你越渺小。”
天地越大,你越渺小。
送给每一个人,也送给我自己。
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