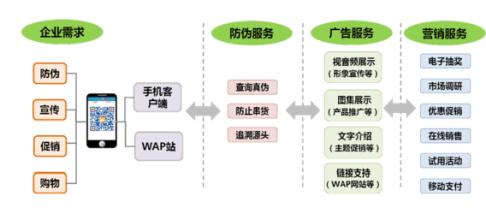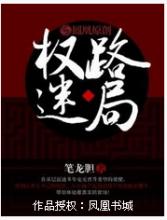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风窗》: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 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南风窗》: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 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一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南风窗》: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 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评说“上海帮” 《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回看向来萧瑟处 《南风窗》: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自由。退出来了,倒了霉了,我也并不感觉自己见不得人。就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摸摸良心,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我当常委、委员,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没有跑过官,上面定的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为毛泽东做事,觉得很光荣。因为当时很多相当重要的事情,都是从毛泽东那里下来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没关系。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在我老师一辈里,也是这样的,尽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愿意不舒服不开心,但到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比如周予同临终以前的陈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得失在一整个大的运动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则的话,你反而给人家小看了。 《南风窗》: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无可奈何?写作组是实践你们的抱负的平台吗? 朱永嘉:写作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做一点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现实终归是现实,你要在学问上能够有所创见、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人家高兴听你,不高兴由人,是别人说了算。你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成,环境起很大的作用,怎么做,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行人事听天命,你不过就是行人事罢了。 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一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知识分子的光彩不在权力上面,要是硬往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结果的人不会很多。这片土壤上,他们没有办法生长。权力结构上卑鄙龌龊的事情太多了,你没办法在这块土壤上很好地生长,要么你就随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你要想拼命往里面挤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里面挤,还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余地,有的问题可以退出一点。 《南风窗》:经过那段历史之后,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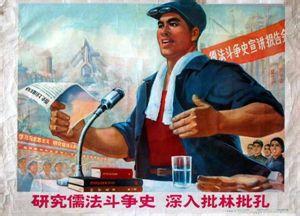
朱永嘉:过去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依附于皮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除了为权力机构服务以外,独立谋生的道路并不多。在过去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做官,参与政治。孔子那时候讲儒家思想,是从官僚场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点。总体上来讲,他是离不开这张皮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