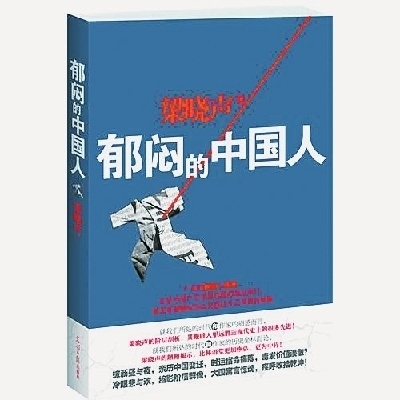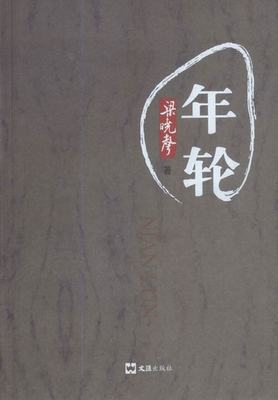曾经被称为“理想斗士”的梁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以《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描绘一代知青的青春年华。如果要为他设定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理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商业社会的猝然来临,梁晓声也开始了从理想主义向人文主义的悄然转变
梁晓声的新小说《伊人,伊人》放在案头,40余万字的长度,四分之一世纪的重量,书写的却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主题:爱情。
“人们习惯于在我的小说中看到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看到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命运。而我,特别希望写出一部与以往打上‘梁记’风格的小说不一样的作品,”梁晓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因此,梁晓声刻意剪除了宏伟的背景,整部小说似乎也无关理想,简单的情节、简单的人物关系,一切像暴风雨过后归于平静。是平淡的,也是唯美的。“我写了一个关于大爱的故事。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爱与被爱。”梁晓声说。
小说主人公乔乔和乔祺的生活,也是梁晓声自己渴望的生活——无数次,他在公开场合坦言,江南小镇的生活将让他倍感亲切,“两三排砖房,门前养鸭养鸡,有洗澡的热水,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年龄能够倒退十几年,他会像乔祺一样,在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秦岑和乔乔中,选择与乔乔在乡间生活:“乔乔所需极少,她对于幸福的概念很简单。一个男人和乔乔生活在一起,他会变得简单,变得快乐。”
他仍居住在北京简陋的房子里,不用电脑,亦没有手机,保持过最简单的生活,唯有写作让他安心:“我习惯了,伏案心就会定下来。”
只是,小说的最后,他宣布了乔乔的死亡,如同物质生活的盘剥有时让他这个所求极少的人也感到无所适从:“我必须宣布乔乔的幻灭。即使他们依然相互支撑,当他们过江到对面城市的时候,钱可能就不够花了。他们居住的坡底村,可能慢慢地也会变成江那边的世界。”
于是他叹息:“小说中还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其实我知道自己太理想化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真正幸福。”他也了解,他所渴望的江南小镇生活是地主生活,并非真正的农民生活:“当你遭遇到真正残酷人生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还能说什么呢?”他很无奈。有很多事情,并非靠一根笔杆子所能改变。但他,仍然执著于用写作来寻找社会公正。或许,20余年的理想并未褪色,改变的只是形式。他在一个文学已经降到最小值的时代里,找寻一个“最俗常化、最泛滥”的情爱题材,以一种“最不可能、最冒险”的方式,来追问当代:理想的分量,究竟还有多重?理想主义包含献身的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北大荒度过了将近7年的时间,并在那里开始你的小说创作。那一时期,有什么事情对你的写作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吗?
梁晓声:我是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1968年到北大荒。北大荒和很多地方不一样,那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开始写作。
但我早期的作品,受现实生活的影响不大,在精神上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更多。如俄罗斯文学中,有作品描绘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爱情追随着他们,这种带有一点悲壮色彩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此外,共青团的理想也对我的写作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1984年是“梁晓声年”,认为你在那个时候扛起了理想主义的大旗,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我想,同为青年,当年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非常不一样。如果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把今天的独生子女放到那个环境中去,苦闷、挫折、玩世不恭,这一切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呈现出来。然而,那个时代的青年呈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我”两个字,如果一个人流露出较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不是成为另类,就是成为受批判的对象。因此大家的群体意识和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非常明确。大家的基本共识是:“我是集体中一员,我必须忠实于集体。”因此抗艰苦的能力特别强。我们的理想恐怕是这点。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理想,但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含有随时准备奉献的精神在内的。为了别人、为了集体,随时准备牺牲自我,富有牺牲精神的这样一种主义才叫理想主义,否则和我们今天对于房子、车子、票子的追求有什么不同?

理想主义让我遍体鳞伤
《第一财经日报》:1993年、1994年前后,你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感慨“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比较失落的时期?
梁晓声:1993年的时候,我已经会看,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说失落也对,我预感到时代的变化。1993年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恨不得从商、下海、挣钱,那是一个极其浮躁的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坚信,我们就是这个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是与以后的新人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商业时代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就使我们变得和下几代一样。
《伊人,伊人》中,我借用乔祺的口问当代人,问当代已经超越贫穷的人: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贫困地区的百姓,当他们挣到一点钱,过年拿回家的时候,他们很快乐。但在城市里,很多人的快乐指数不高,他们在不断折腾自己。已经不穷的人想变成富有的人,因而变得焦躁不安。这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很多普通人的脸上都焕发着快意。
《第一财经日报》:你渴望过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但有没有想过,当商业狂潮一步步紧逼的时候,连简单生活的权利也会被剥夺?
梁晓声: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严格说来,这样生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电视、资讯、报纸、广告,你的平房后边可能就是豪宅,这些东西都在你身边,它咄咄逼人。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的理想主义,让你们遍体鳞伤。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梁晓声:有的。我想,我要在商业时代里站稳脚跟不被冲动,我的脚下就必须有一块稳定的基石。对我来说,这块基石就是我从20多岁开始从事的写作。以前我们把写作的意义尽量放大,放得越大,我们感觉越有重量,感觉自己站得越稳,因此就别无旁顾。因为你抓住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超过任何物质的诱惑,超过其他享乐。现在,我不认为写作这件事的值被扩大了,相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值已经向最小的方向靠。但我必须还得相信它有一定的意义。否则,你就会被冲走,这并非指被遗忘,而是指变得和别人一样。
抓住理想我才能继续前进
《第一财经日报》:1999年你为《保尔·柯察金》改编剧本的时候,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阐释,你要借此回到人性的立场上?
梁晓声: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在临去世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一段我们从小就能背诵的话。但是,按照我的剧本,保尔逝世之前说出的不是别的话,而是“我爱过”。然后,这句话通过他的妻子传达给其他人。我当时在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我已经将他定位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一生无论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都是他带给别人的。对于他只有一次的生命,如果他没有真实地爱过,或者获得过爱,肯定是令人忧伤的。这是我的生命观。
我也把这一生命观用到乔乔身上。她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牵挂,她知道自己生病以后,只要那份爱。乔祺把爱给了她,她的遗憾就少一些。这是我从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延续过来的情结,乔乔也会说:我爱过。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计长短,如果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不是那种为时代和社会做动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最后我们也能说“我爱过”,就是一种安慰。
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聆听,我们会发现对爱感恩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以前的爱像松木、红木,现在的爱就像合成板,质地变得非常疏松,但是乔祺和乔乔不一样,双方都因为拥有对方而对世界感恩。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种爱面前,宏大的理想也退位了,是吗?
梁晓声:一篇作品就是写一些元素而已,在《伊人,伊人》中,我坚决不允许宏大背景进入,不允许特别戏剧化的情节进入,也不允许那种大张大合、特别激情的语言进入。这部作品和从前的理想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就是一种情愫。
理想主义几乎只能是非常时代的一种精神特质。在这样一个俗常时代,人没有信仰,我就是用最俗常的爱情作为主题,看看我的小说能变化到什么程度。其实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几乎意味着是一种行为艺术,是我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放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已经泛滥成灾的主题上。
《第一财经日报》:你现在特别强调“人文主义”,这是不是一个在《今夜有暴风雪》的时代被遮蔽的立场?
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我还想不到这些。此外,我的很多作品当时处于能发出来和不能发出来的边缘,是理想主义拯救了它们,使它们能发表。
《第一财经日报》:写《伊人,伊人》是为了回到这个立场?
梁晓声:《伊人,伊人》不能完全涵盖这一立场,因为其中不包含社会公正。我还写过很多杂文、议论文和散文,分解掉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话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你来说,“人文主义”的立场是否就是一种平民的立场、情感的立场?
梁晓声:是的。为富不仁肯定是最令人嫌恶的。西方文化已经成功地用200余年的时间教育了西方社会,使穷人在心理上自强、自立,同时,社会在道义上给穷人提供更多帮助。这也使富人了解到富人对社会公益的义务远远多于穷人,使他们明白那才是富人受人尊敬的一方面。而我们却帮助富人炫耀他们拥有财富之后所过的那种得意的生活,以此在文化上进一步伤害穷人,伤害穷人的人生感觉。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你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告别了理想主义,但还是理想主义支撑着你。
梁晓声:说到底,所谓理想主义有一个特征,它总是企图抓到一点,现在我抓住的就是人文主义,我一定要说服自己相信它。如果哪天这一点都在我的搂抱中动摇了,确实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
人物档案
梁晓声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使其一举成名。之后,随着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等作品的发表,梁晓声成为知青小说代表作家,1984年因而被称为“梁晓声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