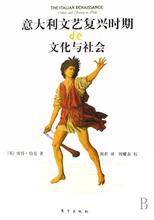“一个爱国,各种表述”。曾经被视为高尚的情感为什么渐渐沦为一种“脏话”?爱国还是不爱国,以及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为什么也成为问题?如果站在三十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便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精神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而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未来,必首先决定于全体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加塞特的不安爱国必须讲逻辑。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某种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初,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8226;加塞特便在《大众的反叛》一书里条分缕析,发出警告:“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此时,加塞特已经意识到国家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当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让加塞特不安的是,国家作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在加塞特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就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www.aihuau.com|34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这样谈到“大众人”(A Mass-Man):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者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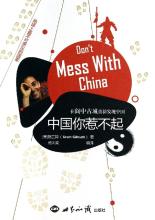
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加塞特将人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加塞特的洞见预言了发生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样是今天欧洲国家让渡主权,建设欧盟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正是因为这一洞见,该书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称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于二十世纪,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十八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十九世纪。替罪羊和替罪狼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行,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唯一未来”(人间天堂)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为国家献祭通常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奉献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个人自由;另一种是将别人奉献出去,此时“爱国”便与寻找替罪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方面,当年纳粹无疑是将两者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二战期间犹太人是替罪羊,那么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纳粹犯下的罪恶完全推给希特勒则无异于寻找“替罪狼”。毕竟,希特勒是民选总理,他在组织吃人的时候每个选民都在场,甚至领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尽管旧时代已经翻过去,但“爱国者”热衷寻找替罪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式的伤情追问。应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或这或那的不足,任何国家都会给人还不够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为看到时代有不足,看到“国家还不够爱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大有可为。近两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现代国家,就在于实现公民与国家相爱的宪政爱情。被策划的情绪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十来年后的2009年,一本由五个人拼凑而成的《中国不高兴》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开支持中国走西方市场经济道路,或者赞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锺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体制外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五人帮”与出版商却很高兴。事实上,只要看看《环球时报》的头版标题,你就知道,在中国谈政治还有比民族主义生意更好做的吗?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就此撰文:“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