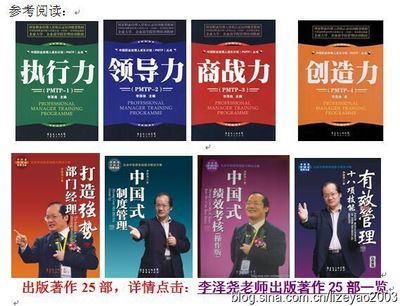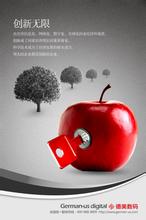关于汉语、汉字、国学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很久没有那么热闹过了。2013年以来,从繁简体字之争到台湾国学教材引进大陆,从“保卫汉字”的呐喊到电视台一时涌现各种汉语知识型节目,从降低高考英语分数比重到语文教育被指僵化,媒介和民间的讨论几乎没有停过。空前的热闹讨论常常意味着空前的焦虑,汉字、汉语、国学真的遭遇严重危机了吗?在危机面前,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为传统文化寻一条出路? 台湾,一直被认为保存了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文传统写作方式。那么台湾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对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奭学,请他讲解英语与国学在台湾的真实情况,及其折射的东西方文化。 在台湾,很多课会被英语占用 时代周报:在台湾,英语教育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 李奭学:像我们那个时代,也就是四五十岁年龄的人,英文教育是从小学毕业,也就是初一开始的,现在就比较早了,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我们那时候资源没这么好,所以从初中一年级才开始,但要是家里条件好可以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在私立学校就可以较早地接受英语教育。 时代周报:英语教育在台湾的学校里是什么样的地位? 李奭学:在台湾,学生学习英语是占用很多时间的。在中学时,英文跟数学是最重要的两门课,国文都还不算是重要的课。在考试制度下,大家都觉得国文自己读就会了,数学要推算,英文也不是说自己读就会了。特别是我们那个时代,“升学主义”是第一位的,体育课、音乐课都不见了,尽管课表上都排着这些课,但都挪给了数学老师、英文老师,所以他们占用了很多时间。即使在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学生升学的通道已经顺畅了很多,但英语和数学还是占用很多时间。我看我小孩的课表,英文的比重还是很大的,其他课还是会被英文或数学占用,特别是到考试前,很多其他课都会被拿来给英文或数学用,台北尤其严重。 我听这两天电视的新闻,讲大陆有些地方英语(在考试中的)比重想要下降,激烈一些的省份如江苏想要取消掉英语考试,是吗?如果真就是新闻讲的那样,我觉得是有点太超过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觉得太过了呢?英文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李奭学:是英文对人生的影响?还是英文教育对人生的影响?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大陆太大了,而台湾只是一个小岛。台湾现在的国民教育,也就是基本教育是12年,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读英文至少得读到高中三年级结束。我们那个时代只要读到国中结束。这样看来,英文在基本教育里占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一是看英文教育本身对人生的影响,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类人怎么读也读不会,越读越痛恨英文:一类人一读就会,越读越有趣也越喜欢。在任何社会都有这两种人,台湾有大陆也有。 二是英文对人生的影响,只是考试的工具呢,还是说对生命来讲是有用的?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是非常肯定的。不管你喜欢英文还是不喜欢英文,但只要是英文程度好,对你一定是有好处的,对在台湾的人来讲是这样的,对在大陆的人来讲也是这样的。台湾是一个小岛,资源有限,必须依靠四面八方来的讯息,同时需要把自己制造的东西往外面送,所以贸易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英文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就非常要紧了。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英语确实只是工具而已,英文不会是对象。即使是我,我也只是在写《英语词源》时才把它当作研究的对象。话说回来,其实把英文当作工具,对有些人来讲是可以的,在使用英文方面是会发挥很好,但是把英文当作研究对象的话,更得力,好处会更多,因为对它的了解会更大,使用的范围就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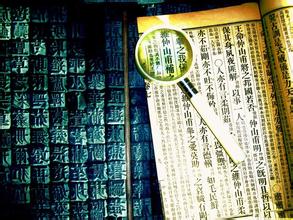
对大多数人来讲,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考完试了,搞不好就不用了。比如说你考到中文系去了,你对中文有兴趣了,可能很快就把英文给忘了。对我来讲,英文就不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比如常常在我看英文书的时候,跟某个词汇、某个句型相关的外文就会全跑到脑袋里来了,尽管现在我不再研究词源也不研究英语的历史,但这些相关的外文还是常常跑到我脑袋里面来,它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读国文基本是为了修学分” 时代周报:那“国学”呢?国学在台湾的学校教育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李奭学:它真的只有考试上面的作用。 时代周报:最近有一套台湾的国学教材引入大陆的中学,引起很大的关注。现在大陆人能去台湾自由行,不少人都会讲感受到台湾人的彬彬有礼,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孔孟之学很丰,如此之类。这和国学教育有关系吗? 李奭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当然,台湾在国学方面读得确实比较多,但你说的那个印象我觉得是个错误的印象,只能说台湾社会所使用的中文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1949年以前中文的表达方式。 近年来两岸交流很多了,我观察到,现在有5%-10%的人使用的是大陆式的语言。大陆强调比较通俗的语言,比较粗。我跟大陆人接触后的感觉是:大陆的语言和台湾的语言差别是非常大的。这有历史的因素,比如大陆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台湾在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学教育是否那么重要,见仁见智,有些家庭觉得重要,有些家庭觉得没什么,在学校里面它只是被当作一种升学的工具。像我们读书时,国文的比重非常大,高到125分,英语才100分,所以国文好的人占很大优势,但现在没有这么重了。现实是如果你要生存,要生活,但又不当国文老师的话,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英文可能更重要。 在台湾,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人想要出国念书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风气,至少在十年前还是一种风气。现在可能要好一点,因为台湾教育已经处于一种完整的状态,很多人都不大愿意出去念书了,反而是我们这边的教育部门鼓励学生出去读书,那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都是往英语系国家去的。在这种状况下,英语当然比国语来得重要。 即使在台湾本土也是这个样子,比如我女儿现在在读艺术史研究所,但可以说我女儿是沾英语口语的光才考进去的:她在美国长大,回台后念的是英文系,她的英语非常顺,非常自然。考研究所都有口试,有的所如果用英语跟考官作答是会加分的。就我所知,在所有学生中只有我女儿能从头到尾用非常流畅的美式英语跟考官对答如流,她笔试只是考过而已,但在口试中占了太大便宜。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出英语在台湾的作用有多大。 还比如,有的学校规定,老师若全程用英语授课的话,课时费会增加;若有英文著作出版或英文论文发表,那优势就更大了。这样看来,就语言来讲,国文是读书过程中不得不读的,国学就要看有没有兴趣了。 现在的国文教育也没有我们那时那么强,我上大二国文时,老师给我们上的都是校勘学、版本学。所以过去跟现在,台湾的国学也是很不一样的。学习主要也看有没有心,有心的人在看国文或国学的时候,就会记得比较牢,能出口成章。国文在升学的教育里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不升学的时候,它几乎就没有地位,尽管你还是要读国文,但大部分时候只是为了修到学分。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是否会有人出来强调国学如何重要,文化必须如此传承? 李奭学:社会上当然还是会很重视那些讲中文讲得非常好的人,能出口成章或下笔成文,能看出中文底子的,但跟英文比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大陆人会觉得台湾人讲话有礼或有内涵,这的确是有历史因素的。大陆报纸和图书上的文字都比较通俗,还有一个原因,像马列全集都是翻译来的,所以翻译腔自然存在于大陆的语言中。大陆在推行这种翻译腔的时候,台湾正在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时候在台湾,即使写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简体字,也是会被扣分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大可能写简体字的。我是蛮喜欢写简体字的,但只是个人习惯。 说是崇洋媚外也好,说是实际利益也好,或者说是整个社会风气,但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国文教育是蛮长的,对学生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我们的课本到现在为止,都还要求中规中矩的中文,就是1949年以前的那种文体,以此来写作,课本是这样的,学生又受课本的影响,所以下笔、讲话都是传统中文的那种使用习惯,翻译腔当然也会有,但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台湾比较少一点。 我在念书时,有很多人讲国学很重要,但现在非常有限,听你问题时我就在想说有谁会出来强调说国学有多重要,因为现在没多少人强调国学是多重要,也没有人会讲文化是要借着国学传承下去的。其他层次的教学我不清楚,我是在翻译研究所教书,学生都是博士,是社会的精英,但不大讲国学。 外来文化是避免不了的。在台湾,且不说英剧、美剧,电视早被日剧和韩剧充斥了,这对台湾文化影响当然很大,而且到一定时候就会被人认为是固有的文化。我们知道很多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文化,最后都会本土化,比如佛教,很多人拜,但都不知道自己拜的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像观音的坐像已经中国化了,而不是印度佛教里观音的形象了。在唐朝,“谏迎佛骨”,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大事件,韩愈认为是外国来的东西,皇帝不可以迎接,但更多人已经接受佛教并认为佛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了,所以韩愈并未成功阻挡外来的文化。那时候冲突还比较严重,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文化传承在任何时候都是跑不掉的,但别的文化过来也是没办法抗拒的。18世纪的伏尔泰说过一句话:“任何翻译的文本对于接受这个文本的国家都是一种暴力。”到了现在,大家不会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 时代周报:那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英语与国学的教育? 李奭学:我认为两者都蛮重要的。现在没有人会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英语教育当然很重要,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英文讲得很好,能用英文写作,更多的人还是必须要靠国文写作,我个人认为两者都不可以偏废。就一般人而言,我比较倾向于英语工具化,国语是涵养。除非是专攻英语,否则英语只能是工具,英国文学也很少能跑到一个人身上去。当然像从英语系到英语研究所,一路读上来的人又很不一样了。我个人认为,如果英文能钻研得更深的话,去接受西方好的东西,对自己会有好的影响。这一点,西方人还不是很了解,他们现在基本上还是“西方中心主义”,将来可能会吃到苦头—东方人对西方人了如指掌,好处也吸收差不多了,还融汇了东西,可他们还是单纯的西方体。 两岸的计算机书写已把汉字拼音化 时代周报:你提到你喜欢用简体字,现在台湾对简体字的争论多吗?在大陆,有知识分子越来越喜欢用繁体字,也是因为电脑打字不费事,似乎喜欢从繁体字中找到些失落的东西,你怎么看呢? 李奭学:我喜欢用简体写,有个人原因:我用光笔写作,简进繁出,方便得很,辨识率还比繁进繁出强。台湾一般人仍难接受简体字,倒没为这事争辩过。一般人大多用注音符号打字,繁体一点也不难打出,大概也构不成争论。两岸的计算机书写其实已把汉字拼音化了。这点我没意见,唯一担心的是同音白字特多,我们这儿的电视字幕,几乎没有一个节目正确无误。我对大陆简体没研究,但遇到“王而云”、“宋伟杰”时,我就愣住了,不知改为繁体时,这“云”是“雲”或“云”,“杰”是本字或是“傑”。繁体是种文化怀乡病。计算机只管音,已解决了繁体难写的问题。哪日若又回到手写,保证简体又盛行。人往高处爬,语言、文字往低处流,只会愈简,愈俗。 时代周报:你在《中外文学关系论稿》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章,很多话题也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你有一篇文章《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思考—傅斯年“西学为用”的五四文学观》,几十年过去了,大陆仍旧在中西夹缝中思索,似乎还没有找到文化的出路。台湾是否也有相同的困惑呢? 李奭学:大陆有文化断层,如今可走传统,可走西化,两者如一定要择一,必然见矛盾。但如可兼容并蓄其优者,我看不出矛盾—你我讲传统中文时,不也都用西来的电冰箱?如今的问题不是傅斯年那一代要在“中西夹缝中思考”,而是应放任自然,彻底让新的文化自然形成。台湾在1960年代也延续“五四”,有过一阵子中西文化的辩驳。如今几无辩论,我敢说大家在想的是“师夷之长技”,但目的非在“制夷”,而是“争锋”。“竞争”是我们无可遁逃的命运。我学生生涯最后阶段是念比较文学,因我读书一向不分东西方文学,见“好”就收。如今几乎以明清间耶稣会文学为研究对象,大家或以为狭窄,天晓得这里面牵涉到跨国、跨洲、跨宗教、跨文化与跨文学等诸多事项,问题大得我从1990年初到今天都还研究不完。我的心得是:今后人研究文学若再死守着所谓“固有”,将来必定出局。 时代周报:这样是说传承文化和接受外来文明并不矛盾,那如何更好地融洽呢? 李奭学:这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问题,得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有非常强的认识,在这种前提下去接受外来文明,才不会迷失在外来文明中,否则会变成“banana”—黄色外表,白种人的思想。当然这并没有错,但是这当中白的,应该是西方好的方面,而不是西方坏的方面。比如到西方去,那些服务生的态度,绝对比在中国的服务生的态度好太多。再比如说西方大学的图书馆,他们的图书馆馆员对学生的问题都能有非常专业的解答。像我去西方那些研究性图书馆,他们的专家都会出来接待,但我在大陆遇到的某些情况是被拒于门外—我想借一本古老的书,但他们根本就不想借给我,他们把善本书当作是古董,是要秘藏的东西,这种情况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很严重—上海图书馆就好多了。你是否把你的职业当作是服务人群的职业看待—是在保存这件家私,那自然不会外借,可对西方人而言,书籍就是要给人研究、给人看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大方,即使是中世纪的东西,只要你好好对待,还是照样会拿出来借人读的。我去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借书看,像羊皮卷之类的古书也能借阅。西方好的东西不应该拒绝,若拒绝就是自绝于世界;同时传统文明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部分应该保留,坏的东西应该剔除。 有些普世价值,我觉得没有东西方的差别。我是读外文出身的,但在中国文哲研究所工作,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反而常常还能因为读的是外文,在读中文时,能够跟西方的东西彼此互相照应,这就到研究的层次去了。这是我非常深刻的体会。我经常在大陆出差,会跟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接触、聊天,最大的感触是大陆在学习西方,但只是在学西方的表象,比如大陆也学西方吃牛排、喝红酒,但吃牛排、喝红酒背后的文化就不知道了。我认为大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这个教育不是简单的西方教育,而是要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进来的教育,也不是拒绝传统的教育,应该是把传统的好的东西再衔接起来的教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