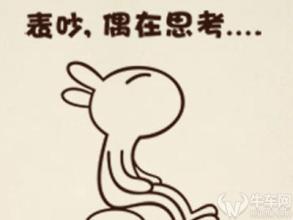中国人经常觉得日本人的英语不好—这是错觉。日本人的英语是“说得不好”,并非“学得不好”。根据雅思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年,在全球41个主要雅思考生国中,中国大陆考生的学术类雅思平均成绩为5.6分,排列第34名,落后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东亚国家,仅排在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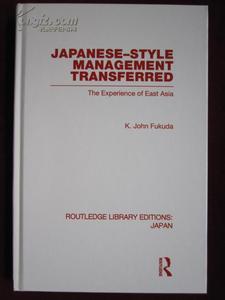
“说不好”,不是“学不好” 日本人在英语学习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发音不标准。这其中有两大原因:一是在日语中存在大量的外来语,这些外来语是各个时期从各种外语(英语最多)中引进的,用片假名进行了读音标注后,成为日语的组成部分。对于从小习惯了听、说外来语的日本学生来说,开始学习英语时,这些似是而非的外来语读音就成了干扰,要知道,“母语”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二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比较内向,追求完美,害怕出丑,因此往往羞于开口,给人一种口语弱、交流不积极的印象。 抛开这些弱点不说,日本的英语教育中有其实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中国地区差异大,应该因地制宜建立“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教育模式。笔者仿照发展经济学中“最适技术”的概念,提出“最适英语教育”的观点。北京教改方案中,中考和高考降低英语分值的同时,增加了听力测试分值,而山东却提出取消听力考试。这种区域性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适英语教育”的现实合理性: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京,其生活和工作中接触到的外国人较多,直接进行英语交流的必要性高,强化英语听力教育,有其合理性—再加上北京的教育资源(人力、财力等)充沛,具有推行的实力。 北京的发展阶段和日本比较接近,做法也有相同之处。传统的日本英语教育和中国相似,即重视语法、重视阅读和写作。作为教育立国的国度,日本从未在教育改革上停步。就拿英语来说,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和英语的实际交流能力,从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自治省与外务省等不断联手推出各种政府项目,投入资金,在中小学课堂引进和充实外教(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师资力量不断壮大)。北京教改方案中对听力的强化,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现实需求是第一推动力。 第二,英语教育的社会化、阶梯化。在教育立国的社会里,教育的实施者不只是学校,还包括职场(雇佣人力资源的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链条。很多人抱怨学生时代花了大量时间学习的知识(包括英语)用不上,这种抱怨并不一定合理,因为知识的学习、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一个厚积薄发、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些知识并非“用不上”,而是你“感觉不到”而已—其实,人生最重要的那些知识,比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份具体工作需要“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一般需要企业通过培训来完成。 在日本,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有比较成熟的人力资源培养规划—包括语言的培训,以及专业知识的培训。我们看到:在终身教育的跑道上—先是学校教育,然后是社会(职场)从学校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下一个阶段的培养教育。如果把学校教育称为基础教育的话,那么社会教育就是应用性教育。没有基础教育,应用性教育就无法延续,而没有应用性教育的话,基础教育就好像是不能抽枝长叶的树干,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第三,快乐学习,是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的通道。 日本在1980年、1992年以及2002年三次推出“愉快教育”(ゆとり教育),目的是使学习者不至于因为填鸭式教育而感到焦躁压抑,发现和培育自身多样的才能。“愉快教育”不是单纯地“减负担”,而是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彻底调整,是回归“快乐学习”—快乐学习,是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的通道。 日本从2011年开始实施小学英语教育。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每周须上至少一节英语课。这些英语课程不是必修课,以简单对话、书写、唱歌和游戏为主,毋须考试。从2020年起,小学高年级英语将成为必修课,每周上3节英语课,以掌握基本读写能力并接受考试。同时,英语教学提前至三年级,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周至少要上1-2节英语课,但无需参加考试,以免他们失去学习兴趣。 对照日本,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幼儿就已经开始,小学升初中英语和数学就成这择校的条件。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包括英语)的后果如今已经显现: 根据2013年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25%,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都是曾经的高分考生。与此同时,近6年间,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激增35倍。而语言文化的障碍,却让他们沉溺在交际封闭的华人圈子。这群涌出国门的年轻学子,似乎从未到达彼岸(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7日)。科学的教育,必然是人性化的教育。快乐学习的理念,会被中国社会普遍接纳并且实施吗? 先精通,再批判 英语是西方文明的载体,不限于工具性意义—但在非母语国家里,英语学习偏重于工具性学习(单词、语法、句型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国语的学习内容偏重于文化、历史、文学等教养性知识。 笔者认为,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的培养等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应该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在了解西方文明之前,应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有比较才有发现,国语的教养水平,是你透视西方文明的那双慧眼,是外语这个壳里的填充物。这次的北京教改提高了高考中语文的分值,固然值得肯定,但成功的国语教育,并非只靠分值提高就能实现的,有助于教养水平提高的教学内容和结构上的调整,是更为艰难的改革任务(这要看后续的教学大纲、评价体系如何改变了)。 说到国语,不能不讲讲汉字。今年夏天被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曝露出国人汉字书写能力降低问题,应该说,这和电脑普及有很大关系—在使用汉字的日本,问题同样严重。不过,日本采取的是弹性应对法:对笔画比较多、使用频率不太高的汉字,平时就写平假名(类似中国的拼音)来代替;比较正规的出版物会使用比较多的汉字,不常见的汉字上面往往会标注假名,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发音,但不熟悉汉字。通过变通的方法,汉字在日本总体上并未被冷落。人们按需学习,汉字掌握的多少,取决于需要的程度。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变通做法,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 现代文明是西方率先开启的—“脱亚入欧”的倡导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在他的自传中说,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汉学深恶痛绝—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日本的发展来说,西学以及后来的英语才是新知识的来源。不过有趣的是,福泽渝吉在少年时候首先接触的就是汉学,而且学得非常不错,汉学功底非常扎实—也就是说,福泽渝吉对汉学的批判,正是基于他对汉学的了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鲁迅身上,鲁迅有过“不读中国书”的大声疾呼,但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古文功底非常深,他自己恰恰是个读了很多中国书的人。 在接触、学习西方文明时,对本国国情、本国文明的了解始终是基础。理性认知能力,是在很多极端中不断奔跑、回头、寻寻觅觅以及思辨的结果,这里没有捷径。 “站在国语肩膀上”的英语学习这一理念,也许可以成为排除国语和英语之间非此即彼的争论,走向和谐统一的路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