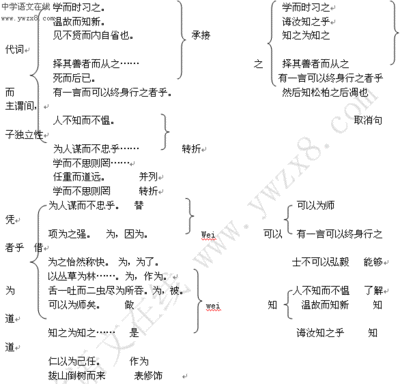王充是一位奇人,《论衡》是一本奇书。作为大半生在县、郡、州三级主管人事的官员,《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方面有着超越前人的研究,后人对其人其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褒贬,都没有对其人力资源思想给予足够的重视。《论衡》一书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以命定与偶合的关系来讨论人力作用的机制,对“遇、幸、偶、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是古代应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人力资源的先驱。在人性问题上,王充辨析了性命关系,强调人性的可变性,推崇教化的作用,又以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贯通人性研究,对人才测评落脚于相术。这些积淀,为他探讨人才群体结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王充是东汉时期人力资源理论的开创者。 奇人王充与奇书《论衡》 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不仅有观点之争,而且还有史实之争。《后汉书》本传对他的记载相当简略,而王充《论衡》的最后一篇《自纪》则相当详细,可以补充本传之不足,近代的研究者,甚至按照《自纪》提供的线索整理出了他的年谱。然而,越是这种看起来清楚的地方,越有可能引发新的争论。例如,王充是否“受业太学”并“师事班彪”,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本传中有此记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否定,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少质疑。但是,由于王充《自纪》中的生平陈述没有写他的太学经历,反而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黄晖、胡适等人,都肯定王充游学洛阳的记载;而另一著名学者徐复观则认为,王充好炫耀,如果有游学洛阳的经历,他在《自纪》中不会不说,所以本传的记载不实。这几位,都是史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家,他们尚且争论不休,普通读者只能莫衷一是。王充研究与《论衡》研究中类似的针锋相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此人此书之奇。 这种学术上的争辩,作为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普通读者,介入其中太费气力。黄晖和胡适似乎说得太肯定了一点,而徐复观的推论又似乎太绝对了一点。好在《论衡》一书确能代表王充的思想,这一点,学界褒者贬者都没有争议。所以,按照《论衡》文本去分析论证王充的思想,要比考究他的生平更切实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王充字仲任,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建武三年出生于会稽上虞,永元年间去世。他与王符始终为处士的情况不同,曾先后在县衙担任功曹,在郡都尉和郡太守手下担任功曹,在扬州刺史手下担任从事,转为治中,章和二年辞官回家著述。从20多岁开始担任县功曹起,几次在家赋闲著述,又几次再被征聘,直到60多岁彻底离职,可以说其生涯大半是在官场。但他的社会影响,却不是来自他的政绩而是来自他的著作。根据王充的《自纪》,他对趋炎附势、世态炎凉不满,写了《讥俗》;对政务失当、治理无方不满,写了《政务》;对文献虚妄、语多不实不满,写了《论衡》;老年则针对保健延年的需要,写了《养性》。流传后世的则只有《论衡》一书。 对王充的批评,以徐复观为代表。王充出身低微,没有当过高级别大官,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徐复观认为其思想狭隘,没有见过世面,认知多有局限。而赞扬者认为,由于王充的底层经历,使他的思想充满了批判精神,代表了民间思想的兴起。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王充担任的官职是否微不足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而他长期在官场的经历,使得他能否代表民间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对王充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对两个方面不满,一是对王充“颂汉”有看法,认为王充写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无聊作品”;二是对他的文辞浅薄有看法,认为王充不过是“一个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但是,徐先生的批评,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王充一心想得到东汉王朝的重用,而且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央朝廷当一个兰台令史。徐先生十分看不起王充的这一志向,称其为“受知于朝廷以后想做的官,乃是俸禄一百石的兰台令史的芝麻绿豆大的官”。对此,徐先生可能过于轻看了。官不在大小,而在职能。王充重史学,尤其推崇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兰台正是朝廷保存档案秘籍、修史传世的重镇。以整档修史为志向,符合王充疾虚妄、求诚实的夙愿。也许,正是因为王充把班彪班固列在司马迁之上,推崇班氏的“颂汉”,立志要“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论衡·须颂》),从而让徐先生反感,认为王充不过是为朝廷拍马溜须而已。但徐先生似乎忽视了《论衡》一书“疾虚妄,求诚实”的主旨。如果把颂誉正统王朝全都看作无聊文章,把春秋笔法全都看作史家曲笔,那么,历代正史恐怕统统难逃其咎。即便是像司马迁、董仲舒这样的学者,在谈及大汉王朝时也是难免要称颂一番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事涉尊亲,言多隐晦”,“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用这种方式追求正人伦、存名教的效果。王充在“颂汉”时注重求实,辨析其中的虚辞,应该说还是值得称道的。至于王充是否因为底层社会的局限妨碍了其视野,似乎也可见仁见智。最起码,王充读书之多,引用之广,在当时的学人中是罕见的。而且他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涉猎儒墨道法诸子百家而不盲从任何一家,矜才负气有之,斥其浅薄则似乎矫枉过正。 至于王充所任的官职大小,尚需对汉代制度稍加辨析。汉代实行辟除制(辟除指长官直接任命部属),衙门中的掾属都由长官直接征聘。而按照汉代的规定,比二百石级别以上官员,均须朝廷任命。所以,凡是长官直接辟除的下属,不管重要与否,级别一概都是百石或者比百石更低的斗食。衙门中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因为属于朝廷任命,所以与长官的关系并不紧密,往往成为虚置,反而是级别较低的百石斗食之职,因为是长官自选,更能得到长官的信任。例如,六百石的郡丞,因为是朝廷所派,其实权远远比不上郡太守自行辟除的百石功曹。郡丞为闲职,而功曹为要途。所以,才留下了赵温被任命为六百石的京兆丞后感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并弃官而去的典故(见《后汉书·赵典传》)。王充恰恰在地方上一直担任功曹要职。所谓功曹,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主管一级官府的官员选拔和任免。县衙郡署,属于朝廷任命的官职不过三五个,而由功曹选任的数十上百。可以说,功曹可以替郡守县令当半个家,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守令的委托下主持地方政务。当地方长官不想理事时,功曹往往理直气壮地代替长官行使权力,而朝廷正式委派的辅佐丞尉则不能插手。汉代有不少民谣,形容郡太守不管事务而由功曹号令郡内,说明功曹一职不可小觑。王充作为功曹,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他后来担任的州从事,同样是刺史直接聘任的百石之吏,其职权更为重要。各州按照下辖郡国分设的从事,负责直接监督郡国守相,每个从事盯着一个二千石的太守,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震撼地方。“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续汉书·百官四》)所以,汉代的州从事,绝不能以“小官”视之。王充担任的从事,不是监督一个郡而是监督丹阳、九江、庐江三个郡(扬州只有六个郡),后来又以从事改为治中,所谓治中,就是州级的功曹,主管一州人事(有些研究王充的专家把治中看作无关紧要的文书之职,误;认为王充对担任这样的小官不得升迁而心怀不满,更误。治中是刺史或者州牧手下第一要职;王充自称担任治中职务是“材小任大”,可为一证)。东汉全国只有十三州,其中王充任职的扬州,主管东南地区。对于这样一位担任过相当于现代省区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后来又担任大区组织部长的人物来说,说他没见过世面或者身处底层,岂不荒唐?王充的唯一遗憾,不过是没有到中央机构任职而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王充的思想,与纯粹来自民间的王符就有了很大区别。如果说,王符代表了来自民间的批判思想,王充则是自觉地代表朝廷到民间采风;王符揭露朝政的黑暗,王充则颂扬大汉的光明;王符的论著不乏情感流露,王充的作品则注重学理辨析。 另外,汉代的地方政府中,上下级关系与后来的情况迥然有别。当时地方衙门中自行辟署的掾属,并不是对“国家”负责,而是在长官与掾属之间形成君臣关系,掾属只对任用他的长官负责,长官对掾属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这种君臣关系,对汉代掾属的影响非常之大,使得百石掾属与长官的关系,可以与三公九卿与皇帝的关系相匹。弄清这一点,对理解王充的思想不无帮助。 不过,徐复观的批评,有一点值得重视。由于王充对自己的学术有着充分的自信,形成了他的唯物而不唯心、重验证而不重传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注重物理式观察和批判性思维,常常提出一些他人匪夷所思的新颖观点。自诩“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论衡·自纪》);史称“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后汉书·王充传》)。后人往往看到了他思想中的点状闪光,而忽略了对他的整体观察。徐复观批评胡适“不曾从根源地、全面地去把握王充的思想,而只采用摭摘片段字句的方法,以建立自己的论点”,还是切中要害的。至今,我们所看到的《论衡》研究,多有“语录式”的流弊,摘出其中只言片句,脱离当时的情境任意解释,赋予其跨越时空的含义,致使对王充的赞扬声中有过分拔高的倾向。例如,《论衡·效力》中论证“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有不少人拿出其中“知为力”的观点,声称王充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比英国的培根早1500年,全然不顾王充与培根思想内涵的不同。类似这种偏差,需要引起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高度警惕。另外,徐复观在评论王充时指出,作为思想家,影响其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四:一是本人的气质,二是学问的传承与功夫的深浅,三是时代的背景,四是生平的遭遇。这几点,确实是思想史研究的门径。不论我们是否赞同徐复观对王充的点评,他所指出的研究思路,都值得后学深思。大家之大,就大在这些地方,不服不行。 王充在启蒙阶段,就显示出他与别人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为幼童,他不好与同伴嬉戏,六岁识字得到父母的赏识,八岁就学受到老师的赞扬。上百儿童中,别的小孩都因为过失受过各种惩戒,唯独他没有受过任何责备。王充自述这些时充满自豪感,然而,从他“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来看,显然性格内向甚至有点自闭,孤寂而自负。“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这正是“矜才自负”的写照。但读书多、肯思考、记忆强、善质疑,则是他的优势。 王充后来在官场上的不得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其耿介正直造成的。“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君将”在这里指地方长官;蘧伯玉、史子鱼的典故,见《论语 · 卫灵公》和《孔子家语 · 困誓》)“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这些言辞是否含有自夸,可搁置不论,但起码可以看出,在汉朝的体制下,王充注定要被官场抛弃。前面说过,汉代的郡守县令,与其辟除的掾属要结成君臣关系。王充的“君”,先后有县令、郡都尉、郡太守、州刺史,功曹一职,作为长官的倚重心腹,必须与长官取得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才可履职。如果有不同见解,也必须得到长官的认可。凡是功曹,肯定是以材能见长的文吏角色,而王充的自我定位,却是以思想见长的咨询角色,过于独立,所以会在实践中碰壁。正是这种碰壁,才会导致他对管理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很多研究者,都对《自纪》中的“污伤”、“蜚条陷之”展开想象,认为王充是被人中伤陷害而离职,实际可能不尽如此。因为按照当时的君臣关系,只要长官信任,任何诬陷都没有关系;而一旦失去长官信任,即便众人全都拥戴也无济于事。当然,长官的信任会受到其他掾属拥戴与否的影响,但这不具有决定意义。正是王充的任职与离职,使他对人事管理和君臣关系有了深刻的思考,更加重视“遭际”和“偶合”,形成了他的人才管理学说。 《论衡》一书的传播,也很有戏剧性。王充的著作在当时属于“大部头”,仅仅《论衡》一种,就达85篇(最初可能上百篇),20馀万言。对于王充的学识,当时就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按照谢承《后汉书》的记载,谢夷吾曾称道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然而,很少有人赞同这种评价,不了解他的人相当多,批评他的人也不少。《论衡》能够得到流传,得益于蔡邕的赏识。据说,《论衡》写成以后,仅仅在吴地流传,中原无人知道。作为文化名人的蔡邕偶然得到此书,觉得所言新颖,有助谈资,秘藏把玩,后来被同仁发现。另外一说是王郎担任会稽太守,得到《论衡》,回到许昌,言论大进,时人猜其“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追问缘故,方知是读《论衡》所得,遂使该书开始流传。三国时期的虞翻,论及江东人物时,曾经称道赵晔和王充说:“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但是,唐代之前,《论衡》的流传有限,即便在文士中也不普及。唐代刘知几写《史通》,则对《论衡》痛加鞭笞,认为王充“述其父祖不肖”,是名教罪人。写了《后汉三贤赞》的韩愈,对王充也不过是重复了本传中的说法,没有给予更多的评说。 真正重视王充思想价值的,是北宋杨文昌,他在整理了《论衡》后,在序言中感慨说:“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中,此书为多。”“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首次把王充摆在先知先觉的位置上。 明末清初的熊伯龙,针对历朝对《论衡》褒贬不一的情况,对该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解读和删减整理。他说:“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即把他认为“辞多重复,醇疵参半”的内容重新编排,形成新的“删节重排本”,认为原书中对孔孟不大尊敬的《问孔》《刺孟》,以及他认为有问题的篇章,一概判定为“小儒伪作”,摈弃不收;对各篇中有他认为的“小疵”,则“削而不录”(详见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这种戏剧性的“古籍整理”,恰好反映出对《论衡》一书的评价冲突。不过,熊伯龙提出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值得借鉴。所谓直读,是指就《论衡》涉及的具体事项进行层层推理,“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达到“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的效果;所谓横读,是指对《论衡》尚未论证的事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以类而推,莫可终穷”的效果。“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平心而论,熊伯龙的《论衡》删节,在今天看来不足取法,而他提出的读书二法,却没有过时,且不限于读《论衡》耳。 王充最被人诟病的,正是熊伯龙所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孔孟的质疑。所以,古人对王充的批评,多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追求“政治正确”,而学术批评并不多。相比而言,清朝学者钱大昕,对王充就不大客气了,直斥他为“小人而无忌惮者”,其罪名包括非孔刺孟、訾毁父祖、阿谀汉朝等等,尤其是命定论和偶然论,消极影响太大。钱大昕试图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角度反观王充,把王安石“三不足”之类观点,都看作是由王充发其端。“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钱大昕的这种批评,是传统儒学中抨击王充思想的代表者。 古代对王充的官方评价,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其称王充写作的动因是“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悖谬之处主要是倾轧圣贤、直言祖父之短,但也承认《论衡》的说理和辨析有其所长。“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有意思的是,《论衡》的名气之大,致使乾隆皇帝也为此发表了一番议论。乾隆说他曾经对《论衡》的“识博而言辩”很感兴趣,但没读过全书。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才读了《论衡》全文,“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在乾隆眼里,王充的问孔刺孟,与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无异。但乾隆尚未把《论衡》彻底打入另册,而是在跋中写了如下判语:“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到了近代,对王充的肯定逐渐增加。黄侃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赞扬《论衡》。“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馀。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汉唐学论》)对王充评价非常高的还有章太炎。他认为,后汉到曹魏的诸子,值得称道的只有王充、仲长统、刘劭三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论式》)章士钊从逻辑学的角度肯定《论衡》的功绩,一反众人指责《论衡》重复芜杂琐细的问题,认为古代汉语为求表述简练,往往省略推理过程,曾国藩批评古文不适合辩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而《论衡》一书,是古代逻辑推理的异数,以琐细的推理,体现逻辑的精神,“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答张九如》,《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胡适从“效验”角度论证王充的科学精神,认为王充是古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代表。这些不同说法,都从某个侧面对王充的思想有所发掘,但也产生了一些无意识的偏向。侯外庐以唯物史观解释王充,批林批孔又把王充作为古代反孔的先锋,都与这种偏向有关。 从管理学角度看,因为王充有丰富的行政经历,尤其是人事管理的经历,而且加上君臣之间的离合,人才评价上的失真,使他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思考。例如,仅从任职到离职的反差来看,王充曾经多次就职又离任,“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王充的个人得失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或者认为王充对官场上的失意耿耿于怀,或者认为王充对政治的黑暗萌生了更强的批判意识。这些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总觉隔靴搔痒。应该说,从要职到赋闲的经历,作为学者的自我定位和作为官员的在位离位,促使王充对人的本质、人的才能、社会与人、组织与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尽管他的《政务》已经佚失,而《论衡》虽是一部分析事理、矫正虚妄的著作,但其事例往往来自识人用人。从中提炼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和观点,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某些不足。 人力作用的机制探索——命定与偶合 《论衡》一书,本来是针对各种文献的辨谬校正之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 · 对作》,以下只列篇名)但其写作目的,却不是简单的文献考证,而是要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操作办法。所以,王充在辨析论证过程中,首先针对的并非文献谬误,而是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偏差,为现实政治提供新的解释。即所谓“《春秋》为汉立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 一般认为,《论衡》的篇目顺序,出于王充自己编排,后代没有多大变动。由是观之,《论衡》的开篇是命运问题,由命运讨论引申到性情问题,由性情讨论扩展到认知活动中的虚妄辨析(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即“九虚”“三增”到“谈天”“说日”,其中最富批判精神的是《问孔》《非韩》《刺孟》诸篇),然后再回到人力资源的结构关系和评价识别,由人之本质、人事关系到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层层展开。其中关于自然观察、物理辨析、民俗纠谬、文献考证的篇章,服务于人力资源和政治现象的论述。尽管各部分有交叉重叠,但思想线索大体可寻。 当今研究《论衡》者,往往从“唯物主义”、“科学思想”、“反对谶纬”、“破除迷信”等角度总结其内容。这些都不算错,但总有以今度古、削足适履之嫌。如果回到王充的原意,不难发现,他的本意是为汉朝的现实政治服务,反对俗儒的厚古薄今。《论衡》的主要篇目,都同汉代现实密切相关。总体上看,《论衡》涉及到以下思想领域:以形神关系和性命关系为主题的人性论;以遇、幸、偶、适为主题的命运论;以道实证验为主题的知识论;以宣汉颂德为主题的政治论;以君臣关系为主题的贤佞论;以德才关系为主题的儒吏论。至于今人特别看重的唯物思想、科学记载等等,则是穿插在这些主题中的素材和资料。回归《论衡》的本意,我们不妨说,王充开创了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研究的学术领域。 《论衡》讨论命运问题,着眼于个人如何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人的作为要受何种因素制约,这些制约对人的成就有何影响。很有可能,正是王充长期担任功曹的职务经历,使他对人力资源有着特殊的感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王充以《逢遇》、《累害》、《命禄》、《幸偶》以及《偶会》等篇,大谈人生成败的偶然性,形成了他的命运论。 王充认为,人是由命运支配的,而命运与人性是两回事,并进而以此解释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异。他说:“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义》)“故夫临事智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禄》)涉及命运的事项,是人力不可为的。“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智者归之于天。”(《命禄》)并希望以此划出人力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并对人的努力与社会回报之间的不对应给出自己的解释。“才高行洁,不可保必以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以卑贱。”(《逢遇》)许多人都对王充的命运论不以为然,认为他否定了人的能动和努力意义。实际上,王充的这种论点,恰恰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础。如果强调命运可以由自我努力改变,固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励志说法,然而,这种说法的最大漏洞在于其逆推理的荒谬,即命运不好来自于缺乏自我努力,从而否定社会的不公和管理的缺陷。王充特别强调命运不由人,正是要揭示道德、才能、品行、行为与社会回报不相符的奥秘。正如孔子也承认生死有命,却并不因此否定个人努力的道理一样。 那么,为何会出现个人努力与所得回报的不对应?王充看到社会上存在大量类似现象。“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禄》)他给出的答案是:出自偶然。汉代儒家谈命,有“三命”之说,“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是“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随命是“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遭命是“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这种“三命”说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对应到实践中的具体个人则只有“一命”。王充指出,三命不并至,正命不需要个人努力,从个人努力的角度看,“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命义》)。所以,三命之说并不能回答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为何具体人员会遭际不同的命运。由此,王充提出了自己的偶合观点,并在他对遇、幸、偶、适的论证之中展开讨论。 所谓“遇”,是指不靠自我努力的遭际。《论衡》的第一篇就是《逢遇》,说明王充认为“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首要位置。他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表现在人事管理上,遇与不遇有多种情况。“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把不遇归纳为以下五种情形:“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对于这些情形,王充都举出了相关事例加以说明,在此不赘。归纳起来,上下之间,合则遇,不合则不遇。合与不合,既有品行、道德、才能、技巧等因素,又有欲念、目标、言说、相貌等因素。“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所谓“遇”,不是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更不是见风使舵,主动适应。“遇”是自然而然,“揣”是迎合,“求”是努力,后二者都不是“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由于“遇”是非人力的自然状态,所以,赞誉“遇”,诋毁“不遇”,实际是“不能量操审才能”的表现。“遇难先图”,不可通过事先策划谋略来解决“不遇”问题。 所谓“幸”,是指不由自身行为带来的祸福。“脩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累害》)所以俗语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命义》)王充突出论述的是不幸而不是幸。仕途停滞不进,操行遭到毁伤,声名被人贬低,罪过积于一身,不一定是当事人的自身过错,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遭际与当事人的才行智能无关,而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造成不幸的因素,有“三累三害”。所谓三累,一是交友不慎所累,“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二是他人嫉妒所累,“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三是疏远他人所累,“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所谓三害,一是职位竞争所害,“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二是操守不同所害,“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三是被部下的不当行为所害,“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王充指出,士人身处社会,会受三累;身处官府,会受三害。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强调,三累三害所坑的恰恰是圣贤俊杰。他赞同孔子的说法:“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这句话据考证是王充自己所言,假名孔子而已)侥幸一词从来是针对小人的。只有清白无瑕,才会遭受污垢所累害。“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搏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累害》)所以,真正了解累害之谤,反而能够观察到贤洁之实。弹琴者恨不得折断伯牙之指,赶车者恨不得摧毁王良之手。无他,嫉妒心理使然。真正的圣贤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无以防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圣贤不追求虚名,不设防避害,所以最易被伤害,而邪伪小人,“治身以巧俗,脩诈以偶众”,所以人人称道,上司重用。由此,王充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流言毁伤中发现圣贤,在众口交誉中觉察奸佞。 所谓“偶”,是指君臣之间的匹配。“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幸偶》)“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命义》)同样的行为,君臣相偶,就能形成协同作用;君臣不偶,就会遭到排斥。 所谓“适”,是指自然相合。与偶连用,表示恰巧遇合。“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禄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命义》)凡是各种遭遇与命禄偶合,都属于“适”。非人类的自然现象也有“适”,杞梁之妻恰好因为怀念丈夫向城而哭,城墙恰好在此时崩塌,二者偶合,于是流传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王充认为这就是一种“适”。“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感虚》)。由此可见,君臣之适,在王充眼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么,这种遭遇和偶合,是不是王充对自己仕途的感慨?到底对人力资源理论有多大意义?许多研究者认为,王充是因为自己的仕途受挫,才在命运问题上大发议论,有些人干脆就把这种议论看作一种价值不大的牢骚。所以,大量研究《论衡》的著作,都对其命运论着力甚少,或者简单提及,贴一个宿命论和偶然论的标签了事。本文认为,王充的命运论,即关于命定和偶合关系的论证,是中国古代探讨人力作用机制的重要篇章。宿命论完全排斥个人奋斗的意义,而因果论又无法解释善行不得善报、贤能不得重用的不合理现象。古代的人力资源学说,不论是何家何派,都无法在学理上跳出这一矛盾。王充则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人的命运既是“自然之道”,又是“偶适之数”,是既定之“命”通过不定之“偶”形成的随机关系,从而为跳出决定论思路提供了可能。一方面,“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命禄》),从而为孔孟这些圣贤也屡遭厄运、伍子胥和屈原等人为国尽忠反遭冤屈提供解释;另一方面,人在命运面前不是无所事事,认知命运中的遭遇偶合可以增进主动,防范不幸。在逻辑上,王充首次把随机分析引进了人力资源领域,在论证方式上几乎接近于当代管理学家马奇的“垃圾桶理论”——人具有不同的材质,面临不同的场景,上司有不同的需要,官场有不同的准则,是否能够取得积极的社会效应,全在于这些因素的际遇偶合。可以说,《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首开了随机性研究的先河。固然,王充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对随机性的理解偏于消极,但这种思路,仍然值得向纵深发掘。 再进一步,管人者强调外在命运,被管者强调自我努力,有利于产生正面效应;而管人者强调命运在己,被管者强调外在时运,就可能导致怨天尤人。批评王充者往往只看到他的仕途失意,而忽略了他本来具有的功曹身份。理解这一点,对于评价《论衡》的人力资源思想至关重要。 人性 · 禀赋 · 骨相 任何管理研究,都会遇到人性假设问题。《论衡》对先秦以来的人性讨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充把先秦的人性观点归为四大类:一类为孟子的性善说,一类为荀子的性恶说,一类为告子的无善无恶说,一类为世硕的有善有恶说(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同世硕有细微差异,但都属于这一大类)。在此基础上,王充进一步介绍了汉代以来陆贾的礼义为性说,董仲舒的性情阴阳说(性生于阳,情生于阴),刘向的性内情外说等。 王充基本同意世硕一派的观点。他感叹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本性》)在王充眼里,孟子说性善,符合中人以上的人性;荀子说性恶,符合中人以下的人性;告子说性无善恶,扬雄说性善恶混,符合随着教化改变的中人之性。他们都只把握了人性的一个侧面。 在性命关系上,王充强调,性有善恶,命有吉凶。性是可以改变的,而命是人力无法操纵的。“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禄》);“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命义》)。从性与命的不同出发,王充指出人性是可以变化的。“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率性》)善恶的渐染变化,体现了教化的力量。在这里,王充回归到儒家的治理思想轨道,彰显人为的作用。王充认为,命运是人力不可为的,而善恶是人力可为的。如果不能改恶为善,治理就毫无意义。王良和造父以擅长驭驾得名,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把驽马变成良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们不过是平庸的驭手而已。子路本来是个狂徒,在孔子的教育下,名列贤人。“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砺,闿导牖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土壤有肥沃的,有贫瘠的。肥沃如同性善,贫瘠如同性恶。农人对贫瘠之地“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教化可以化恶为善,进而使善者更善。“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祸也。” 但是,在不同的篇章中,王充所说的命又有两种含义。“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气寿》)王充把这二者的差别,称之为禄命和寿命的差别。后者即强弱寿夭之命,又等同于生命意义上的性,即本性。由此,他分辨了两种命运的不同。贵贱贫富之命,同际遇偶适相关,而生死寿夭之命,同禀气薄厚、体质强羸相关。在这一意义上,王充称:“禀得坚彊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彊,坚彊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命义》)这种禀赋之性,实际就是生命之“生”。所以,王充所说的人性,有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两个方面。在王充看来,善恶不仅来自后天修炼,而且也与先天禀赋有关。“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率性》)所以,人性善恶,不独同后天教化相联系,而且同先天禀赋相联系。由此,王充特别看重“骨相”。 从春秋到秦汉,相术有着很大发展,以相貌取人,是古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面相和骨相学说。荀子曾经对相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然而,到了王充这里,由于他把人性善恶同先天禀赋联接起来,把性与命联接起来,所以他倡导相术,专门写有《骨相》。声称:“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在《命义》、《吉验》等篇中,类似论述相当多,说明王充是从内心推崇相术的。汉代有专门的“相工”,承担人才鉴别任务。王充对此深信不疑,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骨相》) 对于王充迷信相术,简单地批评其“比荀子的‘非相’说倒退了一大步”无济于事。应该认识到,这种对相术的推崇,恰恰反映了当时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应方法。在缺乏人才测评科学方法的古代,使用相术实属正常。与王充同时代的王符,尽管富有批判精神,但关于面相、骨相也十分赞赏,称其为“贤人之所察,纪往以知来,而著为宪则”(《潜夫论·相列》)。相比之下,西方一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时期,笔迹学和颅相学依然是人事管理的基本方法,说明其具有普遍性。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对这种方法给出符合当时情境的评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