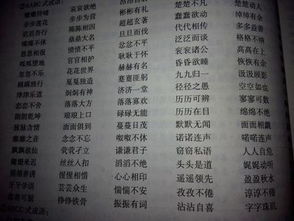采访者 珍妮·麦克克鲁齐 莫娜·辛普森 翻译 梁彦 克林顿是个只有三千居民的小镇,艾丽丝·门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黄昏将至的时候,我们停在了门罗家门口,门罗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雷林就住在这里。后院很深,有个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门罗解释说,她丈夫弗雷林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艾丽丝·门罗在厨房里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飘散着当地调料的香味儿。饭厅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书;而在其中一侧,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是一台旧式打字机。这就是门罗写作的地方。 门罗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还是流露出某种敬畏和不安全感—那是你在刚开始写小说的人身上才会看到的。她全然没有某些著名作家的炫耀或者自夸,很容易让你忘掉她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谈到自己的作品,她倒不完全是说自己的写作非常容易,而是说写得好有某种可能性,好像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得到。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受了感染,觉着写得好是有某种可能性的。她的风格看似简单—但那是种完美的简单,是需要花上好几年、反复打磨才能够掌握的。正如辛西娅·奥兹克曾说的,“她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在女儿们睡午觉时写作 采访者:你最早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是什么时候? 门罗: 《致命殴打》发表于1977年,那是我在《纽约客》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不过,我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作品,都曾寄给过《纽约客》。之后,我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把稿子寄给加拿大的杂志。《纽约客》曾给我寄过很客气的便条—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短信。他们从来不署名,也不会极度鼓励你。我还记得其中一张,写着:文字非常好,不过主题过于老套。确实是。那个故事写的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罗曼史—老农场主向一名老处女求婚,而她明白这正是她想要的。我的故事里有很多老处女。小说的名字叫做《紫苑花盛开的那一天》,写得很糟。那还不是我17岁时的作品,我当时已经25岁了。我疑惑为什么我会写老处女的故事。我其实不认识什么老处女。 采访者:而且,你很年轻就结婚了,也不像是你在预测自己的老处女生活。 门罗: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 采访者:你上了两年大学,马上就结婚了? 门罗:我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立即就结婚了。我20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结婚是件大事—还有搬家,也是个巨大的冒险。在加拿大境内,我们搬到了力所能及最远的地方。我们俩一个只有20岁,另一个22岁。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考虑买个房子,生孩子,而我们也很快做到了这些。我21岁时就有了老大。 采访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一直在写作? 门罗: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每次我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采访者:那在你女儿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你什么时候写作呢? 门罗:她们睡午觉的时候。 “我希望身后不只留下些零碎的故事” 采访者:你的《乞丐女仆》里的故事都有内在的联系。 门罗:我不想过多地预测一些事情,不过,我经常想写另一个系列故事。在我的新书《公开的秘密》里面,有些人物会重复出现。《破坏者》里的碧·多德在《搬离》当中提到过,是个小姑娘。《搬离》是我为这本集子写出的第一个故事。比利·多德是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在《太空船降落了》这个故事当中提到过他们两个。不过,我决不能够让这类的写作结构压倒故事本身。如果我为了适应一个故事,而开始去修改另一个故事,那我可能正在犯错误,在不应该的地方费工夫。所以,尽管我很喜欢这主意,却不知道是否会再写这类的系列故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一封信里说过一段话,噢,我希望写出一部小说,我希望我身后不只是留下些零碎的故事。如果这辈子只留下些零星的短篇,你心里就很难摆脱那种微不足道的感觉。我肯定你会说起契诃夫什么的,可还是遗憾啊。 采访者:而且,契诃夫总是想写成一部小说。他要把它称为《我朋友们的生活》。 门罗:我知道。而且,我理解那种感觉,其实你是能够做到把所有的素材放进一个大容器里的。 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深感不安 采访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吗?是否有作品对你产生影响? 门罗:30岁之前,阅读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书里面。美国南部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让我感动的作家,他们向我展示你可以描述小镇,描述乡下人,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过,有意思的是,连我自己都没太意识到,我真正热爱的美国南部小说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欢福克纳。我热爱阿多拉·威尔蒂、佛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还有卡森·麦卡勒斯。她们让我觉得女性也可以写奇特的边缘化的东西。 采访者:这也是你一直在写的东西。 门罗:是的。我逐渐认识到这是女人的领域,而关于现实生活主流的大部头小说是男性的领域。我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被排挤到边缘。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边缘社会长大的。我感到自己不具备伟大作家身上的某些东西,不过,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些什么。我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作品的时候,觉得极度不安。我总是对作家有关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采访者:你怎么看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门罗:我的确非常喜欢《百年孤独》。我爱这本书,但它无法模仿。它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当读到蚂蚁搬走婴儿、处女升入天空、族里的长老去世、天上飘下花瓣雨的情景时,真是精彩。不过,正如这本书一样难以写就,也如这本书一样完美的是威廉·麦克斯维尔的《再见,明天见》,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条狗。他让一个原本老套的题材变得光彩夺目。 采访者:你写作的自信心如何?经过这么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么变化? 门罗:对于写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这其中又夹杂担心,担心这种自信是完全错误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自信源自于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文学的主流那么远,我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一名作家,对底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你连个真正读书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认为还写得不错,你当然觉得自己确实有罕见的天赋。 采访者: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你可称得上是个高手了。你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还是由于特定的环境? 门罗: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因为环境使然;不过,后来,就是一种选择了。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主要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我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这被解读成害怕交际。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采访者:所以你对于置身主流之外感到高兴? 门罗:这可能正是我想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无法作为一个作家很好地幸存下来。在一群比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当中,我很可能会失去自信。他们经常高谈阔论,而且在信心方面都公认的比我更有底气。不过,话说回来,对作家,这也很难说—谁是自信的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