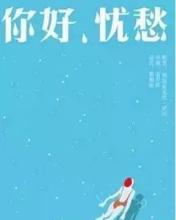继续推进改革
着手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
《第一财经日报》:就是说,我们首先承认1994年分税制改革达到了目标,而且确实是成功的,第二步是认识到还有未完成的财税改革。对于这点,人们提出不少建议,比如需要建立一个横向以及纵向的制度化的、实质性的税收制度,可预期的、透明的制度。我看到你在横向角度有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事实上也得以在实践中推进。能不能给我们做一点介绍?
许善达:最近几年税收的实际工作中凸现一个问题。财政部有一个统计,按照目标各省的收入统计,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大概是在3:1,东部是3、中西部是1。中央财政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税收返还,然后再有一般收入性转移支付,再有专项转移支付。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这三块的比重分别是多大?
许善达:最大的是税收返还,第二是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收入性转移支付比重相对比较少。实际统计发现,税收返还没有解决差距。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它的作用是零。
那么,重点就是后两种办法。通过后两种办法,差距从3倍降到了1.8倍左右。这是我们现在实际统计的数字。对这个数字,应该说社会不太满意,认为1.8倍仍然很大。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原来的3倍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在工作中和一些调查证明,这个3倍的差距,不是税源的差距。
这里需要说说陕西省的一位副省长赵正永,当时我到陕西去的时候,他提出这个问题:陕西省有很多税源,但这个税都没有给我们,而是让别人收去了。在我和赵正永副省长的主持下,我主管的国税局科研所和陕西省的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联合,以陕西作为一个典型进行了调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调查放到全国去,又找了二十几个省来做同样的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你们的测算,税源的差距大约有多大?
许善达:我们没有全国范围的数据,但从一些典型案例来看,我相信不会超过2倍。
《第一财经日报》:可以下降30%多?
许善达:可以缩小这么一大块。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税制有一个缺陷,而我们对税收缺陷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我们在研究税收制度的时候,只考虑怎么计算税基、税率是多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纳税,纳税人是谁。每次税法都有这样详细的规定。但是我们的制度里缺了一个要素,就是收入应该归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公司纳税人在什么地方就把税交给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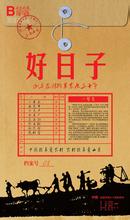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许善达:简单,而且过去矛盾也不突出。随着经济发展,大公司越来越多,税源分布在很多地区,但是交税在一个地方交。
这种现象就是,分布在一个地方的税源产生的税收被另一个地方收去了。
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我们的调查中,这样的材料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原来说过很多次,像西气东输,营业税是按照运输量、运输里程来计算,几千公里的营业税都在企业注册地缴纳,沿途那么多省都得不到税收。但是他们要其提供资源、服务。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研究证明,占整个收入92%的税收,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现象,即一个地方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被另外一个地方收取了。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有所有改进呢?
许善达:有两方面改进,一是,我们采取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三峡电站。三峡电站发电是在宜昌,但是水库淹没的面积主要在重庆。在国务院的主持下,三峡电站发电的增值税直接在重庆和湖北之间分配。当时曾有人主张,中央从宜昌征收,再转移给重庆。但这个设想,重庆不同意。后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接受这个意见,不要再经过中央转移,而是直接分配。
类似这样的个案比较少。国家税务总局也处理过一起,比如发电输电,到最后售给用电户不同的环节,增值税怎么分配。过去,发电环节的税收很少,大量的税收都在后面,交给后面环节(所在)的地方。可是,售电都是在城市里,发电可能在边远地方。所以,在当时政策允许的空间里,提高了发电环节给当地交的税,减少了售电环节交的税收。
《第一财经日报》:但个案对于解决整体问题还不够。
许善达:不是还不够,是很不够。 这个矛盾原来是通过个案解决。这次在《企业所得税法》通过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取得了一个非常实质性的突破。在立法过程中,主要是国务院提交人大审议,全国人大作出决议。
虽然这个法是人大通过的,但全国人大要求,关于企业所得在地方间分配的问题,国务院要制定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一个要求,必须这样做。《企业所得税法》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个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总公司汇总分公司交的税,拿出一半,再在分公司所在地进行分配,而且分配的时候,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谈判式,而是根据分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量、销售收入和工资总额等因素。
这个政策应该说还是很有限的。首先,很多企业没有纳入这个政策范围。但是,我觉得纳入一部分也是不得了的。其次,纳入这一部分也有不足,它只分50%,还有50%没有分。但这也是突破。
这标志着什么呢?就是税源所在地要求获得该项税收,这得到了立法机关的支持,而且已经变成了现实。
我觉得这个意义太大了。虽然它现在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而且在操作上有很多问题,但在中国可以说是税制建设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税源地有权获得它产生的税收。将来有关单位要按这个原则兑现它的税收。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税制建设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实质性的突破,解决了过去税制里一个重大的缺陷。
未完成的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未完成的改革还有哪些方向?
许善达:一个是支出责任和财力的关系。这个现在有很多还处在一种非规范的方式。
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渠道太多。我记得1993年,财政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本打算)一次性改革中央、地方的关系,同时改革财政和各个部的关系。
当时研究认为,不应该一次性做那么多事。先解决中央、地方的关系。所以,当时就把重点放在分税制上。各个部委相对基层分配的财力没有解决。而且,现在这部分膨胀得越来越大。
所以,中央、地方的关系首先要整体化,不能分散到这么多个部门。例如,财政部为某一个项目安排多少资金,然后业务部门又安排多少资金,这两次安排没有协调、没有衔接。这对资金的利用效率是有损害的。
因此,将来我们应该把预算制度覆盖到所有部门,中央、地方的分配关系,不仅要包括财政系统的分配关系,也要包括各个系统分配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一个大的制度改革,是急需的。先搞清楚了这个制度,再研究哪些是你的职责,按这个职责应该有多少资金,资金通过什么渠道支付。
如果财力这么分散,后面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前提是要先把预算覆盖到所有方面,然后再来统筹研究中央、地方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新的制度建设。如果只研究一部分,制度搞了以后效果是不够理想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