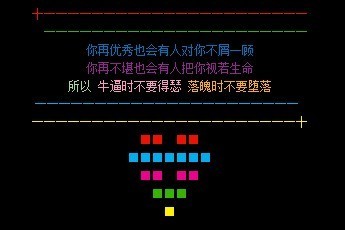章汝奭先生家是简朴的两居室,室外有一个小院,几株青竹引人幽思,顿有“大隐隐于市”之境。章汝奭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床,泡茶、读书、写经。他用蝇头小楷写的佛经,清雅而别具一格。 章家祖上是大家。章汝奭的祖父曾经入选太医,后来告老还乡,是苏州四大名医之一,章太炎是他的小堂弟。章汝奭的父亲章佩乙曾中苏州府长洲县第一名秀才(“案首”,即第一名进学),20岁出头就是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的主笔,后来参加国民议会,在北京做过财政部次长兼泉币司司长。章汝奭回忆:“我父亲救过徐树铮的命。他们那时候全都是反对张勋复辟的。张勋在北京对我父亲还是很器重的,管他叫小老弟。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我父亲是结拜弟兄。张勋要复辟,李思浩就反对,不给钱。同时,徐树铮也是极力反对的,那么,张勋必欲除掉这两个人而后快。我父亲知道了,就去向张勋求情,他一进去就给张勋下跪,说:我替那俩人求情,希望大帅还是放过他们。张勋说:我知道李思浩是你结拜弟兄,这就算了,我也不一定非要他给钱不可。徐树铮不行,此人非除掉不可。我父亲讪讪而退,徐树铮就藏在我们家里,他给徐树铮化个妆,那时候北京一共有三辆小汽车,我父亲有一辆小汽车,有特别通行证,自己陪着徐树铮一起到了天津租界六国饭店。徐树铮从袋子里掏出两张银行本票,他说:老弟,你少打两把麻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这两张银行本票多少钱?五十万大洋。” 章佩乙有了那笔钱以后,既不买房也不买地,就玩玩字画。那时候北京很多古代珍贵字画都散出来了。章佩乙花三千六百两银子买了王晋卿的《烟江叠嶂图》,此画有苏东坡题字,现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章佩乙收藏甚丰,还写得一手欧字,40岁才生了章汝奭,最喜欢这个排行第四的孩子,偶尔也教他写字读诗观赏古书画。章汝奭小时候喜欢赵孟頫,家里有一本旧的《寿春堂》,几乎翻破了。后来,父亲说:“赵孟頫有习气。你多学了他,会染上习气,终身难以摆脱,还是改学李北海的《云麾将军碑》。”章汝奭晚上做完功课总要写一两张字。而经史古文,则是他母亲特别聘请北京孔教学校教务长王君珮亲授的。 章汝奭早年过眼的名画无数,父亲的收藏后来在动乱时代中多已流散。香港收藏家、书画家黄君实收藏的钱舜举《锦灰堆》手卷,就是章父曾经收藏过的,后来专门请章汝奭题字。 章汝奭在北平接受良好的美国教会学校教育,中英文俱佳,一度立志在外交上有作为,后来觉得并不现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收了美国教会学校,章汝奭不愿当亡国奴,想到内地念书。母亲1942年在北平故世,他就到上海找父亲。“我父亲如夫人很多,有好几个。(我大哥二哥是原配生的。原配故世了,继配就是我母亲。所以我大哥二哥对我母亲还是很尊重的,她也对他们很好。)我到上海不久,去找我母亲结拜的小姐妹—我的干妈。我的干爹在重庆是实业家,有好几个厂。我干妈说:你的一切我包了,念书没问题。后来我就到重庆去。但是跟人家拿钱总不大方便,而且我这个干妈也是如夫人,当然大夫人也故世了,但是经济权掌握在她那几个大儿子手里。他们也肯给她面子,要什么钱尽管和他们要。但我总觉得跟人家拿钱不大舒服,后来交不上饭费了,大二的时候我就不念了。” 章汝奭本来考上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退学后去考飞机场的美军翻译。后来转到交通部的战事运输管理局。 章汝奭18岁在成都空运物资接转处负责管机场卡车,曾经揭发当时主管贪污。抗战胜利后,章汝奭回到北平,1946年底,海关招考,北平考区2000多人报名,录取6人,章汝奭考上了。后来,章汝奭被派到上海海关,1949年重逢了他小学同学的妹妹,这一年,他23岁,她19岁,情定终身。 章汝奭26岁时生了开放性肺结核,妻子变卖家里所有东西救他,半年后治愈。后章汝奭被派到外贸公司,亲历了一场场运动,他说:“反正那几十年就是折腾。”“文革”时,他下放到梅山十年,当炊事员。下放结束后,上级要调他回外贸公司。他说:“你砍我头,我也不去了。我又没有犯一点毛病,你们这样对待我。”后来外贸学院复校,章汝奭1979年就到学院教外贸实务和市场调研。 在上海外贸学院,章汝奭1981年评讲师,1985年评副教授,1990年评正教授,1992年领国务院特殊津贴,带研究生。其间专业译著九本书,并首先用英语讲授专业课。国际营销学是他和北外贸的罗真耑、上海的黄燕三人率先引进的学科,后来还开了广告学的课。章汝奭用英文写的教材曾经在联合国的世界贸易中心演示。 一生的工作都与经济相关,章汝奭却淡泊名利,以写书法求学问为乐。时代流行卖字,章汝奭的书法起初全是送人,“《金刚经》五千多字,我送了一百多通。到现在还有送人,老朋友要,我就送。但是大老板要,对不起,就是这个价钱,不要算了,我还不求你。我脾气很怪,人家说高官要字,对不起,我不写。我也没有求你什么,何苦呢?人要讲究气格。”他的书法各体皆精,尤以蝇头小楷名世,他说:“字要讲功力,讲气格,讲韵味。” 临行时,我问:“您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吗?”章汝奭淡淡一笑:“我也谈不上什么隐,我就是小小老百姓,我就有这么点臭脾气,我和他们合不来,我信奉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他们飞黄腾达,我心甘情愿身居斗室,过我自己的穷日子。” 书法应依托于古文之上 时代周报:“文革”十年,你在乡下干什么? 章汝奭:“文化大革命”,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把我给揪出来,又批又斗,又打又抄家又劳动改造。放到梅山十年,当炊事员,每天淘八百斤米,那我就看书写写字吧。 时代周报:看书写字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断? 章汝奭:一直。我年轻的时候,字写得还不错,从海关支援外贸公司,人家全夸我毛笔字写得好,这个找我写把扇子,那个找我写把扇子,如此而已。我平时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写字?早上六点多钟就从家里走了,到晚上十点钟甚至于赶上末班车回到家里。我很少待在家里吃晚饭,结果还落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 时代周报:“文革”时反而看书、写字多? 章汝奭:多。我后来到梅山,除了淘米烧饭,剩下来没事了。我老伴心脏病很严重,在上海养病,她说:你看看书,写写字吧。那我就看看书、写写字。也没有写字台,一个小方凳,上海叫骨牌凳,小方凳上头铺一块板,我自己再打一个小矮凳,只能写小楷。老天爷照顾我,给我一副好眼睛。 时代周报:启功先生说他的字是大字报体,“文革”被人家逼着天天写大字报。当然是开玩笑了。法学家江平在“文革”时也是天天写大字报,把书法练出来了。 章汝奭:人总要有所抒发。老实讲,中国的文化传承是多方面的,我不觉得废除文言文是一大功绩。五四的旗帜是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反得怎么样?我认为是不彻底的,首先日本的罪行没有很好地清算。第二,什么叫封建?我小时候念《三字经》里有六个字“夏传子,家天下”,封建主义开始,试问现在这个封建反掉了多少? 时代周报:你对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章汝奭:我认为古文有不可磨灭、特别了不起的好处,短文字写大文章,言简意赅,可以高度概括。白话文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当然也了不起。现在,洋人研究拜伦、狄更斯的古典文学还少吗?但我们有多少人在研究《离骚》?研究两汉乃至唐宋文?何况古人著书,有些传说也不一定完全对,这要靠后人很好地分析、理解,比方说《滕王阁序》非常有名的句子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前面全是铺叙,全是讲景致,讲缘由,为什么做《滕王阁序》?主旨是“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旨意高远,远远不是辞藻的堆砌,精彩是在后头。 时代周报:我们看古人的书法,有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文章,比如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章汝奭:对啊,这是了不起的好文章。三百多字,他把人事、世事的动荡无常说得感慨万千、淋漓尽致。王羲之是书圣,但是王羲之的字也有参差,不是所有的字全是那么好。跌宕起伏变化那么大,还是有高低的,所以古人的这些论断很值得我们去分析、考虑。 时代周报:在书法与古文之间,你认为书法要依托在古文之上? 章汝奭: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光写字的话是写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一定要把古文读通。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我认为这十篇文章是至文。我这篇八九百字的文章,把这些事情全概括在里面,我的一生也有所述的。我觉得做人一辈子,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回过头来看看,也不过是一瞬。现在回忆梅山岁月十年,1970年到1979年,也只是一瞬,过去了。我现在剩这身老骨头,要好好珍惜它,要回报这个社会。我信佛,我写了三百通《金刚经》,成品,写坏的不算里头,写坏的比写成的多。错一个字就是大不敬了。 董其昌的《琵琶行》值得传世吗? 时代周报:为什么信佛? 章汝奭:我觉得人对宇宙间的事情了解太少,如果没有冥冥中的安排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巧合——在我身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巧合。比如我跟我老伴,小时候我九岁,她五岁,我到她家去玩就碰到她。我十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在上海病了,我从北平临时停学赶到上海来看母亲,因为很危险了。后来我竟然在街上碰到我岳母,又联系上了——本来已经断了来往了。 时代周报:你觉得冥冥之中有天意? 章汝奭:有天意。老实讲,我觉得做人一辈子不可以有败笔。所以,我认为人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事情刀斧加身不可为。“文化大革命”胡说八道,那不行的,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打死你也是这么回事。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常常说知识分子要讲究气节,砍头不要紧,气节不能糟蹋。 时代周报:但是在近百年的时局动荡当中,老百姓的生活往往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 章汝奭:对。人生就这么一段时间,看你怎么对待它。有人说,这个人有了钱、有了地位了,就功成名就了,我说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人要有所追求,追求道德、文章上达到更高的境界,比方说我喜欢写字,我就要追求写字怎样有突破古人之处。 时代周报:古人之中,你喜欢哪几家? 章汝奭:有的东西视久愈无穷尽,可是有些东西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说董其昌,当然他有个别的精品,有个别行草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有些东西实在是不像话。首先他不尊重古人,自以为了不起。沈鹏编的《草书名帖精华》里收了董其昌的《琵琶行》,其中有六大错误。怎么编的?这种东西值得传世吗?他还自鸣得意。 时代周报:我特别喜欢苏东坡。文章之外,书法看起来也非常舒服。 章汝奭:对。但是我以为“件件精品,则无精品”,不是所有的都是精的。《黄州寒食诗帖》是特别好,前小后大,前头很严谨,后头很豪放。“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几个字一下子放大,说明他的心情,尽管身处苦境,还是很洒脱。两赋也是在黄州做的啊。 时代周报:黄州是苏东坡人生艺术里面鼎盛的时期,虽然是最不得意的时候,前后《赤壁赋》是千古名篇。 章汝奭:对,当时最苦啊。前后《赤壁赋》是了不起,而且,现在好像句读都是错的。如“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错的,这个句读不对,应该是“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你细读就觉得这才是对的。所以我说既然读书,怎么样读通?苏东坡很多诗文有点禅意在里头。苏东坡是远远高于李白的,对吧? “书法自娱”的想法不对 时代周报:近代的书法家里面,你觉得谁特别突出? 章汝奭:翁同龢比较好。清代写颜字的人不少,刘墉是写颜字的,但他只是加了一点机巧在里头。钱南园是写颜字的,写得太死板了。何绍基也是写颜字的,但是有习气。 时代周报:后世学何绍基的人比较多,散文家董桥也说他小时候学的是何绍基。 章汝奭:对,像新加坡的潘受就是学何绍基。比较起来,翁同龢的字就要比他们的格调高。所以字要讲格调,气格。 时代周报:清末民初以后呢? 章汝奭:有一个人叫何隽,名不见经传,很了不起,我看见过他写的小楷。我看了以后觉得不只是清雅,耐人寻味,真是美不胜收,了不起。我在小楷上探讨,也走过很多路,在大字上也是探讨过,走过很多路。我到这个年纪了,几乎每天都写,我却经常否定自己。 时代周报:百年书家里,于右任和沈尹默非常有名。你怎么看他们的作品? 章汝奭:于右任好,沈尹默不行。沈尹默堂庑小,气格不高,字写不大,只是秀而已,陈独秀说他“字外无字”,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古人说,不一定名气大就好。赵孟頫是宋代宗室,投降了元朝,而且成了元朝的宠臣,一品大员,皇帝算是喜欢了,认为他的字美,甚至是到清朝康雍乾全都是对赵孟頫顶礼膜拜,这里面有政治原因。宋宗室投降元朝,满族入主中原,汉人也应该这样。赵孟頫就是气格不够,骨子里俗。 时代周报:不喜欢赵孟頫的人,说他的字里面有媚骨,但字的确写得漂亮。 章汝奭:对,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赵孟頫,最早的时候写字就学赵孟頫,那是漂亮。但是就禁不住细看。我父亲给我一个赵孟頫的真迹,了不起,《玉台新咏序》!那是精得不得了,后来荡然无存。 时代周报:我非常喜欢弘一法师的字,觉得他不食烟火气。 章汝奭:这当之无愧。但是作为书法来说,究竟是一种变体,所以他的字不可学,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字应该说是了无俗韵,不食烟火,可以给人宁静的感觉。 时代周报:耶鲁有张充和,她的小字很清雅。 章汝奭:张充和是很雅的,但是实际上究竟就是那一块小天地,对不对? 时代周报:白谦慎是不是跟你学过? 章汝奭:是啊。有些人追求书法的境界不对。白谦慎一直把我当老师的,最近《东方早报》采访他,他说书法主要是自娱。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时代周报:为什么呢? 章汝奭:这是把书法意义贬低了,只是玩玩的,你以为玩玩随便啊。人家杜甫写诗说:诗是吾家事。写诗也好,练字也好,是感情的抒发。有人以为所谓功成名就是钱也有了,权力也有了,地位也高了,以为这就是功成名就。人不应该这样,人应该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学问也好,艺术也好,就是要达到更高的境界。而且你重视的不应该是怎样一个结果,应该重视的是那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古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 时代周报:书法在你生命中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 章汝奭:非常自然的一种东西。我晚上八点钟就睡了,凌晨两三点就起来了。我每天写很多经。佛事功课。这张是清朝的旧纸,写这几行觉得不好,裁掉,写得不好,裁掉。裁掉只剩这点,我一直在算纸还够不够,总算还够。这么小,写5104个字,一字不错,一字不漏。我全是目测的,没有格子,天地行距全是目测的。我这里头一行一行,没有说一行歪了,嫁接过去。人家说心正所以笔正。最近还有人发现说:章老的大字也非常了不起啊。人写字怎么会不写大字?他说是我的蝇头小楷不得了,当然他们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手一点不抖,我戴上五百度的老花镜,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给朋友写的一个匾叫“隻眼堂”,一只眼看世界,用孟子的“只眼能辨秋毫之微”,只眼见诸相非相,这是佛经里的话。拿浓浓的金字写,写得很漂亮,他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跟人家两样,我写得好的才送给人,写得不好经常自己扯掉。 时代周报:古人用书法吟诗唱和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章汝奭:但是我跟现在这帮名流显然是不合拍的。 时代周报:苏东坡也说自己一辈子不合时宜。 章汝奭:对。我看得很清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这钱花掉了才是我的。花不完,留着这些破纸在那干什么。我是晚年了,身体又不好,多少种毛病,我一天要吃十几种药。抗血凝的,心脏有好几种药,心脏换过瓣膜,搭过桥,装过支架,我心肌梗塞加心衰,我还有糖尿病,还有前列腺等等这些病,加起来十几种药。 时代周报:写书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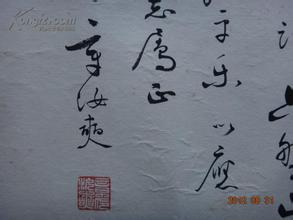
章汝奭:我觉得有好处,至少凝神静气,全抛开就好,早上点一炷香,写经。 时代周报:这其实也是锻炼自己的身心。 章汝奭:这是对呼吸有好处。我写了三百多通的经文,经已经很熟了。 时代周报:书法还是要讲究传统。中国还有一个文人字的传统。以前复旦大学有一些教授写的字,像朱东润先生,王蘧常先生,他们当然是以学问为主,但平时写的书法很有意思。 章汝奭:王蘧常小章草,小字好,大字不好,像描出来一样,板板的,没意思。小行书,小章草,写封信或者写个题跋,确实很好。朱东润的字很好,行书很不错,可惜流传得太少了。 时代周报:像沈从文,写小说、做学问很好,写章草也很好。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业余写的字,画的画也都很有味道。你觉得自己是文人字还是书家? 章汝奭:我不是什么书家,我也不要当什么书家,我就是这么个人,我觉得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做学问,我在书法上有所追求,追求更高的境界。我的小字,人家细看,说:你这是二王的。对,我是有二王的气势,我既有他们的挺拔,还有恣肆纵放的地方,再小我也有大气象。我觉得我是突破古人的。文徵明82岁写出《归去来兮辞》,没有多高,400多字,十九行。我这5000多字是直的,一行200多字。我老师说: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我岁数活得比较长,老天给我时间了。至少这方面,我可以对古人说:你们没有达到的,我达到了。我既有秀润,又有娴雅,又有挺拔,又有纵放,还有恣肆。我的小字还是规矩严谨得很,点画上没有一点交代不清楚的地方,那就是我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古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