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星期二发布了张五常教授的《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一文。此文就是我在《大师的魅力永远惊喜》中预告过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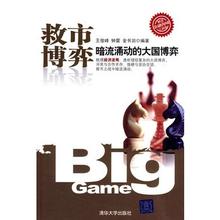
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湛深难明,没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并对张五常教授的理论有深入认识的,其实不容易真的看懂。因此,本期的“博客讨论室”提示此文中的一些理论要点,以供各位参考。
1、Fisher的方程式
这里说的Fisher(国内译作“费雪”,教授习惯译作“费沙”)的方程式不是指货币数量论里的那条费雪方程式,是指利息理论中的那条方程式,即教授文章里说的: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
无独有偶,此前有朋友在MSN上问过我这条方程式,当时我事忙,没有答他,这里顺便作答。
《经济解释》卷二第一章第三节《收入与财富》就是解释这条Fisher的方程式的。收入是未来一连串的流量,折现为一个现值就是财富,使用的折现率就是利率。通常来说,未来收入年年不同,期限也不是无穷的,无法预期,不能成为个人争取最大化的对象。而如果把所有未来收入折现加总之后得到的财富乘以利率,就能得到一个年年固定、且期限无穷的收入,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年金收入”。因此,Fisher方程式中所说的“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严格来说,里面的“收入”是指“年金收入”。事实上,学过计算折现值的公式(《财务管理》一类的课程中一定会介绍这类公式)的朋友就知道,这是一般的折现值公式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于计算英国一种年年利息相等、期限无穷的国债(Consol)的价格。
2、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及其与Fisher方程式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永久收入”与“永久消费”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消费函数,以此批驳凯恩斯的消费函数。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把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认为收入增加,消费随之以较小的比例(那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但弗里德曼指出,现期收入由两部分组成: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是一个随机变量(即无法预期、意料之外的收入或负收入),因此现期收入也是一个随机变量。同样地,现期消费也由两部分组成:永久性消费与暂时性消费,暂时性消费也是一个随机变量,因此现期消费也是随机变量。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随机变量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暂时性收入与暂时性消费没有关系,现期收入与现期消费也没有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的收入与消费,本质上是现期收入与现期消费,说它们之间有函数关系,其胡说八道,显而易见。只有永久性收入与永久性消费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
永久性收入,是将未来的收入以不同的权重(根据未来距现在的时间之长短来确定,时距越长,比重越小;时距越短,比重越大)计算出来的一个加权平均数。同理,永久性消费,也是将未来的消费以不同的权重计算出来的一个加权平均数。
话说,对于弗老这个消费函数理论,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认识与理解的不断深化。
最初,我第一次在本科一年级从《宏观经济学》的课本上读到弗里德曼的这个理论时,当年的我也很无知(当然那时的老师恐怕也不是真的很懂,教得不好),于是自以为是地觉得弗老这个消费函数只不过是比凯恩斯的弄得更复杂些,不如凯恩斯的简单、直观、易懂。
然后,多年之后,在我算是真正有点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之后再来看弗老的这条消费函数,大为拜服。我不由得想,弗老为什么能想得出这些东西来?我认为这跟他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是个统计学家的出身有关。无论是把现期收入(消费)分解为确定的(统计性质为函数变量的)永久性收入(消费)与不确定的(统计性质为随机变量的)暂时性收入(消费),还是把永久性收入(消费)理解为未来收入(消费)的加权平均数,统计学思维的影响深远都清晰可见。
最后,是去年四月份在西安交大听了张五常教授的课,他在讲解Fisher的利息理论时指出,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其实是来自Fisher的利息理论,永久性收入就是Fisher那个方程式中的(年金)收入,将未来收入进行加权平均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未来收入折现为现值的过程。(具体分析请看《西安交大听课记(之一)》。)
3、凯恩斯学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宏观派)之谬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朋友就能看出来,张五常教授那篇文章里说的“宏观派”就是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理论逻辑简述如下:
国民收入的决定公式是Y=C+I+G+NX,C是消费支出,I是投资支出,G是政府支出,NX是净出口(即外国人对本国商品的支出),支出就是需求,因此这个公式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总需求函数。前三项是国内需求,所谓的内需是也;最后一项是外国需求,即所谓的外需。经济衰退时,由于预期不佳,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都不振,外国也经济衰退,构成外需的NX也不振,凯恩斯就主张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支出就由政府来支出,即增加G是也。增加了G,直接增加Y(以GDP来量度)。与此同时,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Y与C有关系,Y增加了会使C增加,于是这条公式中的C也增加了。C的增加又再引起Y的增加,Y的增加又通过消费函数的作用使C增加,C又使Y增加……如此循环无穷,最终的效果是引起Y以数倍于G最初的增加数量而增加。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
所以,我们看到,凯恩斯玩的这整个魔术里,关键就在于他的那个消费函数。
然而,从前面介绍的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我们就知道,这个魔术是玩不转的。因为政府增加G,不是年年增加的,只是暂时性的增加(如那四万亿,只增加两年),所以它只能增加Y中暂时性收入那一部分,不能增加永久性收入的部分。而暂时性收入无论是与暂时性消费还是现期消费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们都是随机变量),它的增加并不能增加(现期)消费。所谓的乘数效应的链条,就这么一下子给割断了。
而如果政府年年增加G,虽然确实是增加了永久性收入,但有两个问题。其一,是教授文章里说的,“如果这宏观派之法不断继续,最终的效果是「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二,政府增加G,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都有挤出效应。政府支出的钱,还不就来自于你我纳税人?永久性地增加G,就要永久性地加税,一来一回,实际上还是没能使消费者的永久性收入增加,而考虑到政府支出效率之低下,同样的钱由消费者来支出肯定比由政府来支出更能增加国民收入,这是对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然后,政府增加G,还挤占了稀缺的资源,拉高了生产要素的成本,降低生产者的投资回报,更加不利于经济复苏,这是对投资支出的挤出效应。
当然,直接增加G是可以直接增加Y(在GDP上直接看到数字在增加)。但一来这个是GDP的数字游戏。人所共知,政府支出怎么可能比私人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有效率?浪费的支出能增加GDP的数字,但真的能增加一国财富吗?更不要说,在上述的挤出效应的影响之下,很可能G是增加了,C和I却减少得更多,最终来说,Y其实还是减少了。
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增加内需来提振经济,增加G(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使短期有点小效,其不良影响也不小,长期则更是弊大于利。
结论是:要人们增加消费,一定要增加他们的永久性收入,从而使他们根据消费函数来增加其永久性消费。而永久性收入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站在今天的人们预期未来收入,当然他们的预期就成了关键。所以,能有效地改变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经济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地增加人们的永久性收入,从而增加其永久性消费,进而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复苏。
4、“流动性陷阱”之谬,兼论“货币派”之高风险
张五常教授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第二派“货币派”是货币学派的观点,即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压低利率,从而稳定人们对财富的预期。
根据前述Fisher的方程式,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当收入因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大跌时,如果利率不能跟着大跌、甚至跌得更大,财富会随之而大跌。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逻辑,是要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使利率下跌得至少比收入的下跌一样的多,以便保障人们的财富不减。
但是,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是失效的。
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是指通常来说扩张性货币政策不断增加货币供给,使利率下降,降低生产者投资的成本而刺激其增加投资支出,也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消费的成本而刺激其消费支出,从而通过上述的国民收入的决定公式使国民收入增加。但在经济萧条时,利率已经降到很低(例如到了零利率的水平),再怎么增加货币供给,利率都降无可降,上述增加国民收入的链条不起作用,货币政策失效。
流动性陷阱的概念是有问题的。首先,利率有下限(不可能低于零),因此会有货币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无法再压低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这近乎是套套逻辑。还不如问,为什么在利率降低至零之前,扩张性货币政策都刺激不动经济,以至于货币政策要用到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极端范围中去?
其次,观之现实,所谓零利率是不存在的。现在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近于零,但那个利率不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而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影响(借贷)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是贷款利率,而不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如张五常教授的文章里指出,现在美国那个贷款利率仍高达6厘,没法降得下去。可见,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把这个货款利率压下去,并不是因为它已经低到无法再低的零利率水平,而是因为贷款利率的高低,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资金供需所决定的纯利率,一部分是弥补违约风险的风险贴水(可以用交易费用来量度)。而在经济萧条时,由于人们的悲观预期与确实存在的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现实,使违约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使这部分的利率不可能降到零,实际上反而比平时经济景气时升得更高。
再次,货币政策失效不一定是因为利率降不下去,而是货币供给无法顺理地转化成有效的资金供需。(按:以下的分析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流动性陷阱”作为一种现象是存在的,但凯恩斯的解释不对,有关的概念需要修正。)这也跟悲观的预期有关。消费者对前景感到悲观时,不肯增加消费支出,即使因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他手头的钱(货币)增加,他不会用于消费,而只会存进银行去(存粮防饥是也)。生产者对前景感到悲观时,也不肯增加投资支出,于是不会向银行借钱,这样银行有钱也贷不出去。而银行也对前景感到悲观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即有人来借也不敢把钱贷出去。这样一来,央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放出去的货币,全都堆积在银行里睡大觉,根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不进入流通领域的钱,其实不是钱,不构成有效的货币供应量,对经济活动毫无作用。
学过《宏观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中关于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原理的人都知道,货币乘数要起作用,央行发出的货币不断在地银行体系中通过借贷活动而周而复始地流转是关键。如果说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的魔术在于其消费函数与国民收入决定公式的互动所带来的乘数效应,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的魔术则在于商业银行的借贷活动使货币乘数发挥作用。但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想借钱,银行也不想贷款(惜贷)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借贷活动陷于停顿,货币乘数无法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货币政策失效。
其实,这实质上是由于货币乘数突然不起作用,于是经济体系中的M2不再是有效的货币供应量,有效的货币供应量遂突然从M2收缩为M0(货币乘数有效时,M0乘以货币乘数等于M2)——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信贷收缩”,这时央行要增加好多好多基础货币的供应量(M0)才能弥补这个巨大的缺口。在此之前,有效的货币供应量暴跌(从M2暴跌至M0),导致严重的通缩发生。
当然,这是很极端的情况,现在的情况还没那么夸张,不至于是货币乘数完全不发挥作用,而只是货币乘数大跌(银行的借贷活动只是大幅减少,但不是完全停顿),因此,即使M0急速增加,但由于货币乘数下跌得更快,于是M2仍然在减少。不过,这还不是最极端的情况,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人们即使直接拿到M0的货币也因悲观的预期而不肯消费、不肯投资,这些货币仍然进入不了流通领域,有效的货币供应量仍然不会因为M0的增加而增加。
当然,通常来说,如果央行强力地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例如直接代替商业银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借出去的钱有得还没得还,一律零利率地贷出去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去消费和投资——其实等于是送钱),有效的货币供应量还是能增加的(因为这钱既然是送的,总会有些人觉得不花白不花,于是就花了)。但是显然,这会使基础货币的供应量(M0)急剧膨胀,一旦货币政策竟然真的大功告成——成功地扭转了人们的悲观预期,使商业银行的借贷活动突然复苏,货币乘数突然再次发挥作用或大幅上升——这时叫做“信贷扩张”——,数倍于M0的M2突然再次成为有效的货币供应量,则经济体内的有效货币供应量会突然爆炸性狂增,之前严重的通缩就会突然变成严重的通胀。
这就是张五常教授的文章里说“如果货币政策能解决美国目前的困境——原则上是可以的——有过半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通胀急升,债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况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无光。”的情况了。
于是,成也萧何,败成萧何。在货币政策不生效之前,我们烧香拜佛祈求它赶快生效,好摆脱通缩,摆脱经济萧条。可一旦货币政策真的生效,其带来的严重通胀的后果,反噬之力之可怕,不下于突然炸了大坝放水而导致的洪水滔天。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能急速地紧缩银根回收货币,把有效的货币供应量压回到合适的水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教授的文章对“货币派”的评价是:“货币政策的困难是适度无方。”
5、“微观派”的实质:以鼓励内供来鼓励内需
前面第3点的最后总结到,提振经济的关键是改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增加他们的永久性收入。“宏观派”只能增加暂时性收入,实际上改变不了悲观的预期;而“货币派”原则上有机会改变人们的悲观预期,但后果很可怕,几乎可以说是“饮鸠止渴”。真正能改变悲观预期而又不会带来不良后果的,在教授的文章中的主张当然就是“微观派”了。
“微观派”的实质,其实是《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中的主张,即不是直接地想办法增加内需,而是通过想办法增加内供来间接地增加内需。而要增加内供,当然不是政府去增加供应,而是让企业去供应(其实就是刺激投资支出)。而能让企业去增加供应,一定是因为企业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被扭转了,觉得扩大生产有利可图。
一旦企业的悲观预期被扭转,它要生产,马上首先就要购买生产要素,一方面立即增加了就业,另一方面马上就增加了全部要素所有者(包括劳力所有者,即工人)的收入,使他们增加消费支出有了基础与前提。企业的生产使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这可是永久性而非暂时性的收入增加,因为企业只要一直经营下去,年年都有生产,年年都会购买要素,年年都提供收入给要素所有者,不会像国家的财政投资,今明两年投完了,后年还投不投那是天晓得,而如果一直投下去就等于以国家生产取代了企业的私人生产,计划经济重临矣。而当企业生产完毕,产品在市场上以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卖出之后,生产者自己有了收入,又可以去增加消费和投资了。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需求与供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是不对的。供给从一开始就在创造需求,结束的时候创造更多的需求,而且都是永久性的。而增加需求呢?正如前面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怎么才能增加啊?政府增加自己的需求容易,但效率甚差,而且只能增加私人的暂时性收入,但暂时性收入却是不会增加消费(需求)的,更不要说它还会通过挤出效应挤掉了私人的消费和投资。
另外,价格够低,需求总会有的。但要价格降低而企业还能生存,企业就要能够灵活地下调成本,否则辛苦生产一轮下来,产品是卖出去了,却不足以弥补成本,企业又怎么会增加供应?又怎么能扭转他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而最大的成本刚性,正是来自于工资刚性,所以拆掉工会、废除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之类,是灵活下调成本的关键。而且,这类造成工资刚性的所谓福利制度,是蚕食企业租值的,一旦清除,产品即使降价,企业也会因租值的增加而变得容易承受。
事实上,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认为一国有温和的通胀是一件好事,对经济有利。这种观点正是基于发达国家有工会之类造成的工资刚性而提出的。工资刚性是指名义工资的刚性(即名义工资很难下调,企业很难减薪)。但是如果有一点通胀,则可以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真实工资(因为真实工资等于名义工资除以物价水平,名义工资不变时,作为分母的物价水平的上升就可以使真实工资下降),从而使真实工资的水平较接近于、甚至等于市场竞争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也就有了减少、乃至消灭失业的效果。
由此我们进一步可以明白,为什么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通胀与失业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这条曲线只是一条根据经验数据而画出来的曲线,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一直并不是很清楚。但这里的分析可说是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有工会之类的福利制度之下,由于工资刚性,真实工资是高于竞争所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的,于是在劳力市场上供大于求,出现失业。(所有失业理论,都承认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工资刚性,不同之处只在于以不同理由解释何以会存在工资刚性。)我们之所以看到通胀率上升时,失业率会下降,无非是因为通胀造成的物价水平上涨把真实工资水平拉低到接近、甚至可能等于市场竞争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于是减少了失业。
当然,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变成一条垂直线,原因就在于当工会发现是通胀时,会要求把名义工资增加到追上通胀率,于是物价水平上升所带来的真实工资水平下降的效果消失,真实工资水平再次上升到高于市场竞争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劳力市场上的供大于求再次导致失业的增加。
结论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降低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工资刚性对企业应对经济波动的灵活性的妨碍,但效果也是短暂的。而且,如果经济只是轻微地下行,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只是轻微地下降,那只要制造轻微的通胀就能使实际工资随之轻微地下降到均衡工资水平上;但如果经济是明显地暴跌(经济危机是也),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也会跟着暴跌,那就要制造严重的通胀才能使实际工资也有相应大幅度的暴跌,否则实际工资严重偏离(大大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就会造成严重的失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为什么如果“货币派”一旦能起作用,后果将是严重的通胀——如果通胀不严重,就不足以有效地大幅度压低实际工资以减少失业。
最后,解释一下教授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先要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跌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这句话教授在紧接着的《经济学浅而不易》一文中作过解释,这里换另一个角度再作解释(是我个人的理解)。
实质财富(或实质收入)与名义财富(收入)的关系是后者除以物价水平等于前者。总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变动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在名义财富(收入)下降的时候,如果让物价水平下跌得一样的快,甚至更快,则实质财富(收入)不变,甚至反而会是上升的。
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这里的物价水平下跌并不是通缩,而是跌价。张五常教授以前有一篇名为《通缩与跌价不同》中已经解释过二者的区别。通缩是因为货币供应量收缩而导致的物价水平下降,而跌价是因为货币供应量收缩以外的其它因素导致物价普遍地下降(这些其它因素可能是因为整体经济实力的下降,整体供求关系的变化,等等)。这里是跌价不是通缩,因为这里不是由于使用了收缩性的货币政策而使物价水平下降,而是因为通过拆掉工会、废除最低工资和劳动法等而消除了工资刚性,从而使产品的价格能容易地随之下调。
联系到前面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搞通胀来使名义工资刚性维持的条件下仍能压低实际工资,从而减少失业。这里的“微观派”是通过拆掉工会之类的东西使名义工资刚性消失,名义工资能灵活地随经济衰退而下调至市场竞争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失业自然消失,所以这时是完全不必搞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由此也可见,这时的名义工资下调,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产品价格都可以灵活下调,其本质是跌价,不是通缩(因为没有使用过货币政策)。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