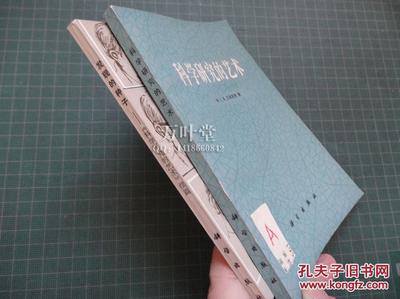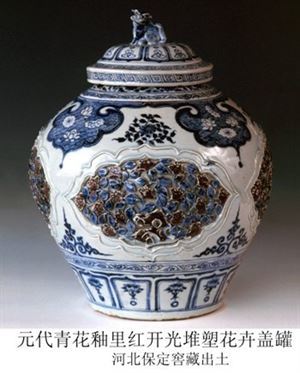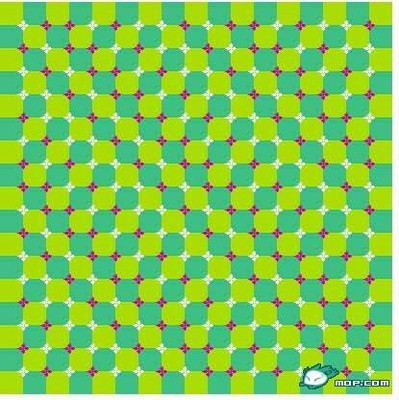脑是人类智慧的生理基础,是人体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其中的许多机理奥秘人类还不甚了解。现代心理学的知觉学习理论和解剖学对于意识、认知和脑功能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认知理论一般认为,认知主体的脑功能在于对外界信息材料的加工:感觉、再认、生成、意象、图式、概念、分类、假设、推理、对信息线索予以概率的权衡,以及由自己的反应所派生的心线索。但无论大脑怎样加工处理,事物始终被认为是由感观信息输入后,经由大脑思维的中介过程添加上去的东西。艾黎诺·J·吉布森在《知觉学习与发展的原理》一书中曾描述过认知过程的模式图(图1.1)[1]。

现代脑科学基于医学解剖学的发现,从脑功能的结构方面对人脑的工作原理及其内部机能做了解释。[2]但目前脑科学研究的困难在于进一步揭示人脑结构的功能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以及脑体内部组织的功能分工与协调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因此,从解剖学上讲,人们的大脑的生理结构、机制都是一样的。人们的大脑的不同只是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不同,这种不同犹如人们的个子的高矮、胖瘦一样。其实,大脑与计算机一样,计算机硬件的功能很少,计算机强大的功能是在大量“软件”的支持下而产生的。人的大脑“硬件”的功能是机械的,大脑的强大的功能也是在大量的软件(知识和信息)的有机支持下而产生的。正如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不可能找到他为什么能创立相对论。要研究他为什么能创立相对论,应该从他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对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去寻找答案。概括而言,如果大脑中没有任何知识和信息,那么大脑就不会拥有任何智慧。大脑的智慧与大脑中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要拥有智慧,就必须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不是源于大脑,而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发展过程和结果。智慧的源泉、创造发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大脑之内,而在大脑之外的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
现代脑科学和认知学习理论对于认知和意识的研究,是从人“脑进化的结果”这一角度来分析认知和意识形成的。在经济学关于制度演化分析的研究中,汪丁丁更为关注脑科学发展的动向,他希望通过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来探索人类理性产生的起源及其工作原理,从而在这一基础上解释理性和主体意识如何参与制度演化过程的事实。与汪丁丁不同,我在本文中的分析则侧重于从“脑进化的过程”来考察,意识和认知理性参与制度演化的过程。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制度演化的过程与人脑进化的过程是伴生的,二者无法截然分开,相反,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是彼此依赖的。关于大脑工作原理的解剖学分析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相反,在我看来,人脑与灵长目动物大脑在工作原理上的类似,不仅说明人脑进化是个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同时也说明解剖学对人脑研究只能提供大脑工作机理的解释,却无法提供人脑在生理学解释之外,区别于灵长目动物的认知进化的合理解释。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单独考察人脑进化在生理解剖学之外的可能因素,来对认知进化的过程给出解答。
图1.2关于人类的脑进化过程说明,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大脑的进化却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这一人脑进化的奇迹,从生物学的基因遗传和适应原则角度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现代解剖学困扰于无法找到古生物的活脑样本,来提供一个对比性的科学说明。 新近的实验心理学则比较侧重于对人与动物在心理、精神以及认知领域的比较来研究人脑的特征,但同样由于无法找到活的早期人种的脑样本只能提供对现代人脑智力水平的经验性解释。准确的说,关于脑进化的研究的可靠材料,只能通过对古生物化石、早期文明的考察发现,以及通过人类进化史的反思来寻求答案。
关于人类进化起源的问题,我在本章第二节曾经论述过斯密的猜测(注释13)。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之自利心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但若是如此,互助的社会何以可能?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餐桌上之所以有面包可吃,不是出自于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对私利的追求。市场经济这是立基于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满足的,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正是它操纵了市场的运转。因此,所谓的“斯密问题”的“斯密解释”或许是:社会所必需的利他行为(道德)其实正源于自利的动机,道德现象就这样转化成了经济学问题,于是,看似矛盾的利他行为和自利本性就这样得到了统一。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其实斯密对此问题是有所涉猎的,在他看来,交换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得以合作的基础就在于分工和交换现象的存在。哈伊姆·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对斯密关于“交换是人类进化的起源”的猜想做了详尽、精湛而又有说服力的展开。他 在近200万年的时间跨度上,探索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换行为对人类进化的影响。哈伊姆·奥菲克将经济学应用于生物学进化论的边界,并针对人类进化中的各种违反自然选择的独特问题做了详尽而有力的解释。他指出,在人类向灵长目动物的边走边吃战略告别,经过狩猎、采集和火的驯化,一直到定居农业的进化过程,跟不上是由“交换”的经济活动推动的。而商业交换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主要特征,也可能是人脑容量扩大和功能进化的主要外部推动力量。
哈伊姆·奥菲克指出,在我们解释人类进化问题时部分的忽略了经济学推理的应用。尽管早期人类距离我们是遥远而又神奇的,但经济学原理作为解释行为的科学探索并不是单为现代人创立的。在将经济原理应用于人类进化问题的分析时,认清两个总体趋势是有益的:脑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人脑尺寸的不断增大在解剖学上是最引人注目的进化趋势,就该器官的本质而言,其进化速度远远超过解剖学的发展。哈伊姆·奥菲克的分析,也让我们明确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经济学从根本上是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发展的学问,那么在人类进化史上所占据的生存环境的不断扩大和改善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应当给予注意的事实过程。真正需要科学家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建立必要的联系。[3]哈伊姆·奥菲克通过比较有机生物体在种群中“交换行为”发现,人类与其他物种在分享了“共生交换”[4]和“亲缘交换”[5]之外,还独特的使用了“商业交换”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竞争中的存续(第9-25页)。亲缘交换行为主要是依赖于情感和血缘的,但共生交换则是种的经验而非个体的经验,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自然选择所限定的资源转移,但不具备战略意义。共生交换和亲缘交换可能促进种群层面和种群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但不会促进种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分工。相反,促进物种内部个体分工的任务是通过同物种成员的交换完成的。奥菲克讨论了生物脑进化的最一般机制:硬性的刺激――反应机制,他称之为“自激式脑进化”(第37页)。奥菲克指出,“如果一个交易者略占上风,其他同物种成员就会效仿他。这一过程一旦被启动,进化循环就会自动的进行,并世代保持自我增强的趋势,直到达到一个种群意义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见得对所有交易者都是最佳的和必须的。其结果是在同物种内部的竞争中产生一种自我加强的竞赛过程。” 奥菲克指出,即使承认人脑产生于这种自激式进化或其他类似的过程,它就不代表自然选择过程中有过渡的设计,也不代表自然选择带有任何预见”。但事实似乎还不是这样。奥菲克进一步考察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分工与交换问题,他指出,我们在建立了人类进化与交换行为的联系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进一步说明人类的多样性的问题。他认为,斯密关于分工的思想在用于解释人类进化时很容易说明人类多样性产生的问题,但斯密分工理论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或许能解释实行专门化分工的动机,却无法解释得益于专门化训练的能力,即后天通过训练和专门化所获得到能力提升和进化变异。奥菲克指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商业交换与其他物种的交换方式存在本质的差别,它的运作原则是一种“互利的自私性”。在非人类社会中,在高于生物体层面或高于与生物体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层面,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发生的分工失败,都是由于缺乏某种协调和激励机制。 而在自然界的其他地方,在共同承担更大事业的成员的选择层面上,集体的收益被有效内在化的同时,个体却无法独立发展。相反,人类社会行为在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奇特机制,却恰好提供了这种协调和激励的功能,它在是群体层面的利益有效内部化的同时,促进了个体的发展和进化。[6]奥菲克在随后的分析中指出,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火的驯化以及交易空间在时空纬度上的扩展,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得到提升,这极大的促进了人脑的进化。由于人脑进化和分工与专业化带来的益处使得人类面临的资源稀缺问题和生存环境得到逐步改善,这使得在生存竞争之外派生出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需要在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对自然和外部环境的征服才可以满足。因此,由交换而启动的自激式进化,由于交换空间的扩大,导致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材料在数量和复杂程度上大大提高,而每一次认知进化导致的工具和技能的提升都会形成对大脑的解放,这种解放使得大脑可以进一步对更多的信息材料进行加工处理而形成新的知识。
哈伊姆·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中提供的人脑进化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研究制度演化中的“有意识演化”现象提供了进化起源上的认知论基础。根据奥菲克的“交换促进脑进化”的结论,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演化过程本身是伴随脑进化过程的一个共生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知水平的提升是制度进化在自然选择之外的重要动力。由商业交换促进的脑进化所提供的认知论依据,说明人类意识和思维理性的形成不仅来源于交易行为,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有意识的将理性应用于交易的动机。制度演化过程本身即使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理想参与的结果。脑进化到导致的认知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促进工具性技能的提升和分工与专业化的进步,同时脑进化导致的认知改进也会促使人类有意识的参与对行为“协调机制”的改进和创设,这恰恰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有意识演化”的体现。从制度对认知的反作用来看,特定的制度形态和结构都会形成时空纬度上的信息空间,从而形成新的信息材料和认知素材。大脑对特定制度结构的信息材料的认知加工,将导致认知超越制度的空间并形成改进制度和协调机制的更高水平的认知,这也是制度演化在自然力量之外的核心动力。
[1] 参:艾黎诺·J·吉布森,《知觉学习与发展的原理》(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2] 参:A.G.凯恩斯·史密斯,《心智的进化》(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
[3]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6页。
[4] 共生交换是资源和服务跨越物种的互惠和互利的转让,或称交换。主要是指兼顾各方的互利关系,而排除了只对一方有利的寄生形式。
[5] 亲缘交换则主要指物种在家庭成员内部的互惠援助行为,通常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作为边界。
[6] 同注释66,第67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