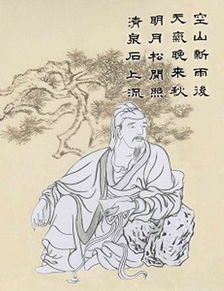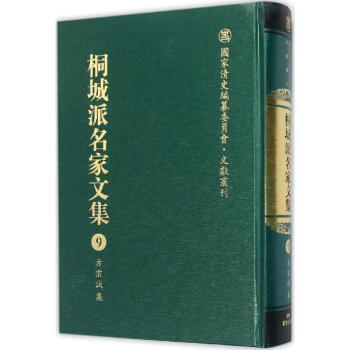像香港这么贫富不均,应该做再分配 时代周报:你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他算不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石元康: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契约的限制》(The Limits of Contract),副题是: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及意识形态的架构,是对罗尔斯的研究和批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但我不是很赞成他的想法。罗尔斯追溯的是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代表人物是卢梭、洛克、康德。康德不是那么明显地谈契约论,洛克和卢梭则非常明显谈契约。他反而不太愿意追溯霍布斯这个传统。我个人的看法,不光是20世纪,罗尔斯是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基得最深的哲学家。罗尔斯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比的,他复兴了政治哲学。19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来,政治哲学像百花齐放一样,非常茂盛。

《正义论》出版后,很多人批评他,有一批效益主义的人批评他,因为罗尔斯的理论就是要反驳效益主义。也有一批左派的人攻击他,说罗尔斯的理论出来以后造就一个阶级的社会。罗尔斯受到左右两边的攻击。有人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结果就搞出个福利社会,罗尔斯的哲学就是替福利社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我想这个讲法是蛮有道理的。 经济学家里面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海耶克,一个是弗里德曼,这两个人都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觉得国家应该是最低度的国家,该管的事情非常少,除非你伤害了人家,国家才可以管你,其他的事情国家都不应该管。罗尔斯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国家应该做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因为,像香港贫富不均到这个地步,不能完全让市场去运作,国家应该多管一点,去抽有钱人的税来再分配,比方说教育补贴、医药补贴、房屋补贴。罗尔斯的哲学为这个福利社会提供了一套哲学基础。 时代周报:你著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如何理清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 石元康:自由主义的理路是清楚的。我觉得自由主义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中立性。这是德沃金提出来的,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就叫《自由主义》,提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一个论旨是中立性。中立性就是政府对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应该保持中立,不应该参与到里面讲话。比方说:过一个基督教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儒家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无神论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是过一个快乐主义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生观,政府应该不能够强制人们接受。自由主义后面所依赖的基础是价值的主观主义或者价值的怀疑主义。 时代周报:痖弦先生认为,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所谓“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监视和批判的态度,因为政府有它的政府机器,有宣传的队伍,有笔杆子队伍,有写作班子,用不着文人在它香炉里再加一炉香。所以这个时候文人就要做一个“广义的左派”,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石元康:左、右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法,说赞成这个的就站左边,反对这个的就站右边。至于痖弦先生讲的,我想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持一个批判的态度,尤其对当权者应该持批判的态度。可是,我觉得右派的人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为什么右派的人不能持?比如说弗里德曼,他是非常有名的右派,对肯尼迪政府批评得很厉害。他很有名的书叫《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肯尼迪不是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就马上批评:肯尼迪对国家和个人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他说国家就是服务个人,我们才将它设立起来的,有什么理由说要我服务国家,我当然要问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持一些批判的态度是没有错的,这我完全赞成。 “我比较不赞成新儒家的传统” 时代周报:你跟牟宗三先生是什么关系? 石元康:牟先生是我的继父。 时代周报:因为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对新儒家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石元康:我对新儒家有些认识,新儒家中像刘述先、杜维明,我跟刘述先当然很熟了,在中文大学同事这么多年,杜维明当然也认识,虽然不是很熟。 时代周报:牟宗三先生在学术上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石元康:学术上基本不能说有什么影响,我不是新儒家。我的思想比较倾向社群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西方两个最大的思想家,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韦伯。韦伯跟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差不多,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不同的历史哲学。韦伯的历史哲学是唯心论,觉得观念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有新教伦理的讲法。马克思是唯物论,觉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觉得新儒家对于现代性不是有很深入的观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不管学社会学也好、历史也好,甚至科学也好,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我们国家怎么现代化的问题,或者我们的文化怎么现代化的问题。哲学就是把时代的精神把握在思想当中。中国任何知识分子所碰到的问题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方说,韦伯一辈子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去研究现代性是什么,他从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去研究。黑格尔、马克思也是研究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性。我曾经从政治、教育、伦理、经济各方面去了解西方的现代性。这方面西方人做的研究真是汗牛充栋,而且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学术上的深度。 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要实现现代化,到现在还不是很成功,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日本人很快就成功了?日本明治维新大概三十年后,到甲午战争已经是现代社会。为什么他们这么快,我们这么久?是不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些结构、要素跟现代性之间有冲突或者不相合的地方?当两个文化碰面时,会有一些什么哲学问题产生?中国人常常想把人家的好处拿过来,拿来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在中国是极有影响力的想法。当时严复就批评说:牛有牛体,马有马体,不能牛体马用。我觉得新儒家基本上还是这个传统,我比较不赞成这个传统。我觉得西方的现代性对于西方来讲也是一种革命,西方现代性把中世纪那套也抛弃掉了。中世纪政治上的传统也是专制政府,经济上也是庄园经济,宗教上的那套伦理学是反资本主义的。观察一下的话,欧洲的国家中,民主政治及资本主义在新教的国家大都实行得比较好,比如说美国、英国。韦伯这个论调不是没有道理的,新教是有一套革命性的东西。 在中国,新儒家的基本想法,从牟宗三先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中国可以保留那些传统核心的东西,然后把西方好的东西吸引进来。可是我就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把西方的民主传统吸收进来的话,中国的专制传统就没有了,怎么还能保持专制传统呢?西方这套现代性的东西进来了,我看不出来传统的东西还能保持多少东西,当然可以保持一些不是核心的东西,可是民主一人一票,这不是以前有的制度。 “我对现在这个社会充满悲观” 时代周报:新儒家能够解决人心灵的问题吗? 石元康:新儒家以前讲了儒家是“内圣外王”。有些人讲:“外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内圣”可以解决了。新儒家当然不会觉得只是“内圣”,也希望“外王”,因为“内圣”跟“外王”在中国传统是通的。 西方现在有两个思想的潮流,一个是社群主义,一个在伦理学上叫做Virtue ethics,就是德性伦理。麦金泰尔的一本书就叫做《德性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论儒家伦理的形态》,就用德性伦理的观念来讲儒家的伦理形态到底是怎么样,认为这是比较符合德性伦理的一个形态。麦金泰尔在那本书里把古代西方的传统伦理叫做德性的伦理,现代的伦理叫做规则性的伦理,就是规则性的道德。道德就是遵从规则。古代的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不是遵从规则,或者道德这个架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美德或者德性。我觉得新儒家的伦理是德性伦理的一个传统。 而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跟隔壁的人都不太认识,彼此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以前,西方的社会学家有一个名词叫面对面的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现在大家都是陌生人,在城市里面都互相不知道。陌生人之间就要定规则。当然不是说古代社会没有规则,古代社会对于规则不是那么重视。现在的社会道德是讲规则而不是讲德性。我认为新儒家即使是“内圣”这一面也不是很适合现代。我对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悲观。对现代社会了解很深入的人像韦伯和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社会很悲观,韦伯有一个有名的词语叫“铁笼”;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当然是更悲观,觉得现代社会里面过的生活是一种“异化”的生活。现代社会不太能够使人安身立命。 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听BBC的节目时,记者问一个教授:现在社会最大的毛病是什么?那位教授说:我觉得最大的毛病一个是Excessive inpidualism,过度的个人主义;一个是Excessive materialism,过度的唯物主义。住在社会里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人。过度的唯物主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价值都是物质性的,吃好的、穿好的。中国传统社会很强调的亲情,或者很强调对生命能够深入一点挖进去,现在不是那么讲究了。新儒家当然有一套很完整的使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可是,所谓规则的伦理跟德性的伦理,到底新儒家能不能够在现代社会里面适用,这是很难讲的问题。这不一定是新儒家的问题了,也可能是现代社会的问题。社群主义对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失望的。 时代周报:中国现在很多人把传统的东西重新拿出来,比如有人提倡国学,提倡传统,你怎么看? 石元康:我发现了,我想这总有它的好处。现代社会发展了,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是商业化。商业化把很多东西弄得很苍俗(苍白、俗套)。中国传统文化总有艺术优雅的一面。但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我想社会越来越富裕以后,总会希望比较优雅的东西。比方台湾人很讲究喝咖啡,讲究喝茶,这都是很好的东西。人总是要了解自己,中国传统核心的价值就是伦理的价值。 麦金泰尔曾经花很多力气讲相对主义的问题,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Who‘s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他说:一个文化传统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发掘。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其中他有一个概念叫做“典范”,大陆译做“范式”。典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像春秋战国出来一大堆东西,然后定一尊于儒家,汉武帝用政治力量把它捧到上面,就要制定新的法则、制度等。可是一个文化发展到某个地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尼克松时代,发生了水门事件,绝对是一个宪政危机。美国人就觉得他们的制度有一套自清机制,自己就会把它清理。 我受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很深,因此也对相对主义的问题下了一些功夫。库恩说一个典范如果弄了半天没有办法修补了,就产生科学革命。政治上、文化上也是一样。中国人以前的革命是改朝换代,汉朝革秦朝的命,汉朝的结构跟秦朝一样,汉承秦制。所以,黑格尔用一个名词叫非历史性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来描述中国历史,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结构的改变,比如台湾,蒋介石虽然不是皇帝,可是他也是专制,变成民主,这是结构的改变。以前是打天下打出来的,或者是禅让给儿子。现在台湾是选举,每人投票把马英九选出来,这才叫革命。政治上革命通常是暴力的,台湾还是运气不错的,没有什么流血,不像当年韩国光州杀了几百个学生。 一个文化如果出了问题,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个文化。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碰到外来的强势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种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解决问题。如果说原来的文化架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文化可以继续下去。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比方说隋唐时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佛教有些观念比如说没有父母,中国要受到这个挑战,假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它吸纳进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历史、思想史的题材。可是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碰到强势的文化,李鸿章才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了解现代性、了解自己,了解相对主义,文化碰撞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国学的复兴,还是自我了解的必要步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