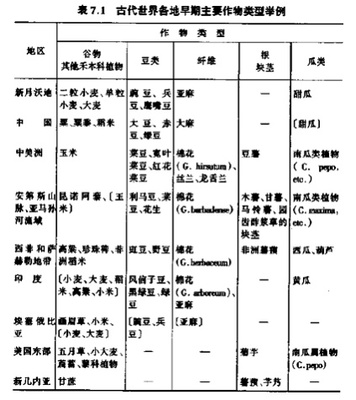1793年,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并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同一年,法国革命者砍掉了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英国人将这条信息不怀好意地通报给了中国人。或许,正是出于对“大革命”的恐惧,迫使中国的“旧制度”维护者设计出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并深远影响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国运。 1793年9月11日,43岁的中国首相和珅,在热河行宫会见56岁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见英国特使,此前和珅已经与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见了一面。 除了客套之外,和珅向马戛尔尼询问了一些有关欧洲局势的问题。当谈及印度时,马戛尔尼说,印度有一些富豪与几个“欧洲大国”勾结,频频叛乱反对英国,这些欧洲强国的野心不仅是控制印度王公们,而且也想左右中国皇帝的政府。 法国当代学者佩雷非特在其著作《停滞的帝国》中认为,马戛尔尼的“话里充满了攻击法国的弦外之音”。此时,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并且已经砍下了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法国革命者难道不会把‘对暴君的仇恨’带到中国吗?马戛尔尼在背着东印度公司教他的话。英国不是殖民主义者,都是那些该死的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他避免点名字)迫使英国不得不把它那些很小的货栈扩大成一个帝国。” 而细致的英国人还注意到,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传承到了第四代。斯当东在他执笔的使团官方记录(中译本名为《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四代连续相传长达149年,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人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参照物:“在欧洲,法兰西王朝的最后四代共183年,但最后、同时也是不错的一个君主不得善终。”——大革命中的法国,被英国人当作了观察中国的一面镜子。 一个幽灵,法兰西大革命的幽灵,在乾隆朝的大清帝国游荡,并且始终笼罩着中国龙与英国狮的第一次对视。 中国首相 在马戛尔尼看来,与和珅的会谈是愉快的。在他的日记中,对和珅的第一印象就是英俊。斯当东后来告诉他,这天的和珅,与前几天接见斯当东时简直判若两人,变得十分“坦白和蔼”。而上次,因为对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安排有不同意见,和珅与斯当东之间有点小小的不愉快。这次,和珅主动表示,考虑到使团远道而来,又携带了珍贵的礼品,礼仪上可灵活处理。 显然,在这次会谈后,英国人相当欣赏这位中国首相——可惜的事,双方都没有详细记录下所谈的内容细节。斯当东在使团官方记录中写道: “和中堂(Ho-choong-taung)的见解相当尖锐深刻,拥有完美的政治家的品质。他的飞跃上升,固然是由于皇帝的特别提拔,这种情况在许多帝国是相同的,但他同时也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长期保得住这个崇高的职位。” 在上一次见面时,斯当东就已经很清楚和珅的重要地位: “在(热河)皇宫里面,和中堂只占据一个很小的屋子。无论多么掌权的大臣,他在唯我独尊的皇帝面前,就变成一个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了。在这样广阔壮丽的行宫里面,他只占据着一间小屋子。和中堂是一位鞑靼人,据说出身低微,二十年前只是皇帝的侍卫之一。皇帝见他像貌不凡,后来又试出他才具过人,于是不次提拔擢至首相。他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 “出身如此低微,而很快擢升到这样高位,这在等级分明讲究班次的国家看来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这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办得到:一是君主可以任意升降百官,不受任何限制;一是在动乱时代,出色的人可以脱颖而出。在第一种情形下,过去的历史经常出现皇帝把大权委给一个宠信大臣,自己一心贪图安逸享乐。但中国现在的皇帝却不是如此。一切国家大事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只是分权给大臣,而不是把国家大权整个委托给大臣。” 在这次与马戛尔尼的会谈中,和珅似乎对欧洲局势相当关注。马戛尔尼的日记记载,和珅问他英国与俄国相距多远、两国是否友邦?马戛尔尼回答了两国之间的距离,并说,除了对土耳其问题有些不同看法外,英俄之间关系良好。和珅又问: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英国的属国,如同越南是中国的属国一样?马戛尔尼回答说:意、葡并非英国属国,但是,英国国王基于友谊给这两个国家提供保护。他向和珅再三强调,英国国王非常热爱和平与正义——马戛尔尼这样说,并非泛泛而谈,在和珅边上坐着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之一福康安,就坚定地认为英国人正在煽动西藏的叛乱,而在中国朝廷颇有影响力的葡萄牙传教士们,则不怀好意地强化了这种说法——尽管葡萄牙与英国在欧洲是亲密盟友,但在东方,他们却不愿意看到英国人前来争夺他们盘里的葡萄。 没有任何史料足以佐证,和珅关于欧洲的谈话究竟是闲聊,还是有所针对。而英国使团则清晰地注意到了,中国官方对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十分警觉。 在这次与马戛尔尼的会谈中,和珅似乎对欧洲局势相当关注。 表面上在批中国,其实板子都是落在法国的政制上。 北京-凡尔赛 拿正在动荡的法国,观照正处于盛世的中国,虽然有点残酷,却的确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在尚未抵达中国时,英国使团就在途中得到了相关情报:针对法国大革命的顾虑和防范,可能会影响到大清帝国对英国使团的看法。 使团的官方记录说: “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北京王朝虽然还没有下令驱逐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的工匠和天文学者们在北京仍然受到欢迎,但他们同欧洲的通讯则受到严格的检查。事实上这些外国传教士们依靠外国教会汇寄一些款项来维持生活,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 到达中国之后,英国使团更是直接感觉到了中国对于大革命的顾虑: “自从英国人航海到中国海岸之后,种种误会和种种造谣污蔑使中国人对英国一直抱有成见。这些成见需要英国政府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来逐渐消除。除此而外,现在又加上英国人帮助尼泊尔进攻西藏的误会。使节团进入中国境内以后,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招待,但中国方面,尤其是鞑靼族的大官,处处流露出怀疑和猜忌。这些鞑靼人好像误解英国人到中国来的最终目的在于企图分享他们统治中国的一杯羹。还有一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其实,对于法国革命,英国人远比遥远的中国更为深恶痛绝。在登陆天津的最初几天,他们发现了:“把这些人(中国官员)的性格同欧洲人作一个比较,他们在以下方面非常相似革命以前的法国帝制政府高级官吏们:态度温和文雅,对人一见如故,谈话大方爽快而随时流露出自我称赞和对自己民族的优越感。”此类记载,处处都流露出对革命前法国人的认可。 的确,只有对法国革命极端敏感的英国人,才会从“第四代”的特殊角度,看到中国与法国在骨子里的某种相似之处。拿正在动荡的法国,观照正处于盛世的中国,虽然有点残酷,却的确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此时的大清帝国,自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定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手里,正好是第四代。在马戛尔尼到访的这年(1793年),这个政权已经存活了149年;而刚刚被推翻的法国王室,自亨利四世于1589年即位,掀开波旁王朝序幕,先后经历了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共四代君主,直到上一年(1792年)君主制被大革命彻底推翻。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6岁的顺治皇帝在太后及多尔衮的辅佐下进入北京城,而与他同岁的路易十四也在母后摄政下统治着法国。并且,他们都刚刚即位一年。与这位日后被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同行相比,顺治皇帝无论是在文治武功甚至寿命上,都差了很大一截。 当25岁的乾隆于1736年即位时,比他年长1岁的路易十五已经在法王的宝座上呆了21年,但是这位法国国王显然大大逊色于其中国同行,国运日衰,以至于他的孙子路易十六登基后,虽然是一位“不错的”君主,却也成了“最后的”君主,如同中国明代的崇祯皇帝一样,最后不仅没能挽救政权,甚至没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在英国人看来,大清帝国的四代皇帝,总体要比法国的四代国王强:“中国的这四代君王不但时间长,而且,虽然是贵族统治、内部还有一些分歧,但国势的兴隆是超越千古的。第一代由一个少数民族用自己的精力和努力奠定了新朝代,以后三代俱都智勇兼备奋发有为,尤其是当今皇帝的功业更是辉煌巨大。” “当今皇帝”、大清帝国第四代核心乾隆,对于发生在遥远法国的大革命,究竟有多少兴趣和了解,在中国官史和野史中似乎都毫无记载,以至于后人认为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帝王,此时已经闭目塞听。但是,英国人的记载显示,这位中国皇帝不仅清楚地知道法国发生的一切,而且对此充满了戒心,并抹去了这种戒心在中国史书上可能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 大清帝国从来都不“宅”,而是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与戒心,而至少在乾隆朝,法国成为最吸引大清帝国注意力的欧洲国家。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曾在私信中表示:乾隆皇帝“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在乾隆皇帝的库房里,“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所用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乾隆皇帝甚至还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巴黎,会见路易十六,作为对前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遣使访华的回访。而钱德明就是这个拟议中的大清使团的成员之一,他在家信中说:“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我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 中法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开始于更早的康熙年间。17世纪80年代,为了绘制航海图,法国派出科学家进行全球考察,而派往中国的,就是从法国耶稣会选出的“科学传教士”,他们既是传教士,又是科学家。这个传教团于1688年抵达北京,受到康熙的欢迎,此后又有更多的传教团前来,这彻底改变了此前葡萄牙传教士垄断中国传教领域的局面,大大推进了中国对法国的了解。据晚清时的法国传教士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统计,截至法国大革命,在一个多世纪里,来华的法籍神父为86人,而葡萄牙籍为79人。 经由传教士们的宣扬,18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其中,尤以法国为重。正处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决战前夜的法国,无论哪个阵营,都在努力从外部寻找着可以资治通鉴的镜子,而围绕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判断,法国的“公知”们发生了激烈争论。如,伏尔泰认为,中国历代君主崇尚孔子学说,中国的政制是最为优秀的,他甚至在读了乾隆的《盛京赋》后,大为感动,高喊“中国皇帝万岁”,将乾隆列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位哲学家和诗人君主之一”。而孟德斯鸠,则对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给予了毫不留情的痛批。 随着大革命临近,法国的思想界越来越激进,对中国特色的专制批判的力度也不断强化,表面上在批中国,其实板子都是落在法国的政制上。“中国热”在法国迅速退潮。 与“中国热”的退潮同步,大革命爆发后,法国势力在远东也迅速退潮。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注意到,法国革命切断了在华传教士的供给线,他们成为法兰西的弃儿,并因此而对反宗教的共和国持敌视态度。正因如此,尽管法国是英国的长期敌人,而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却被英国使团当作可以争取和信赖的盟友,甚至远比葡萄牙人可靠——尽管葡萄牙还是英国的小兄弟。 革命成了障碍 钱德明认为,法国革命令中国政府“害怕”,因此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 如果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其延续时间,不为革命所动摇和改变,那么在文明国家中理当首推中国。 星星之火 尽管英国使团是首次访华,但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大清帝国对于法国革命的防范,并非杞人忧天,中国这个民族实在很容易被革命所吸引。 使团的官方记录中对此有大段的精彩分析: “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据说,法国人提倡的关于民主原则和他们的《人权宣言》等文献被译成一种梵文在印度流传。这种学说在安静驯顺成性、体格脆弱的印度人中发生不了多大煽动作用。中国人性情好动,有进取心,这种学说假如传到中国,那就不同了。 “中国政府知道,平等的观念假如传至中国,在下等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一定得到信仰,因此极力预防它介绍过来。长久以来敬老的传统和老少聚居的习惯是中国的社会安宁的基础,一直维持到现在。老辈人的经验和慎重教导后辈人避走极端,避免不满和乖离举动;他们对新事物的怀疑,在后辈中树立起顺从命运的观念。应当听信老人言,加上家庭情感,在中国已经是先入为主。在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上,这种束缚力对于青年人比严刑峻法有效得多。” 使团第三号人物、“贡物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在他180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之行》(Travels in China,大陆中译本名为《我看乾隆盛世》)中,也深刻地指出: “像中国这样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在2000多年间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这在世界历史中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尽管中国人说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吹嘘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在公元前400年,他们已像今天一样,生活在同样的制度下,受制于同样的法律,被同样形式的朝廷统治。那时,他们那位大哲学家(指孔子)还在壮年时期,他的著作今天仍被尊奉为至理。这些著作的确包含了他们的朝廷赖以为基础的所有格言,包含了所有人们须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于当今的君主来说,他的国家可以说在2000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如果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其延续时间,不为革命所动摇和改变,那么在文明国家中理当首推中国。不管好坏与否,中国朝廷掌握了一门将其臣民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加以塑造的艺术,而且采取的方式是世界各国的编年史中所未有的……闭关自守,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任何往来,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巴罗也注意到,在中国,政府并不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他们既没有被禁止去拥抱自己选择的宗教,也没有被强迫去支持他们不赞同的信仰。”那么,朝廷维稳的着力点在哪里呢?“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局部的暴动骚乱时有发生,但通常是极端贫困引起的。在匮乏饥荒时节,民不聊生,他们被迫采取暴力这个唯一的方式来获得生活资料。这可以认为是他们史料中记载的几乎所有动乱的根源。” 巴罗认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想到过争取个人的权利: “托马斯·潘恩黄金般的思想无法翻译成中文,而那些不幸的中国人除自己的语言外,再不懂任何其他语言。3亿330万人口,注定要停留在愚昧和困苦中,因为他们的语言无法传达托马斯·潘恩的开明学说。” 巴罗认为,对欺压要奋起反抗的学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对于中国朝廷来说,则因此而对此毫无畏惧。 显然,只要他看看中国历史及当时中国朝廷对法式革命的戒备,就会知道自己错得太远了——揭竿而起的反抗,从来都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之一。 尽管担忧西方人带来革命星火的大清帝国,对英国人充满戒心,但还是给予了超高规格的接待——全程负责使团在华的费用,标准为在京期间每天1500两,在北京之外地方每天5000两。巴罗统计的结果是,中国官方在接待费用上至少开支51.9万两,约合如今1.038亿元人民币!与乾隆皇帝的大方相比,英国政府在马戛尔尼使团上的总开支,经决算之后,只有78522英镑,约合23.5万两,不及中国政府接待费的一半。而且,英国人的费用中,约1/4用于购买礼物。 尽管接待热情,对于英国人提出的通商、建交等要求,大清帝国却坚定地说不。这令马戛尔尼十分苦恼,在京苦苦等候,不愿离去,直到一位在华43年的老传教士改变了他的看法。 这位传教士来自法国,中文大名叫钱德明,自1750年来华,已经75岁,卧病在床。他在10月3日派人送给马戛尔尼这封劝诫信,6天后他就在北京逝世。 马戛尔尼在10月4日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封信。钱德明在信中首先解释了中国人对外国使团的一般看法: “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对于马戛尔尼未能完成通商建交等使命,钱德明提供了一个英国人此前没想到的理由:如果英国人能早些到达,“在中国政府接到欧洲巨变的麻烦消息之前到达,使团所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而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人都是无差别的狂人。”所谓的“欧洲巨变”,就是法国革命。钱德明认为,法国革命令中国政府“害怕”,因此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停滞的帝国》)。 但在他看来,马戛尔尼使团并非没有成果,毕竟已经给中国人留下了好印象,关键是不能急于求成,今后应保持英国国王与中国皇帝之间的通信联系,经常派人前来中国参加庆典等,这一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报偿。 对于钱德明的这番书面劝解,在斯当东执笔的使团官方记录中,却不仅隐去了他的名字,也否认了他的来信,仅仅说是“特使的一位私人朋友来访”: “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使节团虽然遭遇了暂时挫折困难,但确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已经对英国人发生了有利影响。英国人现在所受的压迫,将来总有解除的一天。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但等它对这个事物的新鲜感觉逐渐冲淡,习以为常之后,它未始不可以重新考虑加以采纳。特使既经来华,并谒见了皇帝,这已经争取到了在中国立足的初步。以后,仍由英王陛下通过商船时时以书信与中国皇帝联系,可以促成事业早日瓜熟蒂落。” 从钱德明所说,可以佐证,法国大革命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戒心。但是,马戛尔尼却并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导致其使命未能达成的关键因素,在他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中,他说:“未必彼等因厌恶法国革命,而忽然迁怒于与西方有关事务。”这之外,还有葡萄牙人的暗中破坏、中国人对英国人支持西藏叛乱的担忧以及广州地方官员的阻挠——他们害怕英国人去北京告御状,揭发他们在广州对外商的勒索。 (英国人所绘)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的场景。 中国会崩溃吗? 英国人看透了一个老大帝国的外强中干,而这个老大帝国则似乎也看透了法国大革命可能对自己产生的巨大破坏力。

钱德明的信,似乎大大宽慰了马戛尔尼,他在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说:“我坚信,我国的贸易将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 或许在这种好心情的推动下,马戛尔尼似乎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提议:中英联手抗法。两广总督长麟将这个提议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在答复的圣旨中,开头就说:“英吉利国远奏进贡,或因现与佛兰西(法国)人打仗吃亏,希冀天朝救助。”圣旨表明,乾隆为此还召集了宫廷中的3位西方传教士问询,他们说:“佛兰西与英咭利人因何打仗,我等实在不知详细。大皇帝统御万国,一视同仁。我等在京当差,久沐大皇帝恩,同覆载于海外小邦,无分厚薄,我等素有稔悉。”乾隆因此决定:“大皇帝于外夷无分厚薄,西洋各国自相争竞,断不因或有干求,即稍为偏向。”拒绝了英国人的结盟提议。(该份圣旨载《乾隆朝上谕档》第1592号,日期为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794年1月25日) 这个时期的马戛尔尼,更为关切的,是中国的命运。 这次历时半年多的访问,令他对大清帝国的底子大致有数,因此,他在1794年1月2日到7日的日记中陆续写道:如果中英发生冲突,英国非常容易摧毁中国的海上联系,并且可能在西藏边境制造麻烦,朝鲜也可能趁机摆脱与清朝的主属关系,台湾亦将与中国大陆分开;同时,由于外贸中断,中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靠外贸为生的人将面临饥饿,可能导致暴乱;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不会放过侵占中国领土的机会。中国的崩溃,不仅将导致整个亚洲的贸易变更,而且会使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相应的变化,列强将在中国到处寻求市场,英国将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中国的这种崩溃,完全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发生。 他写道: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对于这艘船上的“船长”,马戛尔尼则在1794年2月从澳门写给孟加拉国总督的信中评价道: “皇帝已达高龄,心血就衰,未能忽然谋新,而惮于改革。”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前,对中国的批判还是处于思想家们的思辨,那么,在英国人实地观察之后,天朝的光辉形象就彻底坍塌了。马戛尔尼说: “自从鞑靼人150年前进入中国以来,这个国家在一种削弱的管理状态下逐渐衰落,被内战和叛乱搅得混乱不堪,被几个无价值的竞争者争夺不已。” 巴罗则说: “他们在二千年前,当全欧洲相对而言可以说还未开化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跟他们目前所有的一样高的文明了。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任何方面有任何进展,在许多方面反而倒退。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 1793年,因此而在历史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英国人看透了一个老大帝国的外强中干,而这个老大帝国则似乎也看透了法国大革命可能对自己产生的巨大破坏力。 尽管没有确切的史料,足以证明法国大革命对乾隆的战略判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突然开始了全面的“严打”,目标针对白莲教。《剑桥晚清史》如此描述:“1793 年,政府意识到了叛乱迫在眉睫,下令调查整个中国中部的白莲教组织。对地方政府中掠夺成性的人来说,这证明是一次特许他们敲诈勒索的好机会,于是农村笼罩上了恐怖的统治。”(1794年清朝政府的逮捕行动几乎将白莲教的全部骨干一网打尽,但并没能有效阻止两年后的白莲教大暴动。编者注。) 或许,对于乾隆皇帝这位衰老的“船长”来说,正是因为清晰地嗅到了“大革命”气息,而开始了保卫“旧制度”的种种努力,并因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此后的中国历史轨迹,或许主要并非因为无知和颟顸的结果,居然可能是某种刻意做出的“顶层设计”的收获? 天知道!天知道?天知道……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