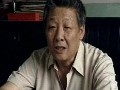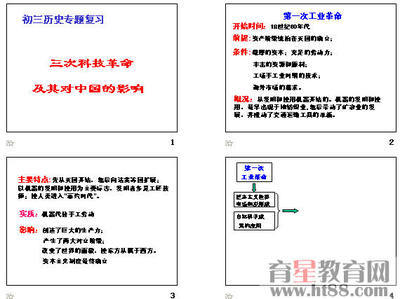七国财长会议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介绍 一、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发展更替 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主要有三个: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和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 1、六十年代的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协调十国集团[1]成员国应对国际债务危机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机制。当年,1962年OECD第三工作组(当时讨论政策协调和国际收支余额调整的主要论坛)成员国以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名义举行会议,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项特殊贷款。从此,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便固定下来。该机制央行行长机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单独的月度例会。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作用是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采取一致行动;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应付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货币危机。该机制最大的成就是制定了《借款总安排》,提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充足率并实行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各工业化国家除了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外,并没有进行大的国际协调活动,因此该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虽然这一机制至今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过于庞大也过于欧洲化,[2]终于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不能承担领导世界经济的重任而被五国财长机制取代。 2、七十年代的五国财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最初雏形是1973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白宫的图书馆会面,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协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谈判中的立场和步调。日本随后加入进来。意大利也曾出席过两次会议,但却没有成为正式成员。后来成员国央行行长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改革非正式决策机构,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后,在为首脑会议服务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会议召开前,一般由五国财政部副职先召开筹备会,为财长会议作准备。会议是不公开的,也不发表公报,直到1985年的广场会议,它才把决策内容告知于众。随即在1986年被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所代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3、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七国首脑会议要有更大的作为,议题不断增加,功能不断扩展,不可能再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于是,1986年5月举行的东京首脑会议决定建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作为成员国在货币与财金合作方面的主要协调方式。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于1986年9月首次聚会。该机制服务于七国首脑会议,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的核心体系。 二、七国集团关于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功能定位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明确了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职责,主要是:⑴及时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⑵促进各国经济低通胀增长;⑶促进市场导向的就业与生产投资;⑷推动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⑸促进汇率进一步稳定;⑹监督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与贸易余额、货币发行增长率、储备率和汇率等经济变量,如果发生偏差,应该拿出一致的补救措施。 三、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运行概况 七国集团的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75年首脑会议诞生到1985年以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五国财长会议,意大利有时参加;五国财长参加首脑会议,有时央行行长也参加,财长会议是不公开的,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atsummit)。1985年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走向公开后,在次年吸收意大利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单独召开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standalone),每年分上半年(lead-up)和下半年(follow-up)至少举行3次,从1998年开始又增加了首脑会议前的会晤(pre-summit)。总的来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挥了很大作用,是首脑会议之外最重要的协调机制。 1、发挥的作用。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作用可以主要地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领导作用。凭借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和在世界经济舞台拥有的强势话语权,影响和引导世界经济的走向,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第二,协调作用。就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交换看法,在经济增长与稳定、汇率问题、贸易逆差等领域协调各成员国的政策,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关系,努力使大家同意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谋求共赢局面。第三,监督作用。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具体负责执行七国集团关于对成员国经济政策相互监督的制度,监督检查成员国对相关协议的落实情况并且向首脑会议报告。第四,服务作用。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筹备首脑会议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聚在一起,就首脑会议经济领域的进行充分而细致的酝酿沟通。 2、存在的问题。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毕竟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众口难调,在运行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就进行的协调实践结果看,功过参半,既有富有成效的协调案例,[3]也有诸多无所作为和失误,比如对80年代后期日元的大幅贬值的放任,对日本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及90年代初对德国统一后财政赤字引发的欧洲货币联盟危机坐视不理,造成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继续延续了“滞胀”态势。[4]第二,就各成员国参与协调的目的来看,其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维护自身利益,各成员国特别是美国与德国、日本、法国之间的利益分歧较大,宏观经济理念和政策也存在差异,对如何合作问题上分歧较大,在许多领域和方面阻碍了达成协议。第三,各成员国特别是美国对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态度不稳定,并且受到领导人个人态度的很大影响,对重大经济问题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已经对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的有效运行造成周期性障碍。美国在七国集团中的支配作用是明显的,[5]当它愿意与至少一个成员国合作发挥支配作用时,协调就会取得明显效果;当它采取独立领导政策时,结果常常会令人失望;当它不愿意充当领导角色时,结果肯定收效甚微。[6]美国的态度虽然不是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有效运行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他不能一定促成协调成功但一定能左右协调失败。另外,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所谓互不指责的新共识以及面对世界经济出现的重大问题不作为的态度也使得它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作用有所下降。 3、面临的挑战。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不仅在运行中自身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要想进一步提高合作成效并在今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必须要努力适应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合法性和代表性要求。七国集团成立初衷极力坚持强调的限制会员数和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使得它在合法性和代表性上具有先天缺陷,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烙印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能否以及如何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是它能否成功应对新的挑战的关键。第二,塑造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的要求。战后70年代牙买加货币体系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国集团的协调与合作对于保障牙买加体系的稳定运行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冲击和风险急剧增加,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在塑造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能有多大作为,将是它是否还能充当领导世界经济角色的重要决定因素。第三,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新课题的要求。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竞争优势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引起了世界经济的深刻变化,也使得他们自己面临许多新的课题。比如随着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独立性而受到更大的限制,面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国内经济目标的压力大大增加;生产的国际化使得国际税收竞争复杂化;发达国家劳动人口比例下降造成的潜在社会保障基础压力等等。第四,运行机制改革的要求。不仅影响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国家数量在迅速增加,而且私人部门金融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封闭的、小范围的、仅限于政府之间合作的运行机制显然越来越不能反映这些现实,一个更开放、更宽泛的协调对话机制是必需的。 四、中国与七国集团关系回顾 从时间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七国(八国)集团的历史几乎同步。七国(八国)集团与中国的关系走过了一个从初期“各行其道”到互相关注、逐步了解、开始靠近和接触的过程。大致分二个阶段。 1、从各行其道到相互了解(1975-__1988)。G7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由于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不多,同时也缺乏参与己无自接关系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图,对国际事务几乎没有强大的公共说服力或者威胁,因此在G7领导人和部长的内部讨论中,在各种宣言中,极少直接提及中国。而当时,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致力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豪,外贸量也不大,基本处于西方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对西方是一件新事物,1979年的东京会议上,G7首脑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在对华贷款方面,保持利率的一致。但中国的实力毕竟有限,很难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事务。这一时期,中国与G7可以说是“来左去右,各行其道”,相互之间没有发生更多联系。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改变。 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增长,G7为应付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和地区性政治问题带来的挑战,必须加强同中国的协调。与中国有关的全球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地雷控制、核材料的扩散、导弹技术控制、中程核武器控制等方面。与中国有关的地区性安全事务包括印度尼西亚华人难民问题、柬埔寨和平问题、朝鲜半岛的稳定等等。198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G7第13次峰会上,与会国一致认为“应当给予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特别的关注”。这是G7正式表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G7一直对中国的改革持鼓励态度,中国也整体上维持了同其成员国的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此,双方的了解逐步加深。 2、干涉制裁与打破制裁(1989-1991)。1989年后,G7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7从总体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转变为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在许多内政上的立场和措施。在1989年的巴黎峰会上,G7发布了一份特殊的“中国声明”,谴责中国对要求获得自由和民主等“正当权利”的人实行暴力镇压,违反了人权,宣称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停止出售武器等制裁措施。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这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是G7第一次自接明确地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但却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一次“关照”。但这仅仅是相互交往的序幕。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增强与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与G7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当然,联系与交往也相应增多。 中国经济很快恢复,局势日趋稳定。西方的制裁对中国并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景象。在冷静分析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后,中国决心通过自己的发展和努力开始打破制裁。同时,G7内部对制裁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在1990年的休斯顿峰会上,虽然经加拿大首相马尔罗尼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再次提出,G7继续对中国 进行制裁,但也认识到中国在一些方面的重要性,因而(G7了支持一项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贷款计划。G7重新把中国当作伙伴,在经济宣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199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17次峰会G7讨论经济问题时,主席声明期待解决与中国经贸关系。同时,中国的经济成就(成功治理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实现“软着陆”)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成为大家赞扬的对象。G7声明也用较长的篇幅记载了这一事实。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G7急需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中国对制裁和打击伊拉克议案的支持。中国对伊拉克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违背国际法的现象进行了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并没有否决西方的行动。G7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作法心领神会,在1990年峰会的宣言中表示,欢迎“中国在反对伊拉克侵略以及另外地区性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并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并表示将视中国为处理全球安全事务负责任的联系对象国。不久,以美国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标志,中国基本上打破了西方的制裁。 3、双方加强合作,G7更加关注中国(1992---1997)。在1992年的慕尼黑峰会上,中国再次受到了G7的赞扬,这次是因为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武器控制体制。G7在主席发言中称赞中国的经济改革“鼓舞人心”,但同时也号召中国“加强努力,推进政治改革”,并且要求中国在人权方面做“显著的、更深的改进”,欢迎中国同意加入国际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防扩散条约,并且希望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更富建设性的角色”。 尽管1993年的东京宣言和1994年那不勒斯宣言没有提及中国,但在1995年峰会上,中国又成为注意的目标和赞扬的对象。宣言中关于中国的段落中对“中国在国际和地区性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 处理的积极参与”表示欢迎,希望中国除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应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他国际论坛,参与解决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期待香港在1997年能够实现和平交接,“以维持它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了建立更加繁荣和稳定的世界,七国分别与中国展开对话。在宣言的最后一段里,G7呼吁南中国海争端各方能按照国际惯例和平解决。在1996年里昂峰会上,G7与中国的联系集中在武器控制机制上。1997年的丹佛峰会标志着G7与中国的关系跃升了一个新的台阶。由于俄罗斯的部分参与,G7峰会变成了部分“G8”峰会。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发生在峰会后2周)。同时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丹佛峰会从两个方面处理了同中国的关系。它首先欢迎中国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之间达成的在边界加强相互信任,削减边界军事力量协议。它发表声明,称“这为区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G7从机制!建立同香港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在会议期间,它表达了致力于维持香港的政治自由的建议。对于香港的经济,G7提出,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繁荣和独立的金融和经济体制,维护香港的“金融和经济中心地位”有利于G7的长期利益。会议还提到,香港的基本自由框架和法律制度是未来香港经济成功的基本要素。在达成的最后文件中,各国对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的意见高度一致。中国与G7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 此时,俄罗斯己朝被全面接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媒体报道说, 日本对美国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会,并成为完全的伙伴十分愤怒,责问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参加峰会)。当然,也有一些成员国(包括东道国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没那么乐观,依然认为(G7不应该吸收中国。不主张吸收中国加入的成员国有一种担忧,中国是否会按照民主和自由贸易的规则参与世界体系。同样,G7成员国政府中也没有人主张“新集团”(俄罗斯包含在内的G8,去对付中国崛起对现存国家秩序造成的威胁。 4、从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开始,G8与中国加强合作(1998-一)。1997年7月,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了东南亚各国,随后席卷亚洲并波及全球,许多国家陷入恐慌,货币纷纷贬值。面对危机,以解决世界经济问题为己任的G8成员国各有打算,G8犹豫难产。中国不惜自我牺牲,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抵挡危机进一步蔓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金融危机为中国发挥潜力提供了机会,G7/G8与中国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从而凸显中国不但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成长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G8看到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合作精神和巨大潜力,对中国从此刮目相看。在中国不是G8正式成员国的情况卜,一些成员国多次主动向中国通报峰会的情况。1998年英国伯明翰举行的G8第24次会议上,G8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抗击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会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都对中国在抗击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G8己不只是关注中国,认识到需要中国加强自己。这以后,中国与其关系加快发展,有关G8应吸纳中国为成员国的呼声渐涨。 1999年,G8峰会东道国德国总理施罗德表示应该邀请中国加入G8。此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施罗德时,就科索沃问题和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事件全面阐述了中方的立场。施罗德代表德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 导弹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遗憾,并再次向事件中死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无条件的道歉。同时,施罗德作为当年首脑会议的主席国,向朱熔基介绍并解释了八国外长在波恩通过的声明。他强调,在发生了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后,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局势更加复杂了。目前,必须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舍此别无选择。他希望中国在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朱熔基表示中方已注意到了G8外长声明,中国一向主张科索沃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过程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会同意在轰炸继续进行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中国用鲜明的立场,表示了对G8绕过联合国武力打击南联盟、单独解决科索沃问题的不满。 2000年冲绳峰会前,关于中国加入G8的问题被炒作起来。正是从这时起,中国是否加入G8的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二向中国发出了入会邀请,希望借中国为峰会添彩。中国政府在2000年2月表态称,无意参加G8首脑会议及其相关活动。这有点出乎国际舆论的意料之外。在G7/G8历史上,只有它拒绝别国加入的事,从没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所以,中国婉言谢绝其邀请也成为当时的国际热门话题。 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应邀参加G8南北领导人会议,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有学者认为这一行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对欧洲推动多边主义机制的支持,是中国以其实力走向全球高层政经体制的开始。20作为新一代领导人务实外交的新成果,中国与G8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同时,中国在四次参加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副手会议后,于2004年10月1日参与了七国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对话。因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中国开始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正式接触,这究竟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无论怎样,都为中国与七国集团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2005年以前中国参加或出席的与G7有关的会议 时间地点会议 1999年4月14日华盛顿第一届金融稳定论坛 1999年9月15日巴黎第二届金融稳定论坛 1999年12月15-16日柏林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0年9月7-8日巴塞尔第四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0年10月24-25日蒙特利尔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1年3月22-23日华盛顿第五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1年9月6-7日伦敦第六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1年11月16-17日渥太华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2年3月25-26日香港第七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2年7月16-17日新德里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2年9月3-4日多伦多第八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3年3月3-4日坎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3年3月24-25日柏林第九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3年5月26日墨西哥主权债务重组高官会 2003年5月30日圣彼得堡圣彼得堡300周年庆典及八国首脑先期会 2003年6月1-3日埃维伊八国集团扩大对话会 2003年9月10日巴黎第十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3年9月20日迪拜七国财长副手会议 2003年9月24-25日伦敦20国集团财长副手会议 2003年10月26-27日蒙拉利亚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4年3月3-4日莱比锡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4年3月29-30日罗马第十一届金融稳定论坛 2004年4月23-24日华盛顿七国财长副手会 2004年10月1-3日华盛顿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 2004年10月法兰克福20国集团财长副手会议 2004年11月19-24日柏林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2005年2月4-5伦敦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 2005年3月14-15日重庆20国集团财长副手会 2005年6月伦敦八国首脑会议扩大对话会议 2005年9月大连20国集团财长副手会 2005年10月香河20国集团财长副手会 2005年10月15-16日香河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资料来源:G8ResearchGroupattheUniversityofToronto [1]十国集团是为了应对从1956年阿根廷开始的国际债务危机、维护美元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于1961年11月成立的,是一个非正式的官方机构,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成员组成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1984年加入,但是名称保持不变),目前发展到19个成员国,但是核心仍然是维护10国(实际上是11国)。由于其经常在巴黎克莱贝尔大街的马热斯蒂克旅馆聚会,因此也被称为巴黎俱乐部(ParisClub)。十国集团达成一项借款总安排(GBA),这样使得国际货币进组织在成员国因短期支付发生货币危机时可以从十国借入10亿美元的资金,贷给该国以维持该国货币稳定。这项安排于1962年10月生效。 [2]朱光耀唐臻怡:《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与对话经济政策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31页 [3]1985年9月五国财长就调整美元高估问题签署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意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卢浮宫协定》,以及80年代旨在救援金融和债务危机的贝壳计划、布雷迪计划等通常被认为是财长机制协调成功的典型案例。 [4]对于该机制的指责还有90年代援助墨西哥、俄罗斯金融危机方面的失策,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特别提款权的“公平”分配。 [5]Johnkirton,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andtheG8Summit,http://www.g7.utoronto.ca/ [6]钱国荣:《西方七国高峰会议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0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