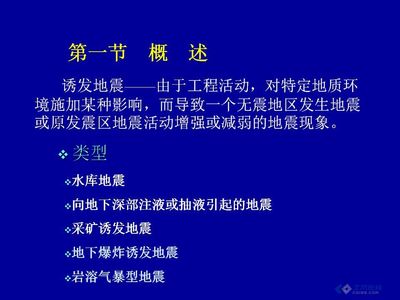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制药业的真相》新药比旧药好?还是不如旧药?令人担心的是,通常我们不知道答案。大多数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带有偏见的研究结果和夸夸其谈的广告。新的处方药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呢?你可能会说,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医生不会开这种药的。你还可能会说,医生根据经验知道哪种药有效,病人也是这样。但是有时候经验会非常误导人。如果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就认为该药物有效,那就忽略了病情本身可能发生各种变化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安慰剂效应(医生和病人都期望一种药物能够生效),也没有考虑到其他很多时候该药物可能是失效的,而且其他药物可能比这种药更加有效。这正是FDA要求对药物进行临床实验的原因。只有在很多人身上经过严格的测试,才能够知道到底哪种药物有效,药效到底如何。你可能会说,好吧,我会买的。我们知道药物是有效的,否则,FDA是不会批准它的。毕竟,如果制药公司不能通过临床实验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不能将新药上市。但是,我们能信任那些实验吗?即使药物研发的初级阶段是在别的地方进行的,但是最后的关键阶段一般是由制药公司赞助的。制药公司是否会操纵临床实验的结果以使其药物看上去比实际要好呢?是的。有好几种手段可以用来操纵实验,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叫醒服务aihuau.com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最近的、没有受制药公司赞助的实验。名字叫ALLHAT(抗高血压和降脂治疗预防心脏病实验),这是治疗高血压疾病的一项大型实验。尽管它从辉瑞公司得到了一些赞助,但主要赞助者仍是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分所。ALLHAT这项研究持续了八年,涉及600多个诊所的42 000多位患者,是关于高血压治疗所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它比较了四种药物:(1)钙离子阻断剂——辉瑞公司以Norvasc的名字来销售,是2002年全球第五大畅销药物;(2)乙型交感神经阻断剂(Alpha-Adrenergic Blocker)——辉瑞公司以Cardura的名字来销售,通用名药叫做多沙唑嗪(Doxazosin);(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阿斯利康公司以Zestril的名字,默克公司以Prinivil的名字销售,而通用名药叫做赖诺普利(Lisinopril);(4)一种在市场上超过50年的利尿剂(“水药丸”)。实验结果刊登在2002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几乎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的是,最老的利尿剂能够很好地降低血压,同时更好地预防高血压带来的严重并发症——通常是心脏病和中风。接受利尿剂治疗的患者比接受Norvasc的患者更不容易得心脏病,并且他们与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患者相比,也更不容易患心脏病、中风以及其他一些并发症。与Cardura相比的实验早早就结束了,因为很多服用Cardura的患者都患了心脏病。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主任明确地总结道:“ALLHAT表明,对治疗高血压来说,利尿剂是最好的药物,无论是从药效上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说。”

然而,这么多年来,新药早就替代了利尿剂作为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利尿剂没有被推广的原因在于通用名药厂商通常都不花钱进行营销,而新药上市时的推广力度非常大。例如,1996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做广告最多的是Norvasc,而利尿剂一则广告都没有。可以想见,利尿剂的使用量会直线下降。1982年,它占为高血压开出的处方药的56%,而十年后,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钙离子阻断剂上市之后,它在处方中仅占27%。总的说来,药物越新就越好卖。如果你观察一下2001年老年人最常用的50种药物,就会发现Norvasc名列第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有三种药物都进入了前50名,但是在ALLHAT实验中被证实更有效的利尿剂却榜上无名。再看一下成本。2002年,利尿剂一年的价格为37美元(基本上是市场最便宜的药物了),而Norvasc一年需要715美元,一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则需要230美元。因此使用Norvasc的高血压患者比使用利尿剂的患者多花费了19倍的价钱,换来的疗效却不比后者好,甚至还不如后者。健康方面的代价更高。高血压是一种很普遍的疾病——大约有2千4百万美国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如果ALLHAT实验的结果正确,那么就有很多人正在忍受并发症的折磨,而如果使用利尿剂的话,这些并发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像ALLHAT实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柯特·弗伯格(Curt Furberg)博士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浪费了很多的钱,而且现在的治疗还可能给病人带来伤害。”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新药实际上不如旧药呢?首先,没有人试图去寻找答案。制药公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新药和旧药直接作比较。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没有人知道新药与利尿剂或者其他几种药物相比较,会有什么结果。新药上市是因为服用它们比什么都不用的效果好,结果它们就被宣传成医药史上的伟大贡献。ALLHAT实验之后,制药业的辩护者声称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需要不只一种药物,因此新药确实非常重要。这种说法毫无诚意。制药公司开发和测试新的降血压药,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补充,而是作为最主要的治疗药物进行的。类似ALLHAT的实验十分罕见。国家卫生研究所通常并不进行药物的临床实验。它关注疾病的深层机理的基础研究,而将药物的测试工作留给制药公司进行。但有时候它也会做点例外的事情。ALLHAT实验开始于1994年,因为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在分属于7种类型的治疗高血压的100种药物中,哪种才是最好的,哪种应当用作首选药物。当然,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为这个问题画上句号。事实上,不久以后,澳大利亚有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将默克公司的Prinivil与利尿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Prinivil似乎疗效更好。但是,ALLHAT实验充当了叫醒服务的角色。可能大型制药公司宣称的“奇迹”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迹”。可能很多新药还不如旧药。除非我们直接将新药与旧药进行比较,否则无法知道真相。研究机构医生如何决定给他的病人开什么药呢?很不幸,许多医生是根据制药公司的营销重点来开药的。但是,大部分、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医生依据的是据说毫无偏见的研究报告。他们阅读医学杂志来了解新的研究;他们使用教科书来了解专家通过整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他们去参加会议、接受医药教育来从这些专家(所谓“思想领袖”)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后面两种途径其实是第一种的衍生。教科书和思想领袖的思想并不比他们以之为基础的证据高明多少。这些证据来自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因此,保证这些报告的公正、无偏见就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确公正、无偏见吗?越来越多的答案是“并非如此”。我曾经说过,大多数药物的临床研究都是由生产它们的制药公司赞助的。如果仅此而已,并不一定导致研究结果带有偏见。但是,现在制药公司对如何进行实验和如何报告结果有很强的控制力。这样情况就不同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一般独立于赞助他们的制药公司之外。制药公司一般将资金提供给学术医药中心,然后静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它们希望自己的产品有不错的实验结果,但是不能肯定是否果真如此,当然也不会告诉研究人员应当如何进行实验。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司参与到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研究的设计到数据的分析再到是否将研究结论发表,这种广泛参与大大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偏向性。控制临床实验的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赞助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自1980年以来,该行业的财富和影响力都与日俱增。当制药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更加以利润为导向的时候,制药公司再也不愿意坐等研究人员的结果了。首先,实验时间挤占了药物的专利时间;其次,坐等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研究结论可能对它们不利。因此,制药公司不再依赖学术中心进行测试,转而寻求那些新兴的营利性研究机构——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的合同研究组织。你可能还记得,这些公司在制药公司的示意下,与私人医生签订合约来搜集实验需要的患者数据。这些医生并不是经过训练的研究人员,因此他们只是按照被告知的要求来做——否则就可能失去与合同机构合作的赚钱机会;而合同研究组织只对大型制药公司负责。这也就意味着制药公司对实验几乎有了全部的控制权。学术医药中心对失去制药公司的合同很不开心——尽管这在它们的研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1990年,制药业赞助的实验中,大约有80%是在学术机构进行的,但是在十年之内,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到40%。随着病人医疗补助付款的减少以及财政对医疗教育支出的缩减,许多医学院和教学医院都出现了财政困难。这样,原来的一小部分收入也显得很重要。因此,它们开始配合制药公司这个赞助者,与合同研究组织展开竞争。当制药公司坚持临床实验必须如何进行的时候,它们几乎总能如愿以偿。此外,整个学术界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随着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的颁布,传统的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学术医药中心认为它们自己是制药业的“合伙人”。请看哈佛大学的一些学术—行业协议。哈佛的一所医院,达娜—法伯(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与诺华公司签订了合约,为诺华提供新发现的癌症药物。日本的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与哈佛的马萨诸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签订合约,十年内支付给医院1亿8千万美元,以便优先获得其皮肤科医生的研究发现。默克公司在哈佛医学院旁边修建了一所高达12层的研究机构。双方都希望达成多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尽管现在具体的合同条款还没有公开。美国医疗联盟(Partners HealthCare)包括哈佛医学院的两所教学医院,它邀请研究人员申请加入与千年制药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的“合作研究人员交换计划”。该计划保证,一旦加入了医疗联盟,“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将会被吸收到千年制药公司的项目组中。”哈佛并不是什么特例。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学术医药中心在赞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拥有股份。制药公司对医药学校十分慷慨。例如,在2003~2004年度的哈佛医学院院长报告中,赞助者名单包括很多大型制药公司。因此,按照制药公司的想法来进行临床实验是大环境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制药公司设计的临床实验由研究人员执行,研究人员只是个“执行工具”——不论实验是在学术中心还是在医生的诊所中进行的。提供赞助的公司掌握了数据和实验的核心,它们甚至不允许研究人员掌握全部信息。它们自己分析和解释结果,并且决定是否要发表出去。一项最新的学术政策调查中表明:“我们发现学术机构很难保证其研究人员能够全面地参与实验过程的设计、不受限制地获得实验数据以及自由地发表他们的研究结论。”这是对研究人员独立的公众形象的嘲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对赞助者的妥协程度不同,但是通常,它们的妥协程度已经超出了可以允许的范围。合同研究组织及其私人医生网络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几乎是俯首听命。研究人员丧失了大部分独立性,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补偿。许多人从制药公司赞助者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员充当了制药公司的顾问,去研究它们的产品,成为了建议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的受雇员工,与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一起申请专利和制定专利使用费计划,在制药公司赞助的研讨会上推销药物和设备,沉迷于昂贵的礼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许多人在制药公司中还拥有股份。这些交易可以使他们的薪水飞速增加。例如,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主任在1998年仅咨询费就赚了50万美元。很难相信与制药公司的利益联系不会给研究人员的医药研究和教育带来偏见。大型制药公司不仅控制实验的整个过程,而且为了给以后做好准备,它还试图让研究人员全心全意地为它服务。此外,大型制药公司还向国家卫生研究所不断渗透。国家卫生研究所用财政资金资助全国绝大部分的基础医药研究,它本应完全根据药物的科学价值来批准药物上市与否,并且独立自主地进行研究,挑选制药业的合作者也应该只考虑公众利益,而不考虑商业利益。但是2003年《洛杉矶时报》上一项由大卫·威尔曼(David Willman)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威尔曼发现,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可以说这些人是政府机构中工资最高的员工)一般都会从与研究所有交易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报酬或是股票期权。此类联系一度是被禁止的,但是1995年,时任研究所主任的哈罗德·沃尔姆斯(Harold Varmus)大笔一挥,放松了限制。此后,国家卫生研究所不再限制它的科学家耗费时间从事外部研究并收取费用。根据威尔曼的报告,与制药业界有财务联系的高级科学家包括:美国关节炎肌肉骨骼皮肤疾病全国协会会长,国家卫生研究所临床中心(主要的临床实验基地)主任,国立糖尿病、消化系统和肾脏疾病研究所(NIDDK)下属的糖尿病、内分泌和代谢疾病分所的前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前所长。一些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赚取了巨额的咨询费。例如,免疫学实验室的代理主任,2003年的工资是179万美元,而他在11年内赚取的咨询费达140万美元,并获得了价值865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很难确定这种经济关系对国家卫生研究所在药物批准、研究优先权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上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据说,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事外部活动必须经过监管者的批准,而且科学家不应当参与影响外部客户的决策,但是威尔曼(Willman)的报告表明这仅有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国家卫生研究所没有要求它的高级科学家们向公众披露他们的额外收入(惯用的伎俩就是将报酬很高的科学家与工资较低的科学家混在一起)。其结果就是,2003年,该机构2259名高级科学家中超过94%的人没有披露他们的咨询收入。与威尔曼的文章同时刊出的《洛杉矶时报》社论非常正确地指出:“制药业在华盛顿无处不在。它出现在书写医疗保险的处方药名单中;它的游说者比议会的议员还要多;它慷慨地向医生送礼物、为他们提供免费旅行,目的是阻止他们直接对比两种药物的效果、而是用安慰剂来进行对比实验。”该社论总结道:“威尔曼的故事听起来十分惊人,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冰山一角。议会能够帮助这套系统建立起来,也就能够帮助瓦解掉它,这必须从高层广开言路才行,废除《贝赫—多尔法案》中最具破坏性的条款。最重要的是,要重塑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声誉。”2004年1月,参议院劳动、健康、人类服务和教育经费委员会开始就这些问题召开听证会,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总监察长和美国会计总署都展开了各自的调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任命了一个蓝丝带小组(Blue-Ribbon Panel)来审查利益冲突的问题。偏见——随处可见一点都不奇怪,偏见弥漫于各种药物实验中。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制药公司赞助的研究对该公司产品有利的研究结果是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的研究结果的四倍。这与很多其他证据相吻合。这些证据表明,与制药业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更倾向于得出有利于公司产品的结论。例如,对Norvasc这样的钙离子阻断剂的研究,70篇与此药物安全性相关的文章中,持肯定意见的作者中96%的人都与制药公司有经济联系,而持批评意见的作者中只有37%的人与制药公司有经济联系。我不会详细描述怎样做就能操纵研究使其带有偏见。但是,有几种方法是值得一提的。有时候偏见只不过是编造的动人故事——研究人员即使没有得出满意的结论也去赞美药物。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制药公司赞助的研究人员推荐它所生产的药物的情况,是非营利组织赞助的研究人员推荐药物的五倍,而不管研究的结论到底如何。但是通常情况下,偏见在实验设计的阶段就已存在,比如使用安慰剂进行对比实验,几乎所有的模仿性创新药都会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上,就像ALLHAT实验的结果那样,如果与已上市的药物进行比较,它们可能并不那么有效。即使是声誉最好的医药中心的研究人员也会进行这样的实验设计,因为赞助者坚持要求这么做。另一种办法是,在实验中只用年轻患者,尽管最后服用药物的可能都是老年人。因为年轻人服用药物,通常不会产生太多的副作用,所以,在实验中这些药物显得比实际使用时更加安全。第三种方法就是不将新药与安慰剂比较,而是与剂量较小的旧药相比较。上一章中,我描述了降胆固醇药是如何这样做的。在许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主要用于治疗关节炎的Naprosyn就是这种药)实验中,这一招也屡次被采用。新的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看上去之所以疗效更好,是因为对比药物的剂量过小。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旧药被错误地使用。例如,在对比氟康唑与旧药两性霉素B对艾滋病人所患的真菌感染的治疗效果时,两性霉素B是口服的,这样就显著降低了它的实际疗效。毫不奇怪,这些实验的赞助者是氟康唑的制造商。或者,还可以将实验时间设计得过于短暂以至于没有什么意义。许多需要长期实验的药物都是如此:降血压药的实验往往仅持续几个月,抗抑郁药实验只持续几个星期,而实际上患者可能需要连续数年服用这些药物。一些短期服用疗效好的药物,如果长期服用就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一种最常见的使研究带有偏见的办法就是只发表部分数据——使得产品看起来更好的那部分数据——同时忽略其余的。治疗关节炎的药物Celebrex的临床实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由该药物的制造者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后来被辉瑞并购)赞助的研究认为,Celebrex比其他两种旧关节炎药的副作用小。这一结论被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并附有一篇赞扬性的社论。后来,编辑才听说这一结论仅仅建立在为期一年的实验头六个月的数据基础上,整个实验结束之后,Celebrex没有显示出任何优势。社论的主笔十分愤怒。《华盛顿邮报》引用他的话:“我很生气……我写了那篇社论。我看起来就像个傻瓜。但是……我当时只得到了文章中披露的那些数据。”杂志的主编说:“我听说他们向我们投稿的时候就掌握着另外六个月的数据,我很痛心。我们原先确认的信任标准可能已经被破坏了。”把不喜欢的东西藏起来偏见的极端形式就是不遗余力地压抑那些负面的结果。在私人控制的实验中这很容易做到,但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术中心进行的实验中。这里有几个广为人知的案例。1996年,一家叫做免疫反应公司(Immune Response Corporation)的生物科技公司与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卡恩(James O. Kahn)博士以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斯蒂芬·拉哥科斯(Stephen W. Lagakos)博士签订合约,对其药物Remune进行多通道的实验。该药物被假定可以通过加强免疫系统而减轻艾滋病病情,该公司正期望FDA批准该药以“治疗疫苗”的名义上市。卡恩和拉哥科斯在77个医药中心的2 500名艾滋病患者身上进行了实验。但是免疫反应公司保留了实验的数据。三年之后发现Remune显然没有效果。但是,该公司拒绝了卡恩和拉哥科斯发表负面结果(也就是说该疫苗无效)的要求。它希望他们在文章中加入对一部分据说药物在其身上显示出疗效的患者的分析。卡恩和拉哥科斯认为公司的分析与科学标准不符,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免疫反应公司威胁他们,如果不将公司的分析包括进去,就不向他们提供最后的5%到10%的数据。经过反复交涉,最后该公司同意只有在它获得对文章的审核权的前提下,才交出剩下的数据。卡恩和拉哥科斯又一次拒绝了它的要求。在他们已有数据的基础之上(数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他们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负面报告。免疫反应公司于是起诉卡恩及其所在大学,索赔百万美元,声称他们损害了它的利益(该公司最终败诉)。看看这场争论的幕后情况是十分有趣的。该公司与研究人员签订的合约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隐患。尽管合约没有赋予免疫反应公司审核研究论文的权力,但它确实使公司全面介入到研究的细节中去。合约规定设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包括该公司的医药主管)来创作论文;它保证了卡恩与公司在实验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它赋予公司在论文发表前阅读并最终定稿的权力。当实验结果显然是负面的时候,该公司强调了进行分析的权力。后来,免疫反应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解释说:“把你放到我那个位置想想吧。我已经花了超过3千万了。我想我应当拥有这些权力。”他真的以为自己有权力获得正面的结论。卡恩和拉哥科斯在捍卫真理上体现出了他们的勇气和诚实。毫无偏见地进行临床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与赞助者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许多研究人员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或是顺从赞助者的意愿,或者是屈服于压力。但是合约的条款有时是让寸失尺。通过允许公司参与整个实验过程,甚至将医药主管作为合作者,卡恩和拉哥科斯最终因小失大。该公司与这项研究显然存在利益冲突。然而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该合约已经给予了卡恩和拉哥科斯很大的自由了。许多现在合约会赋予公司更大的控制权。那么,我们到底知道什么?当一家制药公司向FDA申请批准一种新药时,它被要求提交它赞助进行的所有临床实验的结果,但是并不要求将结果公开。FDA可能基于非常少的证据批准某种药物。例如,该机构通常要求只要一种药物在两项临床实验中都比安慰剂效果好即可批准面市,即使在其他实验中该药并没有效。公司只发表正面结果,而且它们会把文章做一些小改动,在不同杂志上发表多次。FDA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性发表行为。根据这些医药报告,医生会误以为药物十分有效,于是公众也这样认为。而且,公司还往往对药物的正面作用夸大其词,而对负面作用绝口不提。以抗抑郁药为例。2002年,十大最畅销的药物中有两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类型的抗抑郁药——Zoloft和Paxil。大家公认SSRIs是十分有效的药物。数百万美国人正在服用它们,许多精神病专家和初级保健医生非常信赖它们。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人们泼了一盆凉水。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允许公民获得政府文件),该研究的作者获得了FDA1987年至1999年间批准的六种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物——Prozac、Paxil、Zoloft、Celexa、Serzone和Effexor(除了最后两种,其他都是SSRIs)——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批准之前对这些药物进行每一项安慰剂对比临床实验的,所有42项临床实验中大部分只持续了6个星期。这个发现使人清醒。平均而言,安慰剂的有效性大概是药物的80%。药物和安慰剂的区别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抑郁严重程度的度量标准)的62点上仅仅相差2点。尽管数据在统计上显著,但从临床角度看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实验结果对所有六种药物来说都差不多。当然,这些数字是平均而言的,可能对某些特殊病人某种药物会有更好(或更坏)的疗效。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基于所有的证据,而不是那些制药公司发表的证据,新的抗抑郁药并不像它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奇迹”。最近,一些生产SSRIs的制药公司受到了严厉的指控,被控这些药物对儿童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有时是危险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另一项研究也很有教育意义。数十年来,妇女们服用雌激素、采用黄体酮荷尔蒙替代疗法,不仅用于治疗更年期症状,而且还相信它能预防心脏病。这种认识源自制药业赞助的研究。但是现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临床实验表明,综合荷尔蒙替代疗法不仅不能预防心脏病,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发病概率。这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制药公司赞助的研究报告是多么不可信。我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想阻碍技术进步。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正是由于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创新性研究和开发,才使我们能够拥有这么多可以挽救生命的重要药物。没有人希望糖尿病患者没有胰岛素、受到感染而没有杀菌剂、出现了严重疾病却没有疫苗、心脏病发作而没有抗凝血剂、得了癌症而没有化学疗法、没有全套的止痛药和麻醉剂以及许多许多其他药物。Gleevec是一个很大的突破,Epogen和Taxol也是。Prilosec很重要,降胆固醇药以及ACE抑制剂和许多其他药品也同样重要。所有这些药物都延长了生命,极大提高了我们的生命品质。如果我不是对医药研究和创新疗法的价值深信不疑的话,也就不会选择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度过我的职业生涯了。因此,我的意图并不是要说处方药毫无用处,或是危险、骗人的玩意儿。但确实有许多处方药是那样的,特别是有利益关联的公司和研究人员测试的新模仿性创新药。新药比旧药好?还是不如旧药?令人担心的是,通常我们不知道答案。大多数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带有偏见的研究结果和夸夸其谈的广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