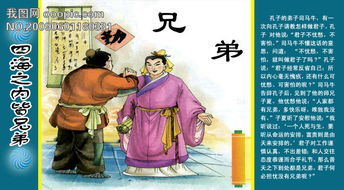本刊记者 韩松 在这篇关于“跨文化管理”的文章中,记者首先避免的是先入为主的定见和不恰当的概括,将接受本文采访的每一位外籍人士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决非某国人或某国银行家或在华外籍银行家的所谓“典型形象”。本文并非是对在华外籍银行家的结论性论述(treatise),而是关于一个小小的实证研究的尽可能翔实的全程记述,以及记者的直观观察。有关英文访谈在翻译为中文过程中,也尽量直译,以避免发生所谓“迷失在翻译中”(lostintranslation)之类的事件。 除了请3位外籍银行家分享各自的跨文化感受,记者亦采访了国际才智服务机构光辉国际(Korn/FerryInternational)资深合伙人DavidEverhart,对记者观察到的外籍银行家在跨文化管理中的感受予以点评。 出场人物 首先,介绍一下本文中的3位外籍银行家,以姓氏英文首字字母为序: 拉蒙(RamonGascon),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中国区主管; 罗丽莎(LisaRobins),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行长,中国区资金管理业务主管; 萨库马(C.R.Sasikumar),印度国家银行(StateBankofIndia)上海分行首席执行官。 拉蒙: “退休后,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叫《我曾在那里且没有人教我》。” 我今年42岁,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在西班牙对外银行渡过。我家世居马德里,是马德里竞技队世袭罔替的铁杆球迷。在西班牙,我们这样类似中国“老北京”的老马德里人被人们戏称为“猫”(gatos)。我早年踢过足球,现在则热衷骑摩托飙车。 从童年起,我一直向往国际化的生活。对我而言,西班牙以外的世界很有魅力,我希望有机会充分享受并了解整个世界。 1989年7月10日,我加入西班牙对外银行,服务至今。其间,我一直从事国际业务,开始在经纪部门,从事资本市场、公司金融、证券清算等;其后转入银行下属的贸易部门。约10年以前,西班牙大企业开始非常激进地在海外扩张,西班牙对外银行即通过我所供职的部门为企业提供支持。我在俄罗斯工作了1年,又在非洲工作了4年,单枪匹马负责银行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业务。当时虽然我常驻马德里,但多数时间在非洲度过,在马德里反而感觉像个外国人。 2000年10月,我被调到中国,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07年,升为中国区主管,常驻北京。当前西班牙对外银行在中国内地有两个代表处,成为中信银行的外国战略投资合作伙伴,并通过他们开展在华业务。 我们同中信银行的合作是由总行的专门人士同中信银行的相关部门直接对口,比如在零售银行方面的合作,由马德里零售银行部门直接同中信银行零售部门对接。但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代表处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居中促进、协调,促成双方间的沟通与合作。这项工作颇具挑战性,有时就像在两股洋流间弄潮。在跨文化语境中,向任何一方面解释另一方的立场和观点、促成共识都没那么简单,但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工作。 中国文化让我变得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从容。现在我会尽量学习运用中国的方式来处理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在中国工作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教益是,我懂得什么是不辞跬步、积小胜为大胜。刚到中国时,我们在中国只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处,而现在我们在中信银行拥有20亿欧元投资。同中信银行的合作项目既富挑战性,也成果丰硕。我们共同探寻合作领域,并不断强化彼此间的关系。 令我自豪的是,我可以称自己是在同中国一道成长。过去数年内中国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在短短时间内,如此迅速地完成如此之多的变革,令人异常振奋,而我身处其中的最前沿,这是一种非常难得、高度不同寻常的个人体验。退休后,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为《我曾在那里且没有人教我》。 罗丽莎: “那种感觉就像你有一块大大的调色板,可以让你尽情描绘心中的画卷。” 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起步。1979年,我作为导游首次踏上中国,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1980年,我再次来到中国,为一家法国公司在中国开办分支机构,并一直在中国工作、生活,直到1986年。 正是在中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一个法国人。我们曾掷硬币来决定是应该由我跟随他的事业,还是他追随我的事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彼此兼顾。我们来到巴黎,在那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也在巴黎创办了一家公司,主要举办讲座和会议,讲述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客户主要集中在航空、铁路、食品等行业。 1988年,我加入了摩根大通的前身之一大通银行(ChaseBank)在法国的分支机构。1992年,我们迁回美国。此后,我在摩根大通内部从事过多种不同工作。女儿上大学后,我们决定回到亚洲,2006年我们迁到香港,当时我负责摩根大通香港资金管理业务的地区产品管理。2007年8月,我有机会回到中国大陆,几乎从无到有建立起我们在中国内地的若干业务。 我早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亚洲研究,主修中国研究,并获硕士学位。这是一个跨学科专业,主要涉及艺术史和人类学。此前我曾在台湾生活过两年,学习中文。 实际上我一直是在美国以外长大的。尽管来自美国中西部,但我的家庭曾在多个不同国家生活,包括印度,当时的东巴基斯坦、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以及伊朗。我本人也曾在墨西哥生活过。 眼下我和我先生住在后海的四合院里。我们没有外侨家庭在异国通常会遇到的诸多挑战和烦恼。我先生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能够回到中国令他兴奋不已。 我想海外生活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或曰作为外侨的一大优势是,你总是有机缘结识形形色色的人,尽情尽兴地缔结友谊,而无须像在本国时要顾虑那么多人际关系、礼俗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非常令人愉悦的体验,可以开拓你的视野。那种感觉就像你有一块大大的调色板,可以让你尽情描绘心中的画卷。而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中,有时你反而会受制于其中的种种社会规范,无法像身处异域文化时那么放得开——当然,我懂中文,因此在中国生活时,很多大门都会向我敞开。 萨库马: “我来自一个同中国近似的文化背景。” 领导印度银行上海分行是我的第一份海外工作。 我生于1957年11月30日,于1978年作为实习生加入印度最大银行印度国家银行,从信贷工作起步,历任印度国家银行在印度国内若干分行的行长,被派往中国前任印度国家银行孟买地区总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部总经理。2006年4月20日,印度国家银行上海分行正式获银监会批准在中国开展业务,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从事商业运作的印度银行,而在印度,目前则尚无任何一家中国的银行开展业务,因此印度国家银行上海分行堪称中印两国间唯一的金融桥梁。 当前,印度银行上海分行有28名员工,其中有4位印度人,24位中国人。除上海分行外,我们在天津还有一个代表处。我们计划向监管部门申请从事人民币业务,并将天津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做为印度人,我来自一个同中国近似文化背景的国度。中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印度历史上的佛教时代。两国人民分享近似的亚洲价值观,包括看重亲情以及为家人尽责。双方的文化差异大多只是表面性的,如着装和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关于着装,我得说,我们印度人比较传统、保守,而中国人则已实质性地接受了西方风格。此外,据我观察,相比于中国兄弟,我们印度人的宗教色彩更浓重些。 来中国前,我预料到会在语言方面遇到挑战,为此在孟买参加了一些基本汉语普通话口语培训。我没有大量阅读同中国相关的关于跨文化问题的文献,但给自己准备了一本(英国汉学家)ElizabethScurfield女士的《中文自学》(TeachYourselfEnglish),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社会评论。我太太和我一起生活在中国,两个孩子则留在印度。定居上海的过程很顺畅,我们所居住的社区住有相当多外侨,尽管居民中多数还是中国人。社区居民鼓励我们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社交活动,我们感觉宾至如归。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我无不受到热情款待。但尽管人们对印度人颇为友善、亲热,但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度电影和电视剧。我想,如果人们对印度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多元性能够有所了解会更好些。但这并未影响银行内的沟通与团队合作,因为金融业的从业人员通常具备高度的专业精神。我们的团队中,本地员工占绝大多数,因此,问题更多是印度员工要如何融入本地体系。我认为这项工作已成功完成。在中国,我所获得的最宝贵的教益是中国人在工作场合和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自律,能够亲身观察到这一点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回忆。 最后,介绍本文的点评专家,著名国际才智服务机构光辉国际(Korn/FerryInternational)资深合伙人、亚洲领导力开发解决方案业务总经理DavidEverhart。Everhart曾同西方和亚洲经理人合作开放并实施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与商业战略,在这方面有超过20年执业经历。Everhart拥有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及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曾在日本生活、工作多年,会讲日语。 “学习敏捷性”:成功海外经理人的素质 我不只是雅典公民,也不只是希腊公民,而是世界公民。 ——苏格拉底(Socrates) “如果看一看摩根大通如何遴选中国区高管,你会发现,众多外籍人士此前就已同中国有某种关联,如摩根大通(中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霍康(CarlWalters),是我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摩根大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黎拓(PeterLighte),早年曾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实际上,当初我之所以受雇来中国,并非因为我通晓业务,而是因为对中国有所了解,且懂中文。当时,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而言,能讲中文至关重要。” 罗丽莎所提到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两位“大佬”——黎拓和霍康,在任何国家的银行家群体中都会显得有些“另类”:前者,照他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网站上找到的一篇资料的说法,“早在‘乒乓外交’前即有幸赴台湾东海大学教英语、学中文……准备从事学术工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乎有点“阴差阳错”,才进入金融服务业。后者则曾留学北大。两位均堪称老牌“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文。 当一家银行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或在该市场从事激进的扩张时,无论如何无法指望“总是”能找到这样的人,原因有三: 首先,市场上要有这样现成的人力资源——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已具备相当深厚的书本知识与一定深度的亲身体验;同时,这样的人才还要愿意改变自己已投入了很多的事业、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取向,尝试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其次,符合上述描述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学习能力和某些特定行为倾向,使其能够在市场和雇主的耐心允许的时限内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学习曲线。 最后,市场发展的进程要恰到好处,可以让这样的人才相对从容地建立自己的学习曲线。毕竟,不管一个人有多出色,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由人文学者到银行高管的蝶变,在今天银行业务越发繁复、带有越来越多技术性含量的语境中,尤为如此。

显然,在市场开放初期,银行在东道国只有一个代表处,首要任务是了解本地市场,并同政府和监管部门打交道,以获取开展业务必需的各种准入许可时,银行CEO的人才管理抉择相对简单:所挑选的人必须具备相当的跨文化沟通与外交能力,以及耐心,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作涉及大量的政府公关与谈判,而在商务实践中,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角度而言,很少有什么比同东道国政府打交道更富文化敏感性与挑战性。但当上述基础性工作业已完成,银行可以在该国全力从事业务活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本地的人力资源供应并不理想时,CEO们经常面临的两难处境也许是:我此刻能够派往该国领导零售银行或资金管理业务的经理人,也许恰好没有充分的国际经验。这个人也许在纽约、伦敦或东京颇为成功,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北京或上海也能成功?我们不难理解在华外籍银行家及其远在异国的老板们所面临的挑战了。 在罗丽莎看来,跨国金融机构为今天的中国市场遴选出色的外籍经理人,同20年前相比,挑战已经小了很多。“1980~1986年期间,外籍人士想来中国工作就需要懂中文”,而到了2008年,鉴于中国同20多年前相比已取得巨大进步,“尽管懂中文依然是一种优势,但外资机构已可以将一些此前并不太了解中国、但具备跨文化竞争力的人士派来中国”,他们不需要像她一样拥有东亚研究学科的高级学位,但需要“具备良好的神入能力(empathy),懂得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着想,能够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如何成长、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等知道怎样打动一个人…… 回过头来看一位合格的海外经理人应当具备的素质,记者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二: 其一,决定海外任务成败的,有多少是跨文化因素,有多少是经理人基本素质因素?从研究角度出发,我们是否能够将这二者合理地区分开,分别计量? 其二,跨文化领导力究竟是天生的——亦即作为CEO,为海外工作遴选人才时,应该按图索骥、找寻具备某些明显特征的候选人,还是可以后天养成——亦即我可以从业务专长出发挑选人才,而后通过适当培训,让候选人具备领导海外业务所需的跨文化竞争力? 光辉国际资深合伙人DavidEverhart有超过20年为跨国公司经理人提供跨文化商业战略与领导力发展解决方案的经历。据他的观察: “当外资银行大力的发展在华业务时,往往会派出数量非常庞大的外籍工作人员团队,这些外籍人士主要具备具体业务和职能领域的专长,而国际经验则相对较为有限,甚至可能没有亚洲经验。这样可能会产生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一位经理人在本国市场能够取得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在中国也能取得成功;对于一个合格的外籍经理人而言,业务专长固然重要,而跨文化竞争力甚至更重要。 针对记者的第一个问题,DavidEverhart指出,目前尚无较为充分的数据来支撑任何观点,因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很难将各种变量分隔开来,因而很难辨识问题的最终根源到底在哪里。 但基于已有研究,有一点越来越清晰,即辨识高潜力领导人的一个标准就是“学习敏捷性(learningagility)”,亦即以非常富于创意的方式来学习的能力。具备高度学习敏捷性的经理人遇到此前从未遭遇的问题时,不是试图套用此前的解决方案,而是去寻找某种独特的解决方案。“学习敏捷性同在跨文化环境中取得成功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管关系。我敢打赌,如果一家银行能够在其纽约或东京总部内发现具备高度潜质的人才,将他们送到中国来,成功几率会比派‘高级专业人士’(highprofessional)要高得多。” 至于记者的第二个问题,DavidEverhart的答案同第一个问题有一定相关:“有些素质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我祖母,今年已95岁高龄,这辈子从未在堪萨斯州以外生活过,但是她却具备非常宽广的世界观,这同从她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她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面对多元种族和文化,同众多美洲原住民接触。这种素质的养成的确受环境因素影响,使一些人注定比另外一些人更具跨文化竞争力,亦即‘天赋论’确有其合理之处。 “但另一方面,跨文化竞争力中诸多方面是发展性的,换言之,如果你具备我早先所描述的那种很强的学习敏捷性,同他人相比,你的进步可能要快得多得多。遗憾的是,公司遴选人才时,往往仅关注具体业务职能上的能力,而不是很关注心理方面的因素,不去找寻那种心理上更加开放、更富探索精神、具备学习敏锐性的人才,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老子还是笛卡尔?商务语境中的文化差异 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史公记述的这段也许是中国文献中关于“跨文化管理”难题最早的记述:指挥本国士卒时可以威震诸侯,而换了另一个国士卒,则无法重现辉煌——即便是廉颇这样的名将。 “在处理专业事务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受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ReneDescarte)的影响较深,更多讲求理性和系统性,要按部就班行事。而在中国,就我个人体验而言,通向同一目标可以有多个不同的途径,不妨灵活些,有时可能需要迂回或后退,以便再继续前进。” 拉蒙一边说着,一边拿过记者的笔记本勾画着他理解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在商务实践中的体现:代表笛卡尔的世界是横平竖直的矩阵,如同在博弈论入门课程中解释囚徒困境或商学院案例分析中常用的那种二乘二矩阵;而代表东方的,则是纠结的圆环,看起来就像太极图——老子的世界。而外籍经理人作为东道国“前线”与千里之外的总部之间的桥梁,需要时刻穿梭于这两个世界之间,并在两个迥异的世界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除了这种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方面的差异,中外专业人士在商务语境中另一个显著差异,据罗丽莎观察,是双方员工的不同行为倾向与沟通方式: “在美国,人们终日将自己做过些什么挂在嘴边,因为如果不说出来,别人也许不会注意到你的成就。而在亚洲,同美国相反,如果不问,人们一般不会主动说自己工作有多出色。我的很多中国同事往往表现得非常谦逊,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信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美国人恰好相反。 “还有在举行全体会议时,在美国,如果你问与会者是否有问题要提,人们都会举手提问,但在中国,人们不大提问,提问的总是寥寥可数的那几个人。也许是因为早年教育或其他因素,如等级观念——虽然美国也有等级观念,但相形之下,这边的等级观念会更强些,人们认为不该随便向上司‘发难’。我想我需要更多鼓励人们更大胆些,要他们知道,仅仅因为我是老板,并不意味着我永远正确。现在,我们这里的确有人开始对我提出挑战,但还没有达到我挑战我的老板的那种程度。” 即便认为中印两种文化近似之处颇多,两国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行为并无太多不同,萨库马也能感觉些许差异:在印度,领导力与决策机制要比在中国更重共识(consensual),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上文提到的“开放的心态”与“学习敏捷性”,DavidEverhart认为: “中西文化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异。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受笛卡尔世界观影响,人们所受的教育是要解决问题。比如我在培训中做过一个案例模拟,假定公司某一业务出现问题,一种解决方式是,你可以直接找另一个部门沟通,跨部门解决问题,另一种方式是向自己的老板请示。参加培训的美国人中,95%选择直接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首选‘维系关系’,考虑诸如,‘如果我自行跨部门寻求解决方案,而不先同老板打招呼,老板会怎样想?这会对我和老板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对我的老板同我要找的另一个部门的老板的关系有什么影响?’等等。在我看来,中国人更关注如何保持关系,而只要保持良好关系,问题通常也很快得以解决。因此,中西文化中不同的解决问题方式,其间的差异不是快或慢问题,而是人们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 回国,不回国?休克,不休克? 怀旧空吟折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在诗中描绘的意境,放在今天的全球商务语境中,可以被定义为“逆向文化休克”(reverseculturalshock)。 先来点名词解释: 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这一术语最早由已故加拿大人类学家KalervoOberg于1954 年提出,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说得很玄,但其实非常好理解:当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异国,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道工作、生活,可能会发现,我们原有的关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本假定,诸如工作伦理、时间概念、人际交往、沟通方式、各种社会规范和礼俗等,在不同文化间往往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多少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文化。很有趣的一点发现,接受本刊采访的3位外籍银行家均表示自己未曾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休克:拉蒙和罗丽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萨库马则是因为他所感知的中印两国文化的相近之处。 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有意地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东道国文化的熏陶,在异域的生活变得越发自如,事业也见起色,又结交了很多新朋友。这时由于种种原因,又需要回到祖国,而回国后,我们可能又需要适应自己本国的文化,经历一种“逆向文化休克”,而逆向文化休克甚至比文化休克克服起来还要艰难:如果我是个“老外”,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不合当地的社会规范,人们一般会表现得很宽容,但如果是个“海归”,人们则没那么宽容。 “有时我在想,自己是否还重新永久性回到西班牙。我不知道答案。”当被问及是否担心逆向文化休克问题时,拉蒙这样答道。 “在国外生活较长一段时间后,不论你是否愿意接受,甚至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东道国的文化都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不同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更加包容。但这期间,留在国内的人也在变化,只是由于环境不同,他们的发展轨迹同你的有所差异。因此,当你回到故国后,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虽然你的根还在那里。你知道你自己归属于这样一个世界,但同时又同这个世界里其他人颇多差异。每次回西班牙,我都有这种感觉,即便我同旧时的朋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次都会同他们一起骑摩托飙车。我仍然喜欢回到西班牙,但只是短期,因为我的确感觉到同自己的本国同胞间存在着文化鸿沟。” 而同普通侨民相比,归国的外籍高管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定义自己在公司总部的新地位。 “外籍经理人回到本国后,相对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能由中国区总经理一下子变成了总部40位副总裁之一,在一个更大的组织内变成无名小卒,仅仅只有一个小隔断,不再有独立的大办公室;另一方面,很多公司并不善于捕捉这些归国经理人的知识。在我看来,很多很多公司未能将这些‘海归’异常丰富的知识积累加以制度化。”DavidEverhart描述道,其结果是,“据统计,大约近一半外籍经理人在回到本国后一年内辞职”。 对此,本刊采访的外籍银行家也有相当的预期。以拉蒙为例:“如果银行决定将我调回西班牙,并继续从事和中国相关业务,毫无疑问我在中国的经验可以用来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的业务或同中国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即便新的工作同中国无关,我的若干通用经验也可用于其他国际性工作,因为过去的几年中,我已经去建立了一个出色国际经理人的声望与能力,而不论在哪个国家,国际管理总会有共通的地方。” “不利之处在于,总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更多层级。过去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新兴市场拥有相当的决策权后,回到总部我又要被重新移植到一个庞大的系统内,成为不起眼的一个小部件,至少开始时肯定会有些不适应,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对于任何一个结束国际任期重回总部的经理人而言,此类心态的转换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无论如何,我还将会把个人的职业发展目标与中国联系起来。我认为,自己在这里取得的经验对集团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拉蒙看来:“有了这样的国际经历,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无须担心一旦离开中国该何去何从——去哪里生活,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