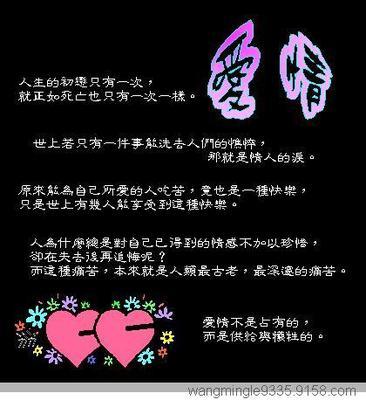近日,一篇关于中国“剩女”的报道成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热点文章。文中称,那些年过27岁、受过良好教育的单身女性在中国被称为“剩女”(leftover women),她们在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该文引发各国网友热议,不少来自亚洲国家的网友表示对此感同身受,而一些西方国家网友则认为“剩女”一说有歧视之嫌,“匪夷所思”。 “剩女”现象一直被反复谈论,却鲜有学界对该现象的解释走入公共视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教师孙沛东的研究《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一经出版,便引来了学界、媒体各界的关注。作为一本纯社会学著作,该书在去年12月出版以来,已经进入第三次印刷。 最摩登的城市,最传统的“相亲” 2007年,孙沛东获得中山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后,自广州来到上海。秉着在巴黎养成的“用双脚丈量城市”的习惯,孙沛东每逢节假日,就用步行的方式认识这座她心目中国内“最摩登”的城市。 2007年9月8日,孙沛东来到人民公园相亲角,看到了一幅奇特景象:一群中老年人拿着写满子女信息的纸牌,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摊位前面。这种特殊聚会似乎暗示这里是某种市场,其商品既非果蔬又非汽车。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聚会。 这是这位在广州生活了十几年,又在巴黎生活多年的学者从未见过的。她在《谁来娶我的女儿》一书的开头这样描写: 他们为人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栉风,却气节不倒,口风强硬,绝不让步。为了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驾车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 这里被分为两块:一块是“自由挂牌区”,印有择偶者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被整整齐齐地贴在长达十几米长的广告栏上,广告栏被安置在蓝色的遮阳走廊上。由于广告位有限,有些父母干脆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平铺在地面上或者用木夹把纸板夹在树枝上供人浏览。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广告分60后版、70后版、80后版、涉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号称另类“儿女交易市场”。另一块是“业余红娘区”,父母们挤在婚介周围,翻看记录册上登记的相亲者信息。 最难以让她理解的是,这些被征婚者竟以“80后”居多。另外。被认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城市的核心地带上演?自此,她每周到这里蹲点,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了43位父母和15位待婚青年,收集了65例真实个案,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和探索。 在这项研究中,孙沛东将一般舆论中的所谓城市大男剩女现象或婚介市场问题,放到了几十年社会变迁历程所积压下来的代际关系中来考察,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父母一代身上,由这代人对爱情婚姻、对上升流动以及生活安全等的“集体性焦虑”,来解释他们奔波于相亲公园的行为。 农村“剩男”最可怜 “从我在相亲角做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年龄介于50-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总体而言,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经上山下乡、经历过‘文革’,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的配偶是知青。‘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六成以上是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平均每个本地家庭占有住房一套半。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做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孙沛东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与此同时,在孙沛东的研究样本中,被征婚者中女性占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年龄在26-30岁之间,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硕士学历,有双硕士、海归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也不在少数;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职员、公务员,或者如会计师、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为主。 有一点引起孙沛东关注的是:被征婚者以女性白领为主,相亲角里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副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在中介费用方面,标准更是“男女有别”。有个中介的摊档前摆放着这样的广告:“业余红娘:几百位优秀男女等你选择,男方免费报名、介绍,大龄女勿扰”。男方父母只需在这里留下孩子的基本资料,即可免费入会,而女方则需支付90元方能成为会员。 “我觉得‘剩女’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含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它的盛行,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底层青年男性择偶难和城市青年女白领难觅佳偶,媒体和大众更关注哪个话题?‘剩女’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易赚足注意力,相亲节目、相亲网站、婚介、偶像剧、该题材的漫画和小说等因此欣欣向荣。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孙沛东说。 “如果说‘剩女’是个假命题的话,广大农村的‘剩男’的择偶和婚姻才是真正的问题。在农村,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这部分男性完全处在劣势。没有结婚可能,找不到配偶,而要几代人砸锅卖铁凑出钱来去更偏远和贫穷的地方买一个老婆的农村‘剩男’被忽视了。《盲井》和郝杰的纪录片《光棍儿》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原因也在此。所以‘剩女’其实是一种主动选择,她们的问题在于愿不愿嫁,而‘剩男’是没得选择,他们长久以来娶不到老婆,已经代际传递。”孙沛东表示。 父母一辈对生活有特殊的“怕”

此外,《谁来娶我的女儿》一书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对“剩男”、“剩女”的父母一辈作出了分析。 孙沛东认为,与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代办择偶,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在新生代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图景。 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是2004年9月在北京的龙潭公园。而在1980年代,北京龙潭公园就曾经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那时他们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当他们的子女进入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 针对父母一辈介入子女择偶,最为引人非议的莫过于“丈母娘”的刻板印象。时代周报记者使用百度搜索“丈母娘”、“结婚”关键词,获得的结果基本都为“丈母娘开出这样的结婚条件,这婚还能结吗?一头撞死……”、“未来丈母娘开出结婚条件,把我吓得失眠”等等网友的“控诉”。 反观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由于实为父母代办择偶,物质条件更是被赤裸裸地提及。“汽车无所谓,房子要有。房子没有不行的,房子一定要有。现在买房子贵呀,买轿车又不贵的咯。以后夫妻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有万把块的话,就可以买车子啦,轿车不贵的,房子不行啦。房子是大价钱啊,小夫妻两个人买到什么时候啊?贷款要贷到什么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找了个朋友工资是很好的,买房子,贷款要还20年。所以我帮我女儿洗脑子,我说:一个男的一个月工资是1万元,一个如果说是8000元,1万元的那个没房子,8000元的那个有房子,我宁愿要8000元的那个。你说呢?这个肯定要算这笔账的,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没房子的我不要。有房子、工资偏低一点点,当然这个还是要有原则的,工资要比我女儿高,一定要有房子的。1万块也好,8000块也好,要是没有房子,等于工资就跌下来啦,对不?要还贷款还个20年,我吓也吓死了,我是不要的。”(摘自书中被访者) 作为社会学者,对这样理性、赤裸裸的经济要求,孙沛东表示“理解”。“‘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并遭受了经济转型的困窘,因此,他们对生活有着特殊的怕。他们的子女—‘邓的一代’迎着改革大潮出生,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或者魔咒,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毛的孩子们’的爱与怕就在子女婚恋这个环节集中爆发。”孙沛东说。 “这种非常理性的物质要求,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现在社会上对丈母娘这个角色的丑化,其实很不公平。你很难说是具体某个人的要求,它是整个社会几十年历史变迁形成的产物。”孙沛东特意指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