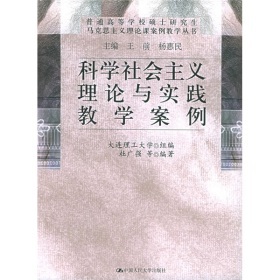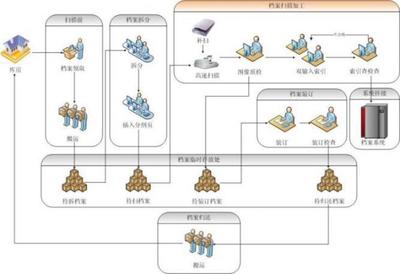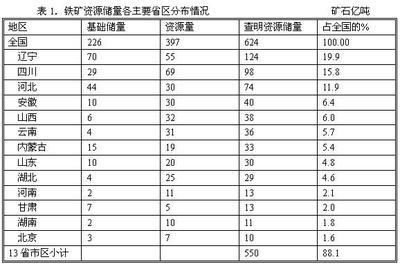和以往的政权更迭不同,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不仅仅在社会管理层面,而且力图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照理想的模式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因此,随着新政权在城市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故鼎新,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是移风易俗,荡涤娼妓、烟毒、乞丐等旧社会污泥浊水。这项工作的开展,对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风陋习,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使整个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因此能否有效地取缔和治理娼妓、烟毒、乞丐等旧社会弊风陋习,是北平(京)市委、市政府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多项社会改革措施,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烟毒、乞丐等污泥浊水,从而净化了北京的社会环境,推动了北京市崭新社会风貌的形成。 一、废除娼妓制度 妓院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也是残害妇女的人间地狱。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解救妇女出苦海,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净化社会风气,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封了妓院。从此,娼妓制度在北平(京)被彻底废除。 1.对妓院采取限制措施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挂牌营业之明娼、妓院主要分布在前门外八大胡同:即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的由西往东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等地。北平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所谓“清吟”是指妓女都为苏州、扬州或杭州人,年轻漂亮、清秀可人,她们自小就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一等小班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内,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卖官买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二等妓院称为“中地方”,或叫“茶室”。设置比一等妓院差一点,但并不是很明显,差别明显的是妓女。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叫“下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妓院的房子简陋,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1](P373-74) 据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布尔(S.D.Gamble)调查,当时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北京、上海为最高。到40年代初,北平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根据公安局在封闭妓院前的调查统计,北京的妓女大部分来自江苏、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东北等地。绝大部分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有的自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妓院迁移来北京,有的自幼被拐骗、出卖,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家乡都全然不知,被迫当了妓女。少数是由于被遗弃或因家庭所迫等原因从妓的。[1](P74)妓女们受到老板、领家的剥削压迫,在妓院中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彭真等在对北京市的明察暗访中,深感娼妓制度存在的危害。毛主席曾急电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罗瑞卿回答:“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2](P46-47) 北平解放后,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市人民政府在肃特和消灭社会混乱现象、安定革命秩序的同时,即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对妓院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一、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薄,详细记载住客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将登记薄送当地派出所备核。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1](P81)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随后,各派出所经常派干警检查妓院遵守以上规定的情况,并及时收容审查嫖客中的特务、土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们不再浪荡于社会,危害城市治安。民警常在一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和适当处置。这样,许多嫖客害怕“丢脸”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还采取在嫖客的证件上打戳子的办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时间,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证件上、货单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举措吓得许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政府对妓女也着手实行“限制”的办法。利用整顿户籍,对妓女登记造册,只准减少,不准增加。规劝妓女从事自食其力的正当职业,要求她们争取自我解放。然而,对妓女的“限制”并不是很成功,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出现了明娼开始渐少,但暗娼则日益增多的现象。而减去的妓女,除个别从良转业的外,大部分又流入其它城市和其它地区重操旧业。”[1](P81) 在多种措施的限制下,妓院老板有的将妓院改为旅馆,让妓女自谋出路。有的害怕斗争或清算,把妓院变卖为钱财隐藏起来或带原班妓女潜往其他城市。少数恶贯满盈又不甘心失败的转到幕后指挥,利用手下亲信充当老板继续作恶。 2.采取断然措施封闭妓院 妓院问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畸形压迫,因此,北平解放后,要求取缔妓院的民众呼声越来越高。为此,1949年8月9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改造妓女、参加生产的决议,并经大会原则通过。随后,由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组成“处理妓女委员会”,积极进行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9月26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该草案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并伤害人命者,除依法惩处外,并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酌留生活)”。[3](P712-713)l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由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等共同组成指挥部,由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负责,统—领导封闭妓院工作。经各方多次研究,明确了“集中、警戒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收容后对妓女的管教、供给、生活由民政局和妇委会负责”的工作分工,[1](P83)并成立了封闭妓院行动指挥部。 11月21日下午5时,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指出:“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决议》宣布:“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3](P835)这个决议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大会宣读封闭妓院的决议时,会议全体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代表们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在新中国,特别是人民的首都北京,决不允许妓院这种野蛮制度存继续存在,必须坚决取缔。会议刚刚结束,市长聂荣臻立即向公安局下达了执行决议的命令。在行动指挥部领导下,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大力协助,动员组织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于晚8时统一行动,乘坐37部汽车,分赴外城5个区和东郊、西郊等地封闭妓院。 为了使封闭妓院工作顺利进行,避免老板、领家转移财物或隐藏起来,指挥部严密地封锁行动的消息,使老板领家措手不及,并给他们以大的震动。各分指挥部按行动计划和规定的方法部署,先以召开会议的形式,通知妓院老板、领家到分局开会,到局后限制他们的活动,并向他们训话,指出他们的罪恶,不许他们欺骗人民政府和公安局,让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刑警队和二处侦查科负责拘捕老板、领家,并统一将他们押送市局警法科,以便按照他们的罪行分别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各行动小组在妓院附近胡同口及房上布置便衣和武装民警,开始了戒严。妓院门口有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 随后,干部们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如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喊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并说明,对妓女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妓女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她们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不像妓院老板、领班欺骗她们说的那样,要把她们发配给煤矿工人或种地开荒的军垦战士为“妻”。讲明政策后,除了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于寄生淫荡生活,“金丝雀”做不成了,抵触情绪较大外,其他妓女们一听政府并不是将她们扫地出门,而是把她们当人看,充分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都很高兴并愿意听从政府指挥。很多妓女说:“这样做很好,这是叫我们换脑筋”;“叫我们到哪儿就去哪儿,政府是叫学好”。深夜12时,各行动小组把集中起来的妓女送到了设在外二区韩家潭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到22日凌晨5时,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老板领家424人被集中,妓女1286人获解放,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52岁,大部分是18-25岁的青年女子。[4](P667)摧残妓女的巢穴被彻底铲除。 22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向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当他讲到“北京市从此再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1000多名妓女从此跳出火坑获得解放”时,全体代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5](P588)84岁高龄的代表、原清朝翰林潘龄皋在致闭幕词时激动地说:“我是封建时代的旧官僚。照我的出身,我应该说封建制度好。可是我现在要说新民主好,新民主比封建制度好过千万倍。……封闭北京的妓院,这是一件大善事。封闭妓院这件事,我过去在甘肃任内是做过的,可是做不到,办不好,现在经过我们代表会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马上就办了,马上就办好了,这就是新民主的好处,这就是新民主比封建制度好过千万倍的好处,也是人民政府真正替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处。”[3](P869-879) 封闭妓院的消息公布后,广大群众拍手称快,特别是妇女,反应尤为强烈。北京大学的全体女同学,看到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姊妹们得到解放后感慨地说:“这是我们女同学早就关切的事情,记得《共同纲领》上说要解放妇女,现在得到了事实证明,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妓女们感动地说:“过去我们死了都没人埋,现在政府救我们出苦海,共产党真是我们的大恩人!”一个妓女的母亲从太原来到北京看到女儿跳出了火坑,感动得哭了。她说:“要不是国民党在太原抓人要钱,谁愿意把亲生女儿押到窑子里(即妓院)来呢!?”[5](P588)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指出:“妓院是束缚、压榨和蹂躏妇女的最落后、最野蛮的制度,依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加以废除的。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有许多妓女受着严重的生活驱迫或被恶棍流氓分子所拐骗与陷害而沦为娼妓,她们饱受妓院老板、邻家和高利贷这的百般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娼妓的存在,又使性病流行,毒害国民健康。”因此,北京封闭妓院,对妓女本身和全社会都有莫大的利益。短评指出:“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过去的的罪恶是应该被清算的。……所有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依靠买卖与剥削妓女积累起来的妓院财产,应予以没收,这些财产实际上完全是妓女出卖肉体和灵魂所换来的,应该作妓女解放的经费。”短评最后欢呼首都妓院绝迹,妓女得到解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社会改革工作。我们庆祝这一改革的完满成功。”[6]北京市还拍摄了记录这一行动的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并在全国公映。毛主席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聂荣臻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3.把妓女改造成新人 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她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被集中收容初期,因为妓女对政府的政策不了解,表现怀疑恐惧,情绪很不安定。为了安定她们的情绪,教养院工作人员“首先向她们解释了封闭妓院及对待妓女的政策,并尽量照顾她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取回自己的全部财物,解决她们的困难。子女无人照管的则接来同住。”[7](P380)由于干部对他们热心的关怀,逐渐打破了她们的疑惧心理。她们的情绪渐趋平稳。此后,人民政府在改造妓女方面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对妓女进行思想教育。采取的方法主要是:(1)系统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分析统治阶级如何运用他们的政权来欺压人民,揭露官僚政客及其爪牙如何为个人享乐挥霍造成许多罪恶,分析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迫害造成的许多恶果,揭露领家、老板的罪恶,说明娼妓制度产生的根源,分析旧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2)从多方面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帮助她们认清新社会妇女的前途及努力方向。(3)教育她们树立劳动观点。讲解劳动创造世界,现在打垮了反动派,劳动人民真正做了主人,劳动是新社会最光荣的事;指出妇女只有参加社会劳动才能解放自己。同时还给她们讲解婚姻法,教育她们树立正确的婚姻观。[8](P21) 在此期间,生产教育院安排她们看与其身世接近的《日出》、《一个下贱的女人》、《侯五嫂》、《中华儿女》等,对她们的教育很大。她们还学会了演话剧。如演出的《千年冰河开了冻》,观众达2000人,这使她们感到“今天是被重视了,大大地鼓舞了她们摆脱黑暗,走向新生活的意志和勇气。”[7](P381)发动学员诉苦是启发学员觉悟的一把钥匙。诉苦一般先由妓女述说自己的身世,找出受苦的典型,个别漫谈,然后进到小组诉苦,逐渐大家诉起苦来,用她们自己的典型例子进行教育,使她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灾难制造者,是真正的敌人。为了使她们懂得受苦受难的根源,看清老板、领家恣意蹂躏、摧残她们,榨取她们血脂血膏的丑恶嘴脸和残酷手段,妇女生产教养院层层召开控诉会,让受害最深的学员对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控诉。“特别是公审黄树卿、黄宛氏时,在他们控诉之后当场宣判死刑,使她们认识到政府是真正为了解救她们,大大提高了她们的觉悟和学习情绪。”[7](P380)

第二,帮助妓女医治性病。妓女不仅心灵扭曲,身体也遭到摧残。在入院后的健康检查、性病检查中发现,患性病者1259名,占总人数的96.6%;无病者仅44人,占3.4%。北京市集中北大医院、性病防治所、先农坛妇婴保健所、第一医院、结核病防治院、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巡回医疗队等6个单位,57位医务人员参加治疗。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怀着对她们的深切同情,满腔热情为她们检查和治疗,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大量心血。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百废待兴,财政非常困难。为了迅速医治她们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拨出一亿多人民币(旧币,折合小米约12万斤),用于给她们治疗。对此,学员们感动地说:“以前,我们害病烂死都没人管,今天政府花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疗,我们要不进步,可太对不起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了。”有的还说:“现在明白了共产党没有坏心眼。”[1](P90)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梅毒患者治好的占40%弱,其余已不传染,淋病患者治好的占95%,其余已不传染。”[7](P381)身体的康复为她们走向新生活打下了基础。 第三,对妓女进行劳动改造。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尤其原来是一、二等的妓女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很多妓女甚至连衣服都不会洗,生活不能自理。为使她们能自食其力,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进行劳动光荣教育,使她们明白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同时,根据她们的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等组织她们参加适当生产劳动,还聘请专门的师傅手把手教会她们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能。通过劳动,妓女们也慢慢树立起劳动的观点,增强了重新做人的信心。在教养院集体生活的锻炼下,许多妓女逐步改变了好逸恶劳的旧习气,还掌握了一技之长。这为她们以后踏上新的人生道路创造了条件。 第四,为妓女安排出路。妓女经学习和治疗后,政府即按既定方针,分别根据她们各自的情况,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对象的准予结婚,无家可归或无对象者,帮助她们安排出路。截止到1950年7月底,“结婚的596人,占45.3%;回家的379人,占28.7%;参加剧团和医务等工作的62人,占4.7%;妓女兼领家62人,占4.7%,已另行处理,罪恶较重的与其他老板领家一并送军法处审讯,较轻者教育释放;送安老所8人,占0.6%;共处理了1107人,占总人数84%”;[7](P382)“还有200多人不能结婚或回家,政府为她们买了80多台机器,办起了新生棉织厂。1200多名学员,基本上得到妥善安置。”[9] 1950年8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肯定了封闭妓院的行动,指出:“本市此次封闭妓院,彻底摧毁了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是正确的和成功的。这是消灭封建残余解放妇女的一项重要措施,对维护国民健康,防止性病传染,巩固社会治安都有很大的好处,有很大的历史意义。”[7](P383) 二、禁烟肃毒 100多年前,当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鸦片也流入国门,此后,并逐步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泛滥成灾。对此,近代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曾发布过禁烟禁毒的通令,屡屡表示禁毒的决心,但都收效甚微。烟毒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至蒋家王朝覆灭前夕,已达积重难返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禁绝病国害民的烟毒,雷厉风行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肃毒斗争。北京市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前北平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结束了鸦片烟毒对北平人民的危害。 1.禁烟肃毒的初步措施 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就采取了坚决的禁毒措施。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指示,1949年7月2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于转发了《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严禁种植鸦片苗(罂粟),违者,烟苗铲除,并处罚之;严禁烟毒之制造、买卖及贩运,违者,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没收,并严行惩办之;严禁烟毒之吸食及注射,违者,烟毒及吸食注射烟毒之器械用具没收,并分别处罚之。《办法》还限令染有烟毒嗜好者,统限于3个月内向当地公安局或人民政府报告登记,并具结限期戒除。[3](P589-591) 为了贯彻市政府部署,组织好禁烟禁毒工作,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同年8月制定颁发《禁烟禁毒登记办法》,限令:凡吸食注射、制造、买卖、贩运毒品(系指鸦片、吗啡、高根、海洛因、金丹或其他质料毒品)者,要限期到公安分局登记,呈缴所存烟毒、烟具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并具结改过;凡不依限或拒不登记者严加惩处。同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由市公安局治安处所属刑事警察大队负责,会同各公安分局侦缉班(组),组织公安力量以打击制、贩、运毒品为重点开展查禁毒品工作。1949年即“查获毒品案件547起,缴获鸦片烟土烟膏等毒品2483两,海洛因341两,各类制毒原料1830两。”[10](P180)通过坚决查禁,北京市公开的烟馆绝迹,制造、售卖、吸食毒品活动大为减少。 2.全面深入地开展禁烟肃毒斗争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宣布从即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专门负责禁毒工作。根据《通令》精神,4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北京市查禁烟毒办法》,其规定:“凡在本市存有烟毒者,或从事烟毒之制造、贩运、买卖及设具供客吸食注射者,应即于限期内,向所在地之公安分局报告登记,缴出烟毒及制造吸食注射用具,其逾期仍不登记者一经查出,严加惩处。”《办法》同时还规定:“凡本市吸烟毒嗜好之烟民,应于限期内,向所在地之公安分局报告登记,缴出烟毒及吸食注射用具,自登记之日起,依其年龄体质,及嗜毒程度,限期具结戒除,其逾期仍不登记或未戒除者,一经查出,定严加处罚。”[7](P180) 为了加强对禁毒工作的统一领导,北京市成立了由市民政、公安、卫生、文教、法院、工会、妇联、工商联、青联、郊区工作委员会组成的“北京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市各级公安机关与民政、卫生等部门联合采取行动,封闭私设烟馆,没收其房屋、烟具及毒品;铲除种植的罂粟苗;收缴并当众焚毁烟土;周密组织对烟民的限期登记、查缴烟毒、烟具和戒除工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对现行活动的贩毒人员及私开秘密烟馆分子给予严厉刑事处罚。公安缉毒工作更加深入,“1950年查获毒品案件365起。其中,1950年1月破获王桂英、任逸轩贩毒团伙,摧毁景山后街秘密制毒所,一次性缴获白面毒品(海洛因)20.5斤;查获历史上最大的毒贩庞辅臣勾结机关内部人员大批走私贩毒案,毒品价值黄金2000两。”[10](P273) 1951年1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彻禁毒政策的令》。该命令要求,“本府所属各单位,皆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售烟土及其他类似之毒品,违者,一经查出,除将毒品没收外,并依法予以惩处。”其还规定,“过去存有烟土及其他类似毒品者,应按前中财委指示迅速提交市财经委员会汇缴中央财政部集中处理。”[11](P8)12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其规定:“一、自布告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制造、贩运、售卖鸦片等毒品。其藏有鸦片烟毒及其制造用具的,应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分局全部报缴;二、吸食鸦片烟毒的,自布告之日起,须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派出所登记,限期戒除;三、医院、工厂、学校、机关等专为医疗或化验用存有毒品的,须到所在地区的公安分局登记,听候通知处理。”[11](P558)根据市政府部署,市公安局以派出所为单位深入各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烟民及其家属座谈会等进行禁毒宣传,组织对制贩、吸毒人员的登记。 截止至1951年12月底,共“登记吸毒人员290余名,制毒人员40名,贩毒人员62名,缴出各种烟具250余件,鸦片烟土1054两,最多1人即缴出鸦片烟土、烟灰670余两。”[10](P273)在此期间,公安机关通过对群众和烟民的调查,组织专门力量开展秘密侦查,全面掌握了地区的毒情和线索。市公安局加大缉毒工作力度,深追猛打。1951年共破获毒品案件306起,其中破获了北京解放以来最多的“肛门队”运毒团伙,抓获以毒贩鲍子庆为首的案犯32名;并查获了大量毒犯以皮毛行、西药行、百货行、茶叶铺等行商职业为掩护,秘密进行团伙制贩毒案件。[10](P273) 3.掀起禁烟肃毒运动的高潮 1952年,中共中央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从中央各部门以及各地区揭露出为数众多的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至反革命分子,从事贩运毒品的罪恶勾当,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更给刚刚初见成效的禁烟禁毒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鉴于此,中央认为,为彻底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发动一场群众性的肃毒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因此,1952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明确指出,“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各地要运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揭露出来的线索情况,穷追不舍,开展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肃毒运动。对于重要案件,要组织专案侦察。在中央部门应以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作为重点;在地方则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即以毒品的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开展运动的重点。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再次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罪犯份子及反革命份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12](P35)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禁毒运动于1952年8月9日开始进行,16日开始向群众宣传。市委除布置在机关、工矿企业进行宣传外,并着重对市民进行宣传,号召市民检举,要求毒犯坦白登记。各区组织专门力量,由召开群众大会、控诉会、片会,而逐步深入到召开院会、小型座谈会,并重点挨门挨户进行访问,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了毒犯对国家对人民的严重危害,激起对毒犯的痛恨,“很多市民破除情面对毒犯进行检举,有的儿子检举父亲,有的母亲检举儿子,逐步形成群众性的禁毒热潮。”截止8月26日,“全市共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群众会11000多次,对52万市民进行了宣传,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共收到群众的检举材料38645件,坦白登记的毒犯共有10014人。”[12](P36)广大市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又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情”,“这是继三反运动后的又一次社会改革”,“人民政府办事干脆彻底,一定能够把烟毒禁得干干净净,不像国民党越禁越多”。很多市民要求“把罪大恶极的毒犯枪毙几个。”[12](P36) 北京禁毒运动于11月中旬基本结束。在这次重大禁烟、禁毒运动中,北京市共登记吸毒烟民55028人,坦白登记的毒犯9172人;逮捕毒犯647名,其中制毒犯119名,贩运毒品犯435名,零售及窝主93名;处决重特大毒犯3人,判处徒刑448人,管制进行改造教育的213人。其中缴获毒品烟土2187两,白面153两,料子517两,其他毒品988两,制毒原料491磅,制毒机器8部并铜模子5个,各种毒具2139件。在禁毒运动中,广泛发动群众,召开各种禁毒宣传群众会议21648次,到会群众达到100万人次以上;收到群众各种检举材料11万多份,被检举对象26870份,这次群众性大规模禁毒运动,使旧社会遗留的毒品危害得到根本性清除。[10](P275) 195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戒烟工作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戒烟工作部署。为加强戒烟工作领导,密切各部门联系,调整了原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政局、公共卫生局、公安局、文教委员会及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市工商联合会等单位组成,并在委员会之下设立办公室,具体指导各区戒烟工作;同时各区有关单位成立分会。“以民政部门出面尽心宣传并作调查登记(不作公开登记),组织戒除,卫生部门负责发药、检查、治疗在戒除中可能发生的疾病,并在医院中腾出一定床位(20张)以应急需,公安部门从各方面大力协助。”[11](P69)在戒烟过程中,贯彻了“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进行宣传教育,说明烟毒的留害和烟毒给吸毒者的苦难,启发吸毒者自觉戒除,组织吸毒者规劝、监督。”[11](P69)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在全市共登记吸毒烟民231人中,除22人身体状况等原因免、缓戒外,全部进行了戒除。自此,由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吸毒烟民在北京市基本绝迹。 三、收容和安置乞丐 乞丐是困扰社会发展、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近代以来,北平(京)城市里的乞丐数目很多,残存的年代甚久。民国时期,虽然政府对北平(京)城市乞丐问题进行过多次处理,但是,对待乞丐的方式基本是“定期收容过期不管的办法,把抓到的乞丐拘留起来,每天每人发给玉米面10.8两,乞丐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还遭到苦打恶骂”。[3](P598)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乞丐的处理,仅是为了市面观瞻,并没有把乞丐当成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来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最终政策流于形式,没有达到对乞丐的根治目的。建国初期,北京市针对城市乞丐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突出的社会改造政策,大大净化了社会环境,为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商界的正常营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 1.对乞丐实行强制收容的政策 北平和平解放后,因新政府政策宽松,“要饭不受干涉”,“行乞得钱容易”,致使乞丐队伍大有增长的趋势。“有三轮车夫转为乞丐者,有打算行乞数月,积累资本以便营小生意者,有自己有职业而派出其子弟、家人当乞丐者,有半日拾破烂,半日行乞者,”一时乞讨成风。[13]同时,乞丐们错误地理解“解放”,误认为“共产党来了,乞丐也该大翻身了”,甚至有些乞丐自称为无产阶级,强乞恶讨。[3](P98)如“有唱数来宝的,不给就骂人,有手拿石头的,不给就打破玻璃窗,有拿大粪的,有数人拦阻买主,使商店无法经营的……有成队乞讨,并说是‘红军叫我们干的’,头戴红缨,手持牛骨,开口就要五元,给迟了不行,说‘耽误了工夫,得加五元’”等。[13]商人们也因一时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不敢加以干涉。当时乞丐们在东安市场集伙,将大大小小商号定出乞讨官价,金店每家40元,普通商店10元,轮流乞讨。据商人们反映,对乞丐开支每天最多400元,最少也得百元以上。一般情况下,一个乞丐每日最多竟讨到二、三百元,约合当时市价小米15至20斤,比一个劳动工人赚钱还多。[3](P598-599)乞丐问题,已经成为扰乱城市秩序、阻碍社会生产的重要问题。 针对北京城内的乞丐问题,1949年3月,北平市政务会讨论决定,由民政、公安两局负主要责任,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纠察队及各群众团体等有关部门合作组成乞丐管理处,负责对城市乞丐的收容处理工作。[14]4月,北平市人民政府组织了对城市乞丐的详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北平市乞丐可分为三种:一种为职业乞丐,有的世袭,有的拜师授徒,比较有组织,在乞丐中为最狡猾,染有流氓习气最深者,成为乞丐中之骨干,亦即处理乞丐中之重点。一种为乡村破产之农民、逃亡之地主,可以回家或想回家而不能者。一种是城市贫民、破产之贵族和部分失业者即老幼孤寡贫苦无依者,为数最多。一种为散兵游勇即流散军人之家属等为数较少。[3](P610-P611)根据这些调查情况,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了收容、遣送回籍与教育改造组织劳动等三种处理乞丐的办法。 5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处理乞丐委员会,由公安局、妇委、法院、卫生局、纠察总队和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代表组织而成。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派出干部若干人,分配在各收容所工作。同时,对北京市收容和处理乞丐的单位进行了分工:救济院,为收容乞丐总办公地点,负责联络督导等责任。凡不能从事生产的老弱孤寡残废乞丐,由区直接送安老所,其余一律送救济院,然后根据不同情况,经过审查后再分配到各收容单位;安老所,主要收容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废及有病的乞丐,收容后先予以教育,能回籍者令其回籍;不能回籍者收容留养,逐渐使其参加部分生产劳动;育幼所,收容8岁至15岁的儿童,主要为学习,但年纪较大者也从事适当的劳动;平民习艺所,收容有劳动力的青壮年男子,经过教育后,编成劳动大队,赴指定地点,参加劳动生活;妇女教养所,收容青壮年妇女和回籍的乞丐,回籍者经甄审后遣送回籍,青年或壮年妇女,经教育后使其参加缝纫等手艺学习。当时,党确定了处理北京乞丐的方针是“一方面收容,一方面组织劳动,对各种性质不同的乞丐,予以不同的处理办法,以期使乞丐劳动生产,或学习技艺,使其达到改造教育、自谋生活为目的。”[3](P599) 5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时办法》,明令在城中严禁恶乞恶讨及以乞丐行业授徒组织乞丐从中渔利行为,并确定了“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5月27日,北京市处理乞丐委员会根据华北人民政府收容乞丐的方针和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开始对乞丐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性收容。在收容时,首先抓到的一般乞丐,直接送到救济院,或直接送到各收容单位。至于抓到的小偷扒手,则先送人民法院,经判决后送救济院,然后由救济院根据不同情况送到各收容单位。“各收容单位所收容之乞丐,须先经医生检查,然后办理入所手续。乞丐所带之物品,除讨饭工具没收外,其余的代为保存,并发给存据以备将来依据领取原物。经过谈话后,发给毯子、手巾(面袋做)、碗筷各一份。育幼所收容的乞丐,衣服特别褴褛的,尽可能的予以更换,然后编班进行教育。”[3](P600)从5月27日到6月3日共收容854人,市面上的职业性乞丐基本肃清。 2.收容所内的管理和教育 随着城市大批乞丐被收容,北京市各收容单位对收容的乞丐施行生活管理、教育改造,使他们能够在短暂的收容生活中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思想观念,改造他们成为社会上自食其力的生产者和劳动者。 1.加强生活管理 收容入所时,处理乞丐委员会就采用了“随收随编班的方法,每12人为1班,选择表现较好的乞丐,暂任正副班长;每3班为1分队,设分队长1人;3分队为1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各1人(正副中队长由原收容的乞丐找其有经验的暂时担任)。如因疾病残废不能编班者,组织特殊班,以特殊方法管理之”,在改造期间,又“经过教育了解后发现积极分子并抓紧培养,有计划有步骤的将各班长、各分队分队长,予以适当的调整”。这不仅使乞丐过上了有组织的生活,有利于培养其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而且通过积极分子担任的队长等参与管理,便于“经常的将我们的政策自上而下的灌入乞丐群众”,“使乞丐自下而上的向组织提供问题及意见,”[3](P601)从而实现对乞丐们的民主管理。“为了克服乞丐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3](P601),各收容单位根据收容之对象不同,订立了作息时间表及生活规则。乞丐们必须按生活规则行事,并且每日须按一定时间起床、睡觉、吃饭、学习、锻炼及娱乐,这样,将纪律观念教育贯穿于各个生活环节,培养了乞丐们良好生活习惯、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同时,收容所还要保证乞丐们能吃饱穿暖,稳定他们的思想以使他们能专心接受改造。乞丐“每日每人小米22两,菜金22元,大家集体吃饭,因收容单位情况不同,有的每日2顿,有的每日3顿,不管2顿或3顿,生活待遇是一样的,吃的是窝头、高粱米、菜是菜汤和咸菜,每隔七八日改善伙食一次,如遇过节和特殊事情时,还能吃到白面、大米及猪肉。”[3](P602-603)例如,平民习艺所,端午节曾吃两顿大米饭,每5人发给牛肉罐头一筒。乞丐收容居住的地方,因各收容单位客观环境不同,有的较好,有的稍差一些,但也比乞丐往日露宿街头好很多。在疾病治疗方面,“由卫生局和巡回治疗队巡回治疗。”为了防止疾病传染,“卫生局曾在各收容所喷洒DDT,扑杀虱、蚤、病菌。”这就给收容的乞丐创造了清洁卫生的环境。[3](P601) 2.加强教育改造 当时收容所主要通过政治学习和人生观教育,帮助乞丐树立自食其力的劳动思想。除每日给乞丐们定时上课之外,还天天组织讨论会。在教育方针上,本着教育改造,使其脱离寄生生活,积极主动参加劳动为目标。采取的步骤是:“第一,首先说明我们收容的目的,解除其思想顾虑,稳定情绪。第二是诉苦,各自述说各自的痛苦经历。第三,帮助他们认识这些痛苦‘是由于地主的剥削与蒋匪之绑架抢劫等种种原因造成的’,引导他们认识谁使我们穷困。第四,指出当乞丐是可耻的,是被人所看不起的,过寄生生活对人民对社会是有害的。第五,树立劳动观念,劳动是光荣的。”[3](P612)这些教育实际上是推翻其原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灌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自从学习了“收容的目的”、“先苦而后幸福”、“寄生生活的前途”、“树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及劳动是光荣、不劳动是耻辱”后,乞丐思想逐渐转变,绝大多数否定了原来的寄生思想并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如平民习艺所乞丐孙某某说:“我决心参加劳动生产,不再作社会上的寄生虫”。又如儿童张某某,“初到收容所时情绪不安,总想逃走,自从学习了‘劳动是光荣、不劳动是耻辱’后,决心参加劳动大队,干部们劝他年纪小不适合这种工作,但他拍着胸脯说‘我有力气,一定参加劳动大队,为人民服务。流浪街头以讨饭为生是耻辱的事情’。”[3](P606-607) 除政治教育外,干部们也用行动也感化乞丐。“干部们经常和他们在一块,给他们上课,进行个别谈话,使他们感到些温暖可亲,改变了日伪时代和国民党时代所给予他们对收容的恶劣印象与恐惧心理。”[3](P612)干部们对乞丐“不拘不束的有什么说什么,安慰乞丐,教育乞丐,替乞丐解决问题,帮助乞丐写家信,并督促乞丐洗澡、理发,衣服破了、鞋不能穿了,尽可能的予以更换,乞丐们在外存放的东西,协助找回来。干部们不断深入群众和乞丐们聊天或谈论问题。”[3](P603)由于干部们的热诚相待,对他们进行真诚的关心和帮助,感动了不少顽固不化的不良分子,使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渐有了改变和提高。 3.对乞丐予以妥善安置 经过收容所对乞丐进行教育改造后,北平市处理乞丐委员会区别不同情况,对收容所的乞丐进行了妥善安置。 首先,对于69名“包括8岁至14岁的男女”童乞,加强管制教育。截止到1949年7月,“25人根据天资、年龄、文化程度,分别编入育幼所初级小学里,随原有的求学儿童—起上课”,其余“44人已筹办识字班准备较长时间教育,现在该所负责同志每天领着他们学习、游戏、工作。”[3](P608) 其次,对于愿回籍又无办法者,由政府统筹处理。依照华北区处理乞丐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沿途由各县招待所招待食宿,并有各地民兵递送至各指定地点”[3](P609),截止到1949年7月,“处理回籍人员155人,其中属于津浦线者62人,平汉线24人,平沽线3人,平沈线16人,平郊20人;其次因家距平太远,目前无力使其返乡者7人(多系国民党流散军人,已送安老所)。送妇女教养所12人,经保释回家者2人。”[3](P609) 第三,对于641名无依无靠的老弱残废及重病的乞丐,除经证明取保回家44人外,“其余准备长期收养在安老所内”。稍有劳动力的搞些力所能及的生产,或“组织起来(伙夫队、清洁卫生队、警戒队各十人)辅助年老残废的乞丐,处理日常生活一切零碎的事情,如不能到厕所大小便的乞丐,使其能进入厕所等”。另外为防止传染,设“重病号房间,使重病的人或传染病的人和没有疾病的人隔离起来”。[3](P609) 第四,对于有劳动力而无家庭负担的乞丐,编成劳动大队,赴各指定地点参加劳动生产。到1949年7月,已先后送走两批。“第一批124人,赴黄河修堤;第二批138人,赴察哈尔修堤及开荒。”[3](P609)劳动大队出发时高举劳动光荣的旗帜,边走边唱,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沿途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在劳动大队出发经过安定门时,当地居民说:“这些小伙子过去真厉害,不给钱下不来台,要多少给多少。小偷们更凶,偷罢东西有钱了不干正经事,吃喝嫖赌一齐来。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都变成好人了,参加劳动生产,以后这些小子,可不能再来了。共产党真有办法,使流氓小偷也能变成好人。”一位卖油条的说:“今后每个人都得劳动生产,不劳动不行了。”[3](P610) [1]马维刚编:《禁娼禁毒》,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1949:北京全面禁娼》,《人民公安》2003年3期。 [3]《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4]北京市档案馆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5]北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6]《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2日,第1版。 [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8]张洁珣:《1949:北京向妓院开刀》,《纵横》1998年第10期。 [9]米士奇、高长武:《解放初期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工作——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 [10]《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11]《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12]《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5期。 [13]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乞丐问题材料》(1949年),北京市档案馆,196-2-191。 [14]《北京市公安局对收容乞丐工作总结的意见》,北京市档案馆1196—2—19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