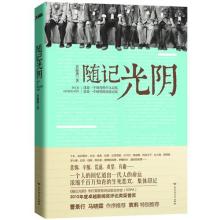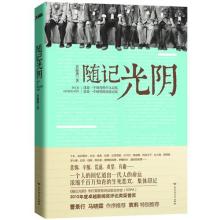下乡第二年,我搬来与长禄合住一间小草房。这房子的房东是杨三爷。 长禄是队里的会计,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早先,他一个人住这间小草房,理由是会计需要一个办公的地方,算账,存放账本、单据和其他公共财物,兼带住宿。恰好杨三爷家有闲房,说好了队里每年记200个工分,长禄就搬进来。也住了两年多时间。他叫我来住,起因是想叫我帮助他搞队里的秋季决算。 长禄对我说,你晚上来帮我算账吧。他告诉我,队里的秋季决算快要开始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要是能帮助他就好了,白天可以不去地。 又说,决算很有意思,你不是想多知道农村的事吗,来这里下乡几年,要是不知道夏秋季决算,算你白到农村来一趟。 说得我心痒。我决定搬来,想看看什么是秋季决算。 长禄他哥是大队革委会主任,“文革”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长禄能当上会计,估计也是沾了他哥的光。他初中毕业,在我们队算学历最高的,身体又较弱,自从当上会计,便不怎么下地干活,队里给他工分补贴,足以使他的收入在队里处在中上等水平。 说实话,长禄对我很好,自认为与我无话不谈。他有时做下不堪之事,说话时也不背我,或者多吃多占公家便宜,还记着喊上我。队里有几个泼皮围着他转,给他出坏主意,唆使他寻乐子,自己得些蝇头小利。有时候,长禄与几个泼皮在小屋里嘀嘀咕咕,商量着做坏事。我很讨厌其中一两个猥琐小人,长禄知道,也不怪我,见我进屋,忙使眼色叫那人走。 我搬过去后,长禄叫我先把全队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每个人名下的工分统计出来,这是决算的基础。 我开始统计工分,重新画工分名册,画统计表,每天忙叨叨的。 生产队长老砖头也在社员大会宣布,队里已经开始秋季决算,今年乔海燕帮助长禄算账。他叫大家支持我的工作。 老砖头宣布以后,我马上就发现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原先人家总觉得我是从城里来的学生,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我。现在,几乎全队的人都用一种对长者尊敬的眼光看我,用晚辈那种亲切、和善的口气与我说话。我只要提出想要什么,就会有人搞到,飞快送到我手上。队里年轻人传看一本故事书《佘赛花》,我很喜欢,等了好长时间也轮不到,现在,我连想都没有想,这书就乖乖来到我手边。中午吃饭时,我从小屋出来,伸伸懒腰,四周的人家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我。我回女生住处吃饭,一路遇到的人家都忙不迭招呼我,搁这儿吧……搁这儿吧……这是代营人饭时的客套话,此时,其热情、真诚,却使我真假莫辨。 开始,我还陶醉于这种被营造出的奉承气氛中。过了几天,半夜细细想来,却觉得不安,工分竟有这么大力量?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即使算错了几分几十分,又有什么? 一天,我正在屋里扒拉着算盘,一阵忙碌过去,听见门外有声响。我以为是鸡挠食,没有答理。过了会儿,又听见同样的响声,伸过去头一看,是人称“群叔”的刘富群蹲在门口。 刘富群见我看他,忙站起来笑,跟着就钻进小屋,蹲在门口抽烟。 有事吗,群叔?我问。 他忙摆手,连说“没事”,蹲着继续抽烟。又说,听着你打算盘,一片响亮,真好听。他瘦,面皮褶皱像干萝卜一样,此时却是一片笑意。 我也不知好歹地“嘿嘿”笑,享受着奉承。 刘富群是队里有名的“受气包”。他家是中农成分,这个成分使他在村里有时候处在尴尬地位。如果没有政治风波,群叔的家倒是值得羡慕。父亲传给他一份家业,土改前家里已经有了些积蓄,盖了三间瓦房,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各样农具齐全,院子里栽着枣树、核桃树,甚至还种了一丛栀子,春天开花非常好看。但是,如果形势收紧,有了政治运动,他家就被隔离开去,置于社会边缘。那根收紧形势的小绳子,有时候并不见得在北京,也不在县里,更不在老砖头手里,而是在长禄们的手里,任由他们牵动。 刘富群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名刘春河,小名狗剩儿。狗剩儿快三十了,瘦瘦的,筋筋巴巴的样子。刘富群给狗剩儿娶了媳妇在家。媳妇叫玉荣,倒比狗剩儿高出半头,且长得丰满,就是皮肤微黑,龅牙,看人时翻着眼白,给人怪怪的感觉。玉荣嫁过来时,刘富群摆了十几桌,有酒有肉,请了大队、生产队、村里有头脸的人来,猜拳划枚,搞得很热闹。 有一次我和长禄闲聊,议论着队里各色人等。说到玉荣,我说,这个人看起来怪模样,黑黑的脸,看人眼睛斜视,我不敢看。长禄就怪笑,说,你看她走路,前面挺着,后面撅着,到晚上还不把狗剩儿吸干了?说完又笑。 我不知道长禄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听村里人说,狗剩儿结婚两年了,玉荣还没有怀上孩子。 到了晚间,我对长禄说起刘富群来的事。长禄眼睛顿时闪光,喜滋滋地说,肯定是冲着工分来的。 他对我解释,现在我汇集起来的全队社员工分:一则不可能是全部,总有遗漏,重新统计的意思,就是要把遗漏查出来,尽量补上;二则已经统计出来的工分中,还包括一些未能确定的因素,比如,从户家出一挑茅子,从猪圈出一车肥,值日的承贺那里只有数量记录,也写明是人猪羊鸡之类。但是,具体分值多少,要在最后统计时才确定,这里就有很大改动的余地。 那要谁才能确定?我问。 长禄笑着看我,说,咱俩就能定。 长禄说,分,分,社员的命根儿,这话一点不假。每年分配,免购点(口粮)按人头固定数量,自留地按户家人口固定数量,油是按人头平均,其余的东西,余粮、棉花、钱,都是按工分。尤其是钱,一个人使多少钱,就看你挣多少分。还有余粮,靠免购点不够你吃三个月,要想多分粮食,就得靠工分。 那就是说,每年分配,有平均一块,还有多劳多得一块。我说。 长禄说,对,1958年吃食堂就是大平均,到了第二年饿死人时,也是大平均,吃死是平均,饿死还是平均。 他又说,所以毛主席又从公社退回来,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分配的点落在生产队,才能多劳多得,要是还放在公社,人也不知道死了几遍了。 又说,主要还是靠平均,因为能多劳多得分配的实物、现金很少,所以大家都很计较工分,你在这里算工分,咱队多少人的眼睛盯着你呢。 我当即表示,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不辜负队委会对我的信任。 果然,刘富群又来我这里蹲了几次,还要给我递烟。随后,就小心提出想看看工分统计表,说,只看自己一家的,不看别人的。 我告诉他肯定不行。我说,你就是能看到,也是在长禄手里看,我这里不行,这是队委会立下的规矩。 他听我说,只点头,连声说:“好!好!”似乎很满意的样子。 我心里却稍稍鄙夷,看不起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事。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改变了对刘富群的看法。 那天,我去地里找妇女队长,也是为工分的事。 秋庄稼已经收完,田野广阔,娴静,又舒展。极目远望,淡淡的蓝天游浮着几丝薄云,蓝天下,一座座村庄,一块块田地,还有公路,都静静地卧着。 我远远看见一群妇女在地头歇着,其中有妇女队长,还有几个“官太太”——支书、主任媳妇妹子之类。走到近处,看见刘富群独自歪斜着靠在一道沟坡旁,几个妇女正撩拨他。 刘富群有疝气,不能干力气活,就是在田里干活,逢到疝气下来,也要独自蹲下挤回去。只见他翻身蹲下,妇女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几个人发声喊,围了上去,将他撂翻,伸手就扯他裤子,几个闺女忙叉着指头捂眼睛,妇女队长领着几个娘们儿在一旁嘻嘻哈哈加油助威。刘富群嗷嗷叫,使不得!看不得!哪能挡住一群虎狼女人!霎时将他裤子扒掉,远远扔到一边。剩下他捂着那话儿仰脸躺着,也不知道翻个身。妇女们哈哈大笑,有人捡起土坷垃砸他,有人攉过去一锨土。 我看着挺有意思,也忍不住笑,想着那些妇女真大胆,城里可看不到这么有趣的景致。我招手叫妇女队长过来,喊着她,有事问你。 只听几个妇女说,算工分了,算工分了。起来看妇女队长过来。 刘富群一骨碌爬起来,呆呆看着我和妇女队长说话,裤子也忘提了,滴里耷拉的,大概他都忘了。 晚上我对长禄说到地里一幕,他说,俺嫂子在那里,群叔也是故意的,叫那些妇女们解解闷儿,讨人家个高兴。 我又可怜刘富群,说,一个男人,一家之主,群叔家又是个中农,难啊! 你可别说这个。长禄对我说,你没有看他坑你、占你便宜的时候,叫你恼死他。 第二天,狗剩儿的媳妇玉荣来我住的小屋,说东说西,没有正经话,又问我有指甲剪没有,听别人说我有一个,用着很方便。说着就凑到桌子跟前,眼睛却瞄桌上的账本。 我看出她的心思,故意不阖桌上的本子,转身在床头找指甲剪。感觉到玉荣悄悄翻账本。其实,那上面什么也没有。而且,她未必能看懂。 我又可笑这一家人,装模作样的,为讨有权人家高兴,不惜自辱其身,就是为了那点工分嘛。自己好好劳动就行了,总想着投机取巧。 但是我也想,群叔家是中农,政治上无地位、无权势,长禄这种人想怎么欺负他都行,故而低三下四,可以理解。 到了晚上,长禄和一帮泼皮朋友在屋里说笑,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 我听长禄起头说,要算计玉荣。他一开口,几个帮闲者嘻嘻哈哈都添办法。毕竟这种苟且之事,我就在旁边,开始几个人嘀嘀咕咕,还小声背着我,说到高兴时,笑声大了,我也能听见他们说的意思。偶尔回头看看他们,说话的人就住口,长禄冲着我笑,对那几个同伙说,没事,他不管这事。说实在,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他们说的,我真听不太懂,只觉得他们想欺负玉荣,想侮辱她,究竟什么叫“侮辱”,我只看过小说上有日本鬼子强奸中国妇女的描写,也仅此,终还是不明白。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在屋里算账。长禄下午就告诉我,喝罢汤去县里看电影。喝汤是代营方言,就是吃晚饭。 我们俩有个约定,谁回来晚,另一个就等着。小屋有电灯,长禄喜欢看小说,他总能搞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书。这是我一直与他合住的原因。我很喜欢独自在夜深人静时看书。 我正忙着,门外有人咳嗽,开门看,竟是刘富群。我想起长禄他们说算计玉荣的事,心里吃惊,担心出事,就问他。他支支吾吾不说,探头往屋里看,问,长禄不在啊。 长禄去大队开会了,我随口应付他一句。我不是恶意,但是,又确实故意不说实话。 大队开会?我将(刚)从大队那边过来,黑着灯呢。刘富群迟疑地看着我说。 谁知道,又去哪儿跑着玩了吧。我含糊地说。 他转身走了。以后的几天,我独自复原这次事件的过程时,想,那天晚上群叔来小屋找长禄,不是找人,而是确定长禄不在屋里。 一直到很晚,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几声说话和嘻哈,长禄和几个泼皮钻进屋来,互相揶揄、讽刺,坐下就吸烟,你一句我一句递话。 我看他们,眼睛都躲着我,感觉他们有鬼,就问,看什么电影? 几个人支吾着,《白毛女》?《红灯记》?说来说去说不清楚。 然后几个人又自顾说,不一会儿又兴奋起来,手舞足蹈的。 我仍然埋头整理账本,耳朵断续听他们说话,大致拼凑出一幅作恶图: 上午,长禄遇见玉荣,悄悄告诉她,晚上县里有好电影,要是愿意去的话,他骑车带她。 玉荣脸上犹豫,不吭声走了一会儿,见长禄落在后面,又回头看他。长禄是风月场的老手,鬼精明,又存着心,见玉荣回头,知道她同意了。 长禄有一辆“永久”加重自行车。喝罢汤,他一个人推着车在村口等。黑地里见玉荣悄悄摸过来,两人只“嗯”了一声搭腔,谁也不说话,长禄骗腿儿上车,玉荣扭屁股坐上,两人一路往县城去了。不远,几个泼皮在后面尾随着。 等到电影演完,两人又骑一辆车回村。那长禄有心使坏,车子把扭来扭去,晃得玉荣只好紧紧抱着他的后腰,连声责怪他。两人一递一句说话。 长禄将车骑上一条旧土路,玉荣先是“哦”了一声,意思是怎么走这条路。 长禄也不说话,依旧扭来扭去,似乎顾不上,走到一处暗地,眼见路旁一道沟壕,也是早就选好的地方,便连人带车滚进沟里,还没等玉荣叫一声,便被长禄搂抱住。那玉荣也是早就料到有事,本来就是甘心送上,到了此时,便躺在沟底不言语了。那长禄便下手将玉荣剥脱干净,恣意取乐…… 那几个泼皮远远见长禄滚下沟去,便停住车,四处张望着放风。 月光底下,黑夜静悄悄的,哪有半个人影。 这件事以后,刘富群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还故意问,群叔,你怎么不去我那里抽烟了? 他默默走路,没有吭声。 突然,我看见他抽泣起来,苍老的、干萝卜似的小脸上,滴答着串串泪水。他可怜巴巴地对我说,兄弟,俺没有办法啊…… 不久,队里给知青盖了新房,我就从长禄那里搬出来。 有一次,我回城,临行前,长禄对我说,你回去帮我找一样药,有了,买点带回来。我问什么药,他给我一个纸条,写着药名:新胂凡钠明。我回去后,竟把这事忘了。回来后,长禄也没有再提起。 几年以后,我在护校上学,一天上药理课,我突然想起此事,下课便问老师,新胂凡钠明是干什么用的? 讲课的老师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我,问,你问这个药干什么? 我告诉他,过去曾经听一个人说过,今天突然想起,就问问。

抗梅毒药。老师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