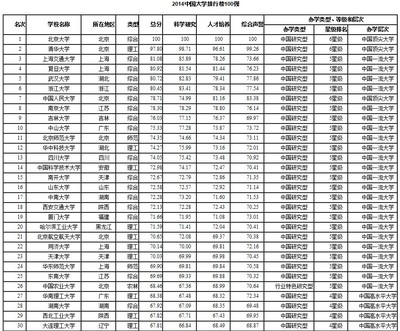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在1952年,燕京大学校园成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的学风至今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燕京大学著名的校友王钟翰、王世襄、黄宗江、张广达、江平回忆在校学习的故事,再现旧时学风。 王钟翰酒事 1934年,王钟翰在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却颇有名气。王钟翰的老师是学术史上卓然成家的邓之诚、洪业、顾颉刚等人。 王钟翰研究过母校的历史:燕大成立于1919年,是美、英等国教会出资兴办的,校长由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当时燕大并没有多大名气。后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聘请著名学者任教,才声望日隆。男女两部先后由城内迁至京城西北部本校,至1928年已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共设十余系。学生约800人,其中女生占40%左右,是当时全国各大学中女生最多的一所大学。 在燕京大学,王钟翰得过好几次司徒雷登奖学金,每次200元,一年的学费、生活费都差不多够了。多年后,王钟翰被划为“右派”的罪名竟是:得过司徒雷登奖学金,对司徒雷登有感情。王钟翰对司徒雷登的印象是:“我觉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也等于政治家,说话很有技巧。不多说,巧说,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才说。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教授、活跃一点的同学都记得。” 当时的燕京大学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王钟翰在同和居喝醉了酒,过马路的时候摔倒在马路旁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王钟翰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王钟翰的老师洪业,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王钟翰的宿舍,让王钟翰去他家里。王钟翰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王钟翰:“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是王钟翰不要去外边喝醉。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 美国和日本还未开战时,日本宪兵队不敢进去燕京大学。日本的宪兵队长叫华田,平时穿着便服,枪掖在衣服里,经常到燕京大学“访问参观”,司徒雷登不得不留下他们吃便饭,就在临湖轩—未名湖南畔。日本人爱喝酒,华田提出来要跟燕京大学的老师比赛喝酒,当时在座也有洪业,正好王钟翰在学校,司徒雷登就让洪业叫王钟翰去陪酒。宪兵队长华田也讲中国话,说今天比酒,全用瓶子喝啤酒,每个人喝十瓶。王钟翰觉得啤酒醉不了,就跟他比。结果对方喝了九瓶酒就掉到桌子底下去了,王钟翰喝了十瓶还没有什么事。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师生都去游行抗日了。日本宪兵开着大卡车,逮捕了10多个教授,把洪业、邓之诚都带去了。但是王钟翰没有被带去,大家就开玩笑说,宪兵队长华田怕再次看到王钟翰,所以就没有捉他。 邓之诚讽刺胡适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邓之诚、洪业、顾颉刚三人风格迥然不同,但关系很融洽。王钟翰向邓之诚请教学习的门径时,邓之诚告诉他,有两部书要反复读,百读不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都经世致用、治学严谨。洪业曾留学美国,眼界开阔,治学善于中西对比,致力于建立历史学科的规范,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历史学家。顾颉刚则被誉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其“疑古”精神对王钟翰后来致力于清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抗战时期,王钟翰有幸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手。 邓之诚有《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学术名著问世。王钟翰回忆:“邓先生是世家子弟,曾祖是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曾经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他年轻时很热情地参加辛亥革命,到处宣传革命。他没有念过大学,但是国学底子深,记性很好,思想也活,作诗作词写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是‘桐城派’,没有过多的之乎者也,叙事简练有起伏,很不错。他作派比较旧式,在燕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姨太太,以前本来是他的侍女,帮他生了儿子,成了姨太太。所以,那些外国老太太借这个理由去向司徒雷登告状,说:‘这像话吗?都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了。燕京大学里边还有姨太太。’司徒雷登后来找到洪业先生。洪先生就说:‘哎,他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士大夫都有姨太太,宋朝明朝士大夫请吃饭,每一个人都有姨太太、艺妓陪酒。日本、韩国也是这样。’他还告诉司徒雷登先生,邓先生人品好、学问好,有个姨太太是私生活,不要去管。” 邓之诚常常讽刺胡适、傅斯年,讲课中间就问学生:“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 洪业的风度

洪业在燕京大学教书是另一种风度。王钟翰回忆:“洪先生不讲课则已,一讲课就会引人入胜。他上课说:‘你们睡觉吧!’但是一个人也睡不着。他声音大,经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话,教室里经常哄堂大笑。洪业先生是比较西式派头,上课时西装革履,叼着烟斗,邓先生则是旧式派头。以前他们出身差不多,都是世家子弟。洪先生到美国留学,会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几种语言。”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王钟翰看了也觉得不是纪晓岚的笔迹。所以洪业让他写一篇文章“辨别”。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他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王钟翰记得当时稿费是27元,算是很高。他很高兴,就请同学吃一顿。后来,他把文章拿给邓之诚,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王钟翰多年后悟出:“后来,我知道了原因,是因为写法不一样。因为洪先生不但是旧式的考据,同时吸取了英美、法国的方法。邓先生还是旧式的方法。邓先生在写《清诗纪事初编》的时候,节衣缩食买了大量诗集,凡是清朝的诗文集他都收集,今天可能买了一部顺治年间的,明天可能收集到一部乾隆年间的,精心筛选了几百部最好版本的诗文,但是他写文章很精炼,就是写他最推崇的顾炎武,也不过是两千字。” 抗战胜利后,王钟翰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从哈佛大学回国后,王钟翰致力于清史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由清史研究转入满族史研究,1957年,第一本结集《清代杂考》出版,而后出版《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主编《中国民族史》,成为清史和民族史学界的一代名家。昔日燕京和哈佛的学友中,王世襄成为成就斐然的文史专家;周一良成为史学名家,“文革”参加“梁效”,有《毕竟是书生》问世;瞿同祖于1965年回国,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馆,除政治学习外,无所事事,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有《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问世;杨联留在美国,成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大师,培养的学生有余英时。 王世襄揣着蛐蛐葫芦上课 王世襄是王钟翰在燕京大学的同学。王钟翰回忆:“我跟他是同系同班。他上大学不读书的,听完课就走了,但是他很聪明,考试成绩很好。他玩小蛐蛐玩得很好。王世襄的妹妹在燕京大学也是很出风头。” 王世襄是一个玩主儿,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蛐蛐葫芦上邓之诚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他本来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他去见傅斯年。一见面,傅斯年对王世襄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王世襄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王世襄第一份工作就能天天和梁思成、林徽因相处,受益匪浅。他深情地回忆:“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 黄宗江以恋爱为主 在燕京大学的校友中,黄宗江是另一类型的玩主儿。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炸毁了南开中学,黄宗江到英租界耀华中学念了一年下午上课的特班,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黄宗江回忆:“自己在校园的生活或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失恋后,燕京大学三年级的黄宗江离开校园,到上海演剧。 对抗战期间的燕京大学,黄宗江这样回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到了重庆,既见了蒋介石,又见了周恩来,都拜托他们,在沦陷区开大学。原来燕京大学就招200人,1938年招了700人,我们当时只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可以考,我17岁就上了燕京大学。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基本上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我的旁边就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什么也不是,我是醉生梦死。后来我一个女朋友要为别人自杀,我就去了上海演戏了。燕京大学念了第三年就走了,回来念第九年大学,也没毕业。” 在燕京大学,黄宗江跟司徒雷登接触过。他回忆:“司徒雷登跟学生很接近的。当时我游泳是横渡昆明湖冠军,他一见我就要提:‘怎么样,最近游泳没有啊?’当时有人说他是‘老狐狸’。其实他是爱护学生的。后来我要走了,我就去找文学院院长,我说:‘我有抗日问题,我要休学。’他说:‘你等等,我研究一下。’他就报告司徒雷登了,司徒雷登下午就找我。当时日本人占领北平了,司徒雷登是跟日本人不合作的。司徒雷登跟我说:‘你不离开校园,我保证你安全。’那时候日本人不敢进学校。而我根本就没有抗日问题,我胡诌的:‘我非走不可。’等1946年我参加美国海军回来时,校长已经是陆志韦,司徒雷登当美国大使了。” 在燕京大学西语系,黄宗江主要读英文、法文。他说:“杭州有一个徐朔方,温州有一个唐湜,都读西语系,因为觉得中文可以自修。我们在上中学时诗经、楚辞都念过了,觉得不用上课,但是西语我们需要上课,我们上西语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搞中文。我当时已经对写作感兴趣了。燕京大学基本上是洋人多,还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空气很浓,爱国的空气很浓,这些都是潜移默化。幸亏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绝对是好人。” 黄宗江原来读的南开中学有戏剧传统,到了燕京大学就搞起剧社,在学生活动中演《雷雨》。当时孙道临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受到感染也开始喜欢演戏。黄宗江说:“孙道临是学哲学的,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长得很帅,是我拉他演戏的。”后来孙道临在一篇文章中说:“假如没有黄宗江,我根本不会演戏。” 从燕京生变成了北大生 张广达的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成教授者。张广达回忆:“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近代科学图书馆;在读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謦,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所有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到西郊,以燕园为校区,燕京大学取消。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而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张广达进入燕京大学时,还能感受到教会学校的味道:“赵紫宸当院长的宗教学院,还有一些团契在。我当年出于好奇,也参加过一些团契的聚会。燕京的三年,尽管它是在抗美援朝以后收归国有的,把教会学校取消了,但是,我对西洋文化有些基本的概念,就是那之前两年半留下的。俗话说,先入为主,确实,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欧文化哪怕有一点粗浅的了解,再接受教条,往往有所存疑,不再容易原样吸收了。” 张广达很早就注意念外语,注意西洋史、中国史并重。燕京大学历史系中,聂崇岐跟张广达的父亲张锡彤是好朋友,对他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课外指点。而翁独健在燕大历史系开了一门蒙古史课,后来由于运动就没有接下去了。在讲蒙古史的时候,翁独健介绍蒙古研究的国际行情,他本人是在哈佛大学念的,跟在柯立夫的门下。所以他很早就介绍并推崇巴托尔德(V. V. Barthold)的书,就是张广达和父亲张锡彤翻译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翁独健是进步教授,言谈没有什么顾忌,那时候又还没有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自由,他说:“中国也得出一个巴托尔德。” 这时,燕京大学的校友王钟翰已经成为教师。张广达回忆:“王钟翰先生开始教清史,因为他当时在燕大的贝公楼顶层的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研究室,他在那儿念《清实录》,很勤奋。他把研究《清实录》的成果拿来给我们讲,讲清初的拜堂子等风俗习惯。他有时也把他的老师邓之诚请来上堂课,所以我也听过邓之诚先生的几次讲课。邓先生的儿子叫邓珂、邓瑞,是比我高两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学,有时我跟邓珂、邓瑞来往,也跟随着他们去邓先生家,坐在客厅里面,跟着王剑英等研究院的师兄们一道听听老先生说这说那,他对掌故非常熟。” 张广达记忆所及,大概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同时为了配合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在这些教会学校首先开展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运动,为打倒美帝在燕京的代理人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铺平道路,进而引申为教授们向党交心、思想改造运动,然后趁热打铁,进行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张广达从燕京的学生变成了北大的学生。当时的新北大在张广达看来也颇为有趣:“老北大、燕京、清华合并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大牌教授,校园内简直抬头就是大师,哲学系、中文系、文学研究所、历史系、外语系、经济系等大师密度之大,今天颇难想象。那时候,中文、历史集中在文史楼二层,西边是中文系,东边是我们系,挤在东头角落里的是图书馆系,图书馆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刘国钧、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有意思,那时候北大拥挤着那么多大牌教授,却没什么人出来带头拥戴他们为大师,今天没国学了,反倒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冒出大师。” 江平:我们应视司徒雷登为朋友 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既沐浴了燕京独特的学风,也亲历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1951年,江平由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此时他对法律一窍不通,而且没有兴趣,但服从安排。他说:“那时候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新闻是很热情奔放的,更自由一些,法律有点按法律条文来办事,比较保守一些,所以这两个职业是不太一样的。总的来说,法律是比较保守,新闻是更开放一些。所以我自己的第一志向就是学新闻。”江平赴苏后,先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系,195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接受了正规的法律教育。此后的人生,江平与法学相伴。 江平在80岁自述《沉浮与枯荣》中深情回顾了燕京大学的历史。他说:“燕京大学跟哈佛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的哈佛大学里面,还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还有一个燕京图书馆。美国的教会到现在,还仍然给哈佛燕京学社拨款。在美国甚至有人主张,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同意在大陆恢复燕京大学,那么现在仍然可以使用这笔钱。” 关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民众多从名文《别了,司徒雷登》认识他。司徒雷登生前有一遗嘱,希望死后将骨灰回归燕园,与他的妻子埋在一起。司徒雷登的妻子在1926年病逝于北京,她的墓是燕大坟园中的第一座坟墓。然而,司徒雷登骨灰回归燕园之事,一直是一波三折。最后,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他的出生地杭州,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遗愿,但毕竟回到中国,也算部分地了却司徒雷登的遗愿。 江平认为:“司徒雷登一直是传教士,从来就不搞政治活动,只不过在历史关头担任了最后一届美国驻华大使。他一辈子的心血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我们应视其为朋友,不要将其当做中国的敌人来对待。现在我们看待国外的传教士,需要认真分析,不能一概一棍子打死。我们讲汤若望、利玛窦,在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都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司徒雷登一生几乎都是为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应该说,这些人给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肯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