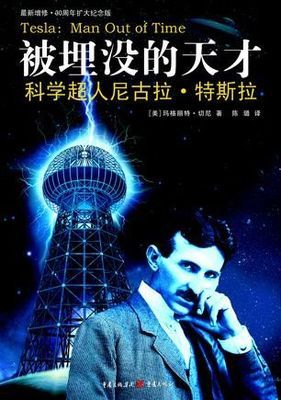第五章 固执己见的创始人
俗话说,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们也应该学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或者也可以说,正确的判断来自于经验,而经验则来自于错误的判断。
姑且不讨论这些道理的真伪,但我的观点是,我宁愿得不到实践带来的启发,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去尝试失败。我更喜欢从别人的失败中去汲取教训——但不管是谁的错误,还是损失越小越好。我们在学习如何激励和管理人以及如何以身作则的时候,绝大部分正统理论是来自于我们直接或间接观察他人对逆境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通过他人的得与失,就会形成我们可以汲取的教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荒谬。或许本该如此——我的父亲和塞尔·刘易斯,就是我的最佳观察对象,尽管他们在性格或很多特性方面迥然不同。最典型的事例:我一直认为,对兄弟们的忠诚和责任一直是父亲在事业上最大的障碍。请不要误解,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重要——我的妻子和她的家庭,还有我的儿子和孙子孙女,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我的所有表亲,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因此,我一直非常谨慎地避免任何有可能伤及这种关系的事情发生。我曾经提到过,我的父亲是六个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他却是整个家庭中的老大。父亲总能妥善、冷静地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说实话,我确实也很关心他们,但对很多人了解太少,以至于很难产生尊重与亲切的感觉,但父亲的方式让我相信,我永远都不想做这样的事情,貌似容易,实际上很难。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经常会听到某个叔叔在工作中不卖力、不负责任以及由此造成何等后果之类的事情,我几乎已经听得厌烦了。这似乎为我理解帕金森定律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企业雇用家庭成员人数越多,相互之间产生怨恨的概率就越大,因此,雇用大量家庭成员会对利润带来负面影响。第五章固执己见的创始人于是,到了1960年,当大多数人还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却没有浪费时间,而是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我的风险套利部助理叫艾迪·荷西,他是一个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有一天,他确实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和我的妹妹迪安妮谈恋爱。我马上意识到,必须解雇他。尽管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尽管我自己也不想这么做。就在他们准备结婚之前,他的母亲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的解释是,我只是不想和自己的妹夫共事,这与不想让孩子长大后和我共事是一个道理。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针对裙带关系的政策,但我心里有数。到1971年的时候,我无意间意识到,包括我本人在内,贝尔斯登的25位合伙人有30个年龄在10~15岁的孩子。我觉得,正式起草这样一种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个备忘录式的政策并不仅仅限于合伙人,它要求公司不得雇用任何与公司现有员工有亲戚关系的人。我们希望让贝尔斯登这个组织免受亲情的干扰。最初,我预料到可能会遇到阻力,但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没有遇到异议。从来没有人认为泰德·洛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想法做,就会失去很多有天赋的人。”“我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对泰德说,“但如果我们不那样做的话,雇用的也许是100%的笨蛋。”争论就此戛然而止。这项政策的规定不能不说事无巨细。它把家庭成员定义为“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儿媳、女婿、叔父、姑妈、姨妈、侄子、侄女以及孙子、孙女”。几年之后,塞尔把我和约翰尼·罗森瓦尔德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告诉我们,他有“大事”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事呢?“我想让我的儿子加入贝尔斯登。”塞尔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说的是长子桑迪。约翰尼和我甚至都没有交换一个眼神。我们都知道,这绝对是一件大事。“塞尔,我们不能那么做,”我说,“我们有明文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打破规定。”塞尔一如既往的固执。“但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得非常好。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子女带进公司,那就是带头违规。没有别的说法,规定就是规定,桑迪非常出色,他完全能到其他公司再找到一份工作。”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谈话就此结束。一周之后,一名叫马克·斯图尔特的贝尔斯登合伙人来找我。“你们一定要给塞尔的儿子想想办法。”他说。“马克,我们绝不会接纳合伙人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塞尔。”“这件事对塞尔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们拒绝这件事更重要。”只要塞尔还是贝尔斯登名义上的掌门人,这样的冲突就会偶尔一现。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而且一直竭尽所能地去尊重他、服从他,因为毫无理由的对抗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此外,自从多年之前我们在塞尔的公寓发生的那次分水岭式的对抗之后,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逻辑或理由。如果公司要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但冲突和征服绝对不会带来良好的文化。它只能来自我们对风险和机遇的客观衡量和理性判断。以宏伟蓝图或是豪言壮语来规划贝尔斯登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对长期规划的反感是尽人皆知的,我同样不赞成依赖外部顾问或是所谓官方言论。我的战略思维可以归纳为一切有助于提升员工士气的信仰以及有助于增加利润的友谊。无论市场涨跌,无论经济形势好坏,理性、自信和成本控制都将引导我们始终如一地勇往直前。每一年,我们的合伙人都将按照非合伙人的贡献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决定他们的年底分红。我必须保证公平原则的实现,就像我和约翰尼·罗森瓦尔德曾经立下的誓言,在我们的监督下,薪酬分配只能更公平。违背这些原则无异于自我摧毁。我一直在学习父亲如何对待自己的雇员,很多雇员在他的公司里工作了一辈子,对企业的忠诚和关心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应有的回报,更带来了企业对他们的尊重。在贝尔斯登,我亲身经历过很多高层管理人士对下层员工的傲慢和自负。塞尔认为我缺少交易员应有的感情和思维,他的评论并没有错,因为这与我作为一名管理者应有的风格是一致的。但不管我的内心世界藏着什么想法,都不应该在背后对人指手画脚。那些从最初就和我并肩工作的人,始终都将是我经营生涯中的朋友。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图谋不轨的事。我在1949年进入贝尔斯登的时候,合伙人的总资本为1 800万美元,9年后,在我成为贝尔斯登的合伙人时,公司的累积资本已经增加至3 000万美元。我们的年净利润全部作为留存资本。每个合伙人的薪酬只是相对合理的保障性工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税后年薪约为6万美元(2007年,也就是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经营年度里,高级执行董事的年薪已经达到了25万美元),外加该合伙人累积资本按6%计算的利息。此外,每隔两年,薪酬委员会会对分配利润在各合伙人之间的分配比例,按各自的业绩进行调整。这种每个人均把大量净资产再投资于公司的做法被约翰尼称为“契约性奴隶制度的绝佳形式”。这样,我们的制度就让合伙人很难提取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同样,撤资必须严格按规定由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只有彻底离开公司,合伙人才能变现其持有的股权——死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否则,支付学费或是购房款之类的非日常性支出,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资本账户随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紧急医疗支出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另外,有些特殊情况是默许的,例如,如果某个合伙人的家庭成员遭到绑架,执行委员会将允许该合伙人撤回资本用以支付赎金。这些特殊情况不需要通过投票一致通过。我与塞尔私下达成的否决权协议,让我享有一份不成文的特权:每天早晨可以和塞尔同乘一辆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和约翰尼·罗森瓦尔德以及约翰·古德菲里德(John Gutfreund)一起上班,加特福伦特当时在市政债券部就职,后来成为所罗门兄弟的CEO。加特福伦特开的是一辆绿色的“奥兹莫比”跑车,尽管我们可以搭他的车,但他却从来不让我们支付油费和停车费,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都愿意尊重的简单规定:不和他讨价还价。塞尔的汽车当然也遵守这个规定。当时,我已经搬到中央公园附近,就在我目前居住地点的东侧。每天早晨,塞尔都会在8点钟准时到这里接我。杰里·戈德斯坦是一家机构的销售员,他住在距离我半个街区的地方,他也和我们一起搭车上班。我、戈德斯坦和司机坐在前排——在那个时候,汽车的前排可以塞进三个人,塞尔和泰德·洛坐在后排。尽管从上车到华尔街只有几英里的路程,但即便是这么短的时间,塞尔和洛也难得不毫无意义地争论一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恨不得揪掉自己的头发,只可惜我已经没有多少可揪的头发了。杰里只是坐在那里傻笑。他经常告诉大家,到24号大街的时候,我基本已经昏迷不醒了,尽管那时还是早晨8点钟。|!---page split---|在我们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的口舌之战还在进行。在第一次听到塞尔提到零售业务销售员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些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人称为“站在最前排的傻瓜”,我并不觉得这很幽默,而且我对自己的感觉直言不讳。我曾听他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每次都会感到不舒服。我真不知道,一旦我们的销售代表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何感受,我几乎不敢想。我必须公正地评价塞尔,并不是他看不起销售代表,因为他对每个人都会出言不逊。1978年,塞尔去世,在他离开后,我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听说曾被他侮辱过的很多人表示歉意。为此,我曾向华尔街的顶级银行业专家、夏皮罗公司(M.A.Shapiro & Company)的莫里斯·夏皮罗(Morris Shapiro)道歉,也曾向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丹·莱根(Don Regan)致歉。在给投资者多元服务公司的董事长霍尔默·巴奇(Homer Budge)打电话时,我说,“我知道塞尔曾经对您……”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你指的是他说我太笨,以至于遇到下雨天就不出来的事吧?我已经习惯了”。贝尔斯登有一名叫弗兰克·琼斯的债券销售员找到约翰尼·罗森瓦尔德说:“我必须离开公司”。“为什么?”约翰问。“因为塞尔认为我是个笨蛋。”约翰尼告诉他不要当真,然后找到我,我们一起去见塞尔。“即使你不喜欢公司里的某个人,你最好还是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说,“每个人对这样的事情都会很敏感的”。“谁又找你诉苦了?”赛尔似乎有点儿不依不饶。“弗兰克·琼斯。”约翰尼说。“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这么说呢?我对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一直待人友善。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刻薄的话。当然,他绝对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混蛋。”对于塞尔的粗鲁,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扩大运营机构,调整机构运营模式,分散经营权,减少权力集中在个人的手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尼和我开始扩展我们的零售业务机构。在纽约,我们拥有的空间和后台能力已足以让现有销售机构扩大一倍。当时,我们唯一真正的分支型办公室位于芝加哥的拉塞尔大街,在几十年前,我们无意间收购了这家经纪公司,并对该公司的业务进行了清算,即:处理债权债务,结账清算,并把基金从买方转移给卖方。此后,芝加哥的这间办公室只从事机构销售,以及为我们在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所的交易员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我们开始为这个分支机构配备销售员和其他人员,在随后的10年里,我们又相继在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和亚特兰大开设了分支机构。对于每一家分支机构,我们都是先从小做起——开始时一般只有几名雇员,并从向机构销售权益性证券做起,然后,逐渐向零售业务拓展,销售对象也扩展到市政债券、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企业融资券。当然,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单纯地扩大规模,我们也没有想过做成像美林或美邦(Smith Barney)那样的大型零售型机构。我们的基本假设在于:继续保持原有的管理精髓;内部培养,内部选拔,以挖掘内部潜力为基础;任何现有雇员,只要认为自己符合条件,就可以毛遂自荐,不必担心上司对自己如何评价,以事实说话,以业绩为证。无论级别高低,鼓励所有人自觉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商机或是削减成本、改善效能的方法。尽管我是事实上的公司管理者,但不存在任何严格的自上而下式的命令链条。不管是谁,只要认为公司在经营、文化、思想或是其他方面存在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任何有能力对问题作出评估的上级进行汇报。只要能解决问题,任何人都责无旁贷地提供支持,当然也包括我在内。1970年夏天,市场形势发生突变,在很多更关注结果的人看来——按照我的想法,主要是指政府、纽约证交所、证券交易委员会、美联储、财政部和白宫的官员及管理者,市场的变化可能会危及整个证券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当时,很多经纪公司正在关门停业(长期的不当管理是个重要起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金融机构遭遇危机时为顾客提供保护的纽约特别信托基金(Special trust fund),也岌岌可危。这次危机的直接起因,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的海登·斯通证券公司(Hayden, Stone & Company)。对于这家拥有庞大零售网络和大量承销业务的老牌金融公司,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寻找收购方,这也是摆脱整体性危机的当务之急。所有投资者都在迫不及待地抽资退出,形势岌岌可危,慌忙之中,海登·斯通证券公司不得不找到几家俄克拉何马州的公司——为什么找俄克拉何马的公司,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些公司以超过1 700万美元的自有股票作为替代资本,为海登·斯通的债务提供担保。作为回报,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则向这些公司提供利息率为7%的票据。但是,不久之后,提供担保的一家俄克拉何马公司——美国四季护理中心(Four seasons nursing Centers of America)本身也面临破产之灾(根据联邦法院的检举,该公司涉嫌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证券欺诈犯罪,很可能就此被彻底清算——不过,这是另一个与贝尔斯登毫无关系的故事)。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可以接受的收购方CBWL 公司(Cogan, Berlind, Weill & Levitt),最后的障碍就是获得海登·斯通证券公司次级贷款人的认可,因为重组很可能会让他们损失大部分甚至是全部贷款。似乎唯一能让这些贷款人满意的就是一个荒诞的怪念头:如果他们拒绝合并,就有可能会让纽约信托基金彻底破产,让整个机构陷入严重的危机。不过,贷款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同意了合并,最后,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杰克·高尔森(Jack Golsen)坚持到底。他的LSB工业公司为海登·斯通证券公司提供了120万美元的贷款。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尔森勃然大怒,他当时说:“我更希望能看到公平的实现,我希望我们能创造这样一个先例。而实现公平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们清算破产,让交易所承受这2 500万美元的损失。我希望这样的罪行能引起公众的关注。”最后的截止日确定为1970年9月11日上午10点。就在前一天夜里的慈善晚宴上,我接到以前的导师也是老朋友——巴尼·拉斯科的电话,他告诉我,俄克拉何马城有一个叫杰克·高尔森的家伙,他已经成了全华尔街的敌人。我认识他吗?实际上,和他结婚的那个女孩和我住在一条街上。此时,巴尼已经是交易所理事会的会长,他想让我给杰克打个电话,看看我是否能说服他同意这次交易。看来,如果我不参与的话,巴尼或许会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找来。“我很理解你,知道你很难过,也知道原因是什么,”那天晚上,我对杰克说,“但我知道,假如你不能顺利签下这份合并协议,肯定会树敌。”于是,我开始绞尽脑汁地寻找能成全这件事的人,从巴尼到美国总统,只要觉得有希望,便抓起电话说:“巴尼·拉斯科是更诚实可信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他一下。”第二天,就在距离最后截止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杰克终于签署了并购协议,合并计划获得批准,创世纪的时刻终于到来。杰克在当天下午发给我的电报中说:亲爱的艾伦,你的电话最终促使我在今晨接受了巴尼·拉斯克提出的要求,对我们达成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你在这笔交易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因为现有方案也是每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我们不能再奢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你的朋友,杰克·高尔森巴尼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我是代表整个行业给你写这封信的。全世界的投资者和金融界都在此感谢你的无私和智慧,感谢你在CBWL与海登·斯通成功合并中给予的巨大帮助。作为最亲密的朋友,我衷心地感谢你,愿主保佑你。你的挚友,巴尼故事并未到此结束。既然全世界的金融界都有愧于我,那么,它难道就不能把这份愧疚化为对贝尔斯登的回报吗?当时已经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产权基金公司(Equity Fund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一家对外自称是专门提供基金项目的保险公司)正准备雄心勃勃地到纽约证交所上市。如果巴尼有意指定我们担任该股票在纽约证交所的财务顾问,我们当然不会拒绝。巴尼显然非常乐于成全这件事。后来的事实表明,产权基金的这笔交易非常成功,交投两旺,因而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巴尼把这份大餐送给我们,自然会让其他公司眼红发狂。但是到了1973年,整个事件发生突变,“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赤裸裸的欺诈丑闻被曝光,手段恶劣,无异于明目张胆的抢劫。于是,产权基金公司的股票在一夜之间便从30美元变成分文不值的废纸。我们当时还持有3万股,这就是说,我们损失了90万美元。按照1973年时的规定,在进行股票交易时,交易者必须在5天之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马上将此事通知所有向我们出售产权基金股票的卖家,并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付款,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把股票原件交付给我们。但纽约证交所断然拒绝,我们必须立即付款——此时,巴尼已经不再担任交易所的董事长,但假如我们申诉,或许可以推迟付款。我们的回复是:“听着,我们肯定会付款。我们只想确认这些股票证券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事实证明,我们同意买进的这些股票,几乎全部为经纪商代表内部人持有的股票,而这种股票在法律上是禁止转让的。最后,所有经纪商实际上都要求我们取消交易,我们全身而退。这件事让我学到了两个教训:第一,如果你帮助了别人,他或许会记得你的恩情,但也可能会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如果你给机构帮了一个忙,那么,你最好还是默默地记在心里,因为今天的掌门人明天或许就不知去向。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年里,我在贝尔斯登内部颁布了一项政策,要求所有合伙人至少把4%的总收入捐助给慈善事业,我们把这项制度称为“格林伯格荣誉体系”(Greenberg Honor System)。所有人均同意执行,我们相信每一个合伙人的承诺。后来,为了确认各位合伙人是否按规定捐助,我们对每个人的纳税申报单进行了核对。事实表明,这项政策带来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效地削减了成本,也加强了我们对累计资本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强化企业文化、提高凝聚力和荣誉感的作用。我们是在共同参与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它不仅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和统一,也有助于提高我们作为企业公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有理由为此而感到光荣。如果公司的业绩在随后的一年更上一层楼,我们的捐赠金额将进一步加大,我们也可以赢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其他几家华尔街的公司曾打来电话,咨询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却没有一家公司颁布类似的公益政策。我一直无法想出其中的原因,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良好的商业意识,它只会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父母不仅为我的成长创造了舒适、优越的条件,更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引导我拥有良知与善良。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这些言传身教,在刚进入贝尔斯登时,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接受贝尔斯登,那么快地融入贝尔斯登。塞尔一直用心地守护着4%的规则。1950年的塞尔和比尔·梅尔,更多的是无私的给予者,在第一次参加犹太人联合呼声(United Jewish Appeal,即:纽约犹太慈善团体联合会)组织的晚宴时,就是他们亲自陪我去的,我的第一笔慈善捐赠是100美元。尽管我参加过很多次纽约犹太慈善团体联合会组织的慈善捐赠晚宴——我的捐赠总额大约有几百万美元,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次却始终让我记忆犹新。除了他的慷慨和无私之外,塞尔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充沛精力和令人叹服的筹资能力。他后来成为纽约犹太慈善团体联合会的会长,并积极参加美国红十字会和城市联合体(Urban Coalition),组织创建了希伯来青年联合会(Young Men’s and Young Women’s Hebrew Associations)并担任会长。在他辞世前的10~15年里,尽管塞尔已经将贝尔斯登的指挥棒交给了我,但他依旧是华尔街的幕后操纵者。慈善事业和志愿活动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塞尔也没有闲下来,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提醒华尔街,他还没有彻底退出,他就会针对金融政策或是公共政策发表一点儿看法。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慈善事业,让塞尔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得到了喘息之机。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股票和债券交易中继续收取固定佣金的日子似乎已经屈指可数了。基于这样的变化,很多在收入上完全依赖经纪业务和销售研究的公司,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就此退出市场。在出现这种变化之前,纽约证交所的所有交易均收取较高的固定佣金,具体水平依股价而定。新的规定于1975年5月1日实施,一夜之间,平均佣金水平下降了75%(在那个时候,在线折扣经纪业务还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一笔5 000股IBM的股票交易,在35年前要收取1 500美元的佣金,但是在今天,只需要8.95美元就可以在线执行)。这种变化给贝尔斯登带来的影响是,我们的大宗交易和机构销售(这也是塞尔的专长,也是贝尔斯登在过去几十年中利润率最大的收入)遭遇不可逆转的大幅萎缩。但是,随着5月1日日渐逼近,尽管已经知道股票费率即将寿终正寝,但塞尔依旧坚持认为,由于我们为机构型客户和零售型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专业咨询、日常服务及市场研究)本来就只收取优惠费率,因此,这会让我们不必降低费率。高盛的格斯·利维也在幻想这样的特例情况。但市场规则永远不会对任何人开恩,在新政实施的第一天,我们也没有成为特例,和所有证券公司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削减收费标准75%。当然,高盛也没有成为例外。勒布罗兹公司(Loeb,Rhoades)在继续坚持了48个小时的幻想之后,也不得不顺应大势,因为在这48个小时里,他们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客户的交易电话。两年前,我们搬到了沃特大街55号的新办公楼,华尔街1号的办公室显然已经无力支撑我们的庞大业务规模。到1973年,我们仅在纽约就聘用了600名工作人员,各分支机构的雇员数量超过了100人。此时,20世纪60年代“高歌猛进”的市场已经让位于衰退和通货膨胀,道琼斯指数走进漫长的下行通道——仅在1973年便下跌45%,整个市场笼罩在灰暗和忧郁之中。不过,我们还是在当年实现了微利,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我们的风险套利,但主要功劳还是我们所属的“优惠产品”。按照我们提-爱华网-供的一种“优惠产品”,贝尔斯登以极低的折扣向投资者出售刚刚以更低的折扣买进的权益证券。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目标是本身价格较低且无人问津的股票。例如,当前市场交易价格为每股10美元,但如果继续以存货形式持有的话,其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跌。此时,我们可以按大宗交易的形式,按每股3美元的价格大批收购,然后,马上在道琼斯的报价系统中宣布,我们准备以每股3.25美元的价格转手交易。于是,经纪商会蜂拥而至——“不可思议的便宜货”,他们可能会告诉自己的零售客户:“就在两天之前,它的市场价还是10美元!”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赚到一大笔利润。正是凭借这种经营之道,我们在黑暗中走过了艰难的一年。|!---page split---|当然,搬到沃特大街55号的新办公楼也让贝尔斯登承受了大量的管理费用。我们本来可以做一笔赚钱的生意,但却一口气租下了12万平方英尺,这远远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空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小经纪公司(也就是我们的转租对象)却在关门停业。要充分利用这些闲置的空间,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办一个全新的业务:交易清算。我们可以帮其他公司去做他们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对交易进行账簿记录, 确认交易情况,代收股利,管理保证金账户、资金的拨付与回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每一笔交易收取极低的手续费(还可以无偿使用客户的隔夜在途资金)。开始的时候,为招揽客户,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免租金服务。泰德·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觉得这么做很愚蠢,他居然说,他不想让这种无聊、乏味的事情玷污贝尔斯登的名声。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用全部精力去争取杜邦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大企业(我告诉泰德,“他们已经是贝尔斯登的客户了”)。对我来说,清算业务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它可以让我们的客户摆脱很多日常性的繁杂工作,集中精力去做他们最擅长的工作——销售有价证券。尽管清算业务的启动和成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到1975年年初,它就已经走上正轨。尽管我们的经常性客户只有十几家,但不管怎么说,清算业务确实成为贝尔斯登最稳定的一头现金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两大主要竞争对手AG贝克公司(A.G.Becker)和勒布罗兹公司先后退出,他们的大部分客户投入我们的怀抱。到1988年,我们处理的清算业务已经占到纽约证交所全部业务的10%,我们的清算客户达到2 000家。就在这项新兴业务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我们却遗憾地错过了另一个利润更为丰厚的机会。在开始执行议价费率时,我就曾督促约翰尼·罗森瓦尔德把主要精力从机构销售向公司理财方面转移。这可以让他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更大的经济回报——因为打折后的机构客户佣金已经给公司的士气造成了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贝尔斯登必须充分发挥他在社会关系上的资源和才华,他似乎认识所有人,而且能和每一个人都成为朋友,这绝对是罗森瓦尔德的天赋。此时,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那就是创建一个公司理财部,去实现贝尔斯登从未真正兑现过的承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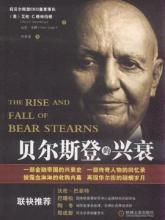
但是,这个新部门的两个主管西格·瓦尔萨格和杰瑞·科尔伯克却互不相容。西格是塞尔的心腹,他更注重于传统的投资银行方法:争取新股发行的承销业务,然后通过这些关系,争取利润率更为丰厚的并购业务。他非常聪明,也是一个精明、熟练的办公室老手。杰罗姆·科尔伯克早在aihuau.com1955年便进入贝尔斯登,那时的科尔伯克只有30岁,在研究部任职。1960年,科尔伯克被调进公司理财部,并在同年成为贝尔斯登的合伙人。他的资历毋庸置疑,同时他也有法律学和MBA学位,举止温文尔雅,但稍显清高和自负。尽管杰瑞的清高不是有意而为之,但很多人还是不接受他的这种自负。从根本上说,科尔伯克善于思考,勤于钻研,这一点显然和塞尔的秉性相去甚远。此外,他有一套自己的投资银行经营模式,而这样的方法显然是塞尔所无法理解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杰瑞和亨利·克拉维斯以及乔治·罗伯茨三个人开始推行他们所谓“布罗波投资”(bootstrap investment),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s)。按照这种方法,他们的投资目标主要是家族式实业公司:创始人已经准备退休,并愿意出售公司股份(只要购买方不是竞争对手)。这些收购均属于杠杆率极高的交易,需要以被收购公司的资产为收购贷款提高担保。尽管贝尔斯登也可以提高部分融资,但大部分资金还是要来自于私人投资者、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组建新的管理层,削减人员开支,提高经营效率,剥离与主营业务无关的独立部门,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或是罗伯茨)将在被收购公司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得贝尔斯登能对新公司施加很大的影响。在理想的情况下,贝尔斯登会选择合适的时机,以数倍于初始股权投资的价格,转让重组整合后的核心业务。尽管这种新型业务的回报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承销业务,但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前期整合。杰瑞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通过投资银行手段,提升并购企业的价值,为贝尔斯登创造更多的价值,但他也意识到,他和克拉维斯及罗伯茨正在逐渐脱离贝尔斯登的其他合伙人。因为他们需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被收购企业中,这就让他们很少有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因此,本来就脾气暴躁的塞尔必然少不了抱怨和挑剔:每次应该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们都会磨磨蹭蹭,看不到人(我不知道塞尔会不会想到,如果他们每天都坐在电话旁边,怎么能为公司赚那么多的利润呢)。最大的障碍或许在于,公司理财部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和西格一起工作。最终,杰瑞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离开,很自然,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也跟着科尔伯格离开了贝尔斯登。如果没有贝尔斯登的支持,不知道KKR集团(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还能不能延续后来的辉煌, KKR还能否书写华尔街最炫耀的篇章。坦率地讲,我不能肯定。尽管我个人对假设性的问题不感兴趣,但我认为,我和约翰尼没有尽最大努力留住杰瑞、亨利·克拉维斯以及乔治·罗伯茨这三个人,这绝对是错误的。约翰尼和我也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结论都是一致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我们的挽留也许没有作用,但我们至少应该尽自己的努力。虽然约翰尼和其他人最终还是设法填补了他们出走后留下的空缺,但是在努力和业绩上大不如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杰瑞辞职之前,也就是在1976年3月,塞尔在贝尔斯登的角色和形象开始大打折扣。在外形上,他的风范早已不再——体重超重,酗酒过度,他似乎还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过去。1978年,他正式宣布不再担任高级合伙人。每年四月,我们都在哈默尼俱乐部召开贝尔斯登公司的合伙人年会,于是,那一年的年会也就变成了欢送塞尔退休的仪式。塞尔原本还想继续以名誉董事长的名义到公司办公室上班。毫无声息地淡出人们的视线,显然不符合塞尔的个性,我们当然不会让他失望。在当天晚上的仪式上,塞尔得到了一个礼品包,里面包着一块高档手表。但塞尔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在他吃力地打开礼品包时,突然后仰倒在地上,严重中风击倒了塞尔。当救护车把塞尔拉走时,我对在场所有人说,塞尔肯定希望我们把这场年会继续下去,为他的健康举杯祝福,没有人会忘记他为贝尔斯登作出的贡献,没有人会忘记塞尔。不管怎么说,晚宴不能戛然而止,贝尔斯登还要继续,一切都要继续。但是,塞尔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两天之后,塞尔去世了。塞尔把贝尔斯登从一个靠佣金生存的小机构变成一个风险经营体。他依靠一己之力就做到了,他实现了前辈的梦想。因此,他理应得到全世界的尊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