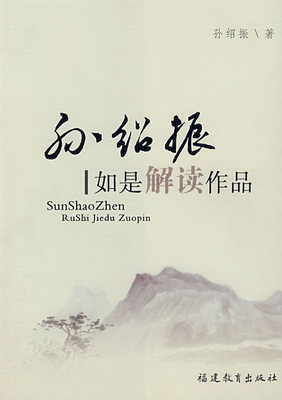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19:29:30分享人:可这一步的距离来源:互联网20
【西林按】这是孙绍振发表在《人民日报》1998-199年间的六篇散文。
撇远一句,这六篇散文在我QQ空间里转载时显示有敏感词语。真可恶!一边告诉你有敏感词语,不让你发表,却又不告诉你到底哪些词汇是其所谓敏感词汇,专制、无能、懒惰、愚蠢。
一 静静的金湖
孙绍振(1998.04.18)
地处闽西的泰宁太小,那里的金湖名气也不大,虽然随着人流,我
已到了泰宁,可对于金湖之美,却毫无思想准备。但一到了十里平湖之
上,望着那浩淼的碧波,城市里那种人与人互相距离太近,连在公共汽
车上、在人行道上都互相妨碍的感觉一下消失了。我被如此辽阔平静的
视野震惊了。首先感到舒畅的是我的眼睛。在城市里被所谓“水泥森林”
横加阻挡的目光,突然获得解放,那平时被高楼大厦分割得七零八碎的
天空,奇迹般地变得完整了。平日里它高高在上,总是令我不得不仰望,
今天它居然低垂下来,变得这么亲近。我再不用仰酸脖子去追寻一片小
小的云彩了,云彩们在这里不像在城市里那么高傲,它们随和得多了,
就在你眼前,你一下子就习惯了和它们对视、平视,甚至是俯视,我指
的是云彩在水中的影子。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上下云彩是对称的,把
天和地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欣欣然,我就站立在这和谐的画图中。
这里的水面与厦门、东山的海面不同。乘在东山的游艇上,在浪尖
波谷中起伏,好像骑在一匹劣马上,你体验到的是与大自然搏斗的惊心
动魄,你和海浪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和城市里的竞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这里的天地是
浑然一体的、和谐的,你一到这里马上就被恬静的水和天同化了。在这
伟大的宇宙之间,我变成了它的一个小小的质点,弄不清是变得伟大了
还是变得渺小了。这一切于我似乎都无所谓了,因为在这里,我不用和
人比什么。我只和大自然相对,伟大也好,渺小也好,都不是我的事。
因为这里不存在竞争,人与人的关系和城市里迥然不同。我可以感到自
己心胸在扩展,有了一种想夸张地吐一口气,想象着自己的心胸与天和
水同化的感觉。在这样清澈的、洁净的世界上,我难得享受到一种不属
于自己而属于大自然的幻觉。当我望着那湖面上形态各异、碧草丰茸的
小岛,双眼追逐着水中的一尾游鱼时,我弄不清是想象还是真实,只是
感到水鸟和游鱼都和天水一样透明。在这种童话似的境界中,我不由得
产生一种愿望:让我的心变得像这里的天和水一样安宁、自由、恬静吧。
人生能有几度体验到与大自然融洽无间、浑然一体的欢乐呢!
我们在金湖上享受着金湖别具灵韵的温厚的微风。经过一个个姿态、
风格各异的小岛,眼睛都看酸了,还舍不得离开那岛上带着原始野性的
树林。从旅游小册子上,我了解到,这里原是一片险峻的群山。水库的
建成,使得人迹不到的虚无飘缈的山顶,变成了近在眼前的小岛。岛上
充满蛮荒景象,一切都在无声地宣告,那里的树和草似乎还活在盘古开
天辟地的年代,除了飞鸟以外,人都不曾打搅过它们的静默。这里的静
谧是永恒的,人类花了好几千年破坏了世界的安宁,这里是唯一的例外,
它是上帝的浪子———那是人类所破坏不了的。
在这种时候,最大的享受就是沉默,一切的人声都将是亵渎。
自然,球形的、卧虎形的、伏狮形的、阡陌形的小岛上的静默,并
不是死寂,这是生命的安谧,仔细看那岛上的树丛,其实并不令我感到
有任何的自生自灭的禅意。相反,我看到了无声的竞争。那一丛丛树木,
明显是分成群落的。很少有单株独枝的大树,那枝叶特别茂盛的,结成
一个群落。那连片的树冠像超级大国似的豪华地展开,占据了更多的阳
光。而那资格老到可以当祖宗的羊齿类,却不得不屈辱地俯伏下来,占
领更多的土地。那中等层次的杂木则在竞争不到天空和土地以后降低了
树干,为利用更多的空气,在苦苦挣扎中不得不扭曲自己的躯体,不管
怎样,每一根虬枝总算找到了虽不算完全足够但也可以繁殖它们生命的
空隙。不同群落缄默地并存着,欣欣向荣,但这是多少世纪生死搏斗的
结果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胜利者,而那失败者是永远地消失了,
连让我想象一下它们濒临绝灭时的呻吟都不可能了。不用有多少生态学
的知识,就可以发现,在这么浩淼的湖面上,居然看不到几只水鸟,实
在是一件憾事。在美国的伊利湖、休伦湖上成群的水鸟甚至是不怕人的,
白水鸟停在超级市场的汽车顶上作绅士式的漫步是很平常的事。
我不知道别人热衷于旅游的目的,在我自己则是为了消除竞争的疲
劳。然而,就是在这童话境界的金湖之上,那残酷的竞争也只是暂时地
离开我,只有我完全不动脑筋的时候,才能享受与大自然融合、没有矛
盾、没有冲突的安宁与和谐。一旦我开始思考,我就看到了也许是更残
酷的竞争。那无端绝灭了的物种,不可能有任何法庭、也没有律师为它
们主持公道,在那里,早有达尔文指出了弱肉强食是唯一的法律。这绝
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仍然在我所欣赏的美丽的小岛上静悄悄中实行。
不论是什么样的美都不可能是没有遗憾的,金湖之美,也不可能例
外。
一个成熟的人,不应该向世界要求纯粹的真善美。
但是,应该珍惜那虽然有残缺却依然动人的美。
因而,回到城市以后,我仍然十分热烈地向我的朋友赞赏金湖之美。
我的朋友在金湖待过一年,他对我的激动嗤之以鼻。他说他当时去“玩
金湖”,绝不像我们这样“土”,他们是带着猎枪和帐篷到岛上去“尽
情浪游”,在枪声豪迈地四处响起以后,把带血的水鸟野物串在枪尖上,
满载而归。
说罢他嘿嘿而笑,笑得很甜蜜,很善良,很温柔,很真实。
我仔细地研究着他的笑容,他真的笑得一点不残酷。
嘿嘿嘿……他还在笑。
而我的心却在颤栗……
|
二九十九分的苦恼
孙绍振(1998.05.15)
我历尽坎坷,中年才得一女。体验到亲子之爱那份无言美妙之后,
才觉得自己心灵中那一块一直未曾发现的感情的空白、蛮荒之地,早已
成为水草丰美的绿洲,那份欢欣恰如刚刚即位的天子,发现自己童年时
曾经流落民间,一无所有。
这爱在开初是一种心灵的欢畅,望着她那越来越像我的小尖鼻子,
比我还玲珑的小嘴,心头洋溢着得意和开怀。我的太太自然也是我忠实
的同盟者,她认为孩子比我长得漂亮,比我聪明,比我有更好的气质,
将来比我更有出息,至于和院子里那些同龄孩子相比,我太太更是自豪,
没有一个能和她并驾齐驱。
在这种情感气候之中,主观地希望花越开越艳丽,这种希望变成了
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等女儿入小学,一年年往上升,这种顽强的宗教信仰却一次又一次
地遭到打击。最关键的是考试成绩,虽然都在九十分以上,但总不能使
她的妈妈满意。在她看来我们的孩子应该门门都一百分才顺理成章,人
家的孩子都能考到九十六、九十七分,她感到不可理解。孩子每次拿了
九十四、九十五分回来,她脸上都没有笑容。有时孩子失误,只拿到八
十几分,于是就有引发暴风骤雨的可能。孩子的每一次失误都是对我们
希望之花信仰之花的摧折。只是我和太太不同,我默默忍受这种摧折,
而我太太却要把这种摧折之痛发泄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孩子,平时各式各样的小毛小病,甚至于非毛非病都
被拿出来数落一顿,论据软弱,而论断却是夸张的。这时孩子默默垂泪,
一副可怜相。那眼神显然是希望我马上相救。可是我太太也在看我,那
眼神显然也是希望我为她找出更为雄辩的论据。
夹在两种目光中的我只好装傻。
孩子自然拿我没办法,但太太对孩子的数落却有了发展。原来用的
是第二人称单数,“你总是”如何如何不听话,不久就变成“你们总是”
如何如何,最后干脆成了“你们两个人”如何如何。这时,我如果和她
在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上进行逻辑的、语法的分辩,其结果“你们”立即
变成了“你”,孩子解放了,批判的矛头立即转移到我头上。平时我的
懒散、不爱整洁,待人大大咧咧,买东西又贵又次,多年前的学生来访
叫错人家名字,来香港二十年还听不懂广州话,等等。我想,好男不跟
女斗,尤其是斗嘴,就是斗赢了又有什么光荣!不如遵循沉默是金的格
言,“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乃我家乡人传统智慧的结晶。
我逐渐感到,随着孩子功课难度的上升,对孩子的爱,不再单纯是
种甜蜜的温馨,其中也掺杂着忧虑和委屈。大凡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复合
的,光是白糖,甜得也叫人发腻,加上点酸的、辣的,甚至是苦的(如
咖啡),就美妙了。对孩子的爱也一样,如果没有那些苛求、专制,对
孩子的成绩下降不痛苦、不忧虑也就说明对孩子的爱不强烈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减少一点甜蜜中的苦味。最关键的是切实有效地
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放下教授的架子,亲自辅导孩子做作业。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孩子放学回家老远就喊着冲进门来了:“
爸——爸!”知道这肯定是好消息了。
果然带回来一个九十九分。
我大喜,待她妈妈下班归来,我努努嘴暗示孩子把考卷奉上。
我看到太太脸上一丝微笑还没有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
她往椅子上一瘫:“我就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
分!”
我大为震惊,本想顶回去:“你上小学考过几个一百分?我看连九
十分都难得。”但是我知道,这样意气用事的话是绝对愚蠢的,只能破
坏孩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所带来的良好气氛。美国人的幽默理论说,幽
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把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甚至享受。
我灵机一动,叹了一口气说:“都是我不好。”
太太奇怪了:“平时都是骄傲自满得不得了,这回怎么谦虚起来了?”

我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老师没
有教好。但是这种可能不大,因为人家的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并没有
听说成绩不理想的呀。这就有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她的头脑不好,天
生的笨。”
太太有点不同意的神色,我按住她的肩膀,请她让我说完。
“天生的笨,是遗传的原因。这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你
笨。”
“这不可能。”
“我同意。那就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我笨。”
“我看这样说,还比较恰当。”
“但是,这也并不能怪我,更不能怪她呀。想当年,你找对象:背
后跟着一个连队,你满园里拣瓜,拣得眼花;拣了半天,拣了个傻瓜。
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
女儿捂着嘴巴笑。
太太也忍不住笑了。
|
三燕园历史感
孙绍振(1998.11.05)
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北大校园山石园林仅仅当作风景来欣赏,从来
没想到几乎每一个景观都隐藏着我们民族悲怆的故事。1955年8月,一
进校门就看到办公楼前的一对华表,第一印象是:和天安门前的一样庄
严。从那以后,我的感觉和思绪就瘫痪了,在三十八年以后,读了一本
关于北大校园的书,感觉神经元突然复活起来,一百多年以前圆明园安
佑宫前吹过华表的烽烟才扑上我的面颊。走近办公楼,那带着皇家气派
的丹墀、麒麟,是目睹过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浩劫的。海盗的喧嚣,
也许曾经使麒麟那石头的心震裂;那冲天而起的火光,一定曾经把它的
身躯烤得发烫。如今,石头当然不再烫手,可是也没有完全冷却。经过
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风雨,周围的一切差不多全都变幻了,唯一没有改变
的就是它的庄重和沉稳。未名湖中那总是露出头和尾巴的石鱼,曾经吸
引年轻的我,让我联想起许多浪漫的神话式的爱情,如今才得知,它来
自圆明园的喷水池,西洋雕刻的写实风格和燕南园里传统风格的花神庙
碑,有同样的历史沉重感。
多少次走过燕园,只有今天才有走过时间隧道的感觉,从风光鲜丽
的校园可以透视到历史的长廊最黑暗、最屈辱的尽头。
再没有比未名湖上那石舫更有象征意义的了。当中国的江河上千帆
竞发,帆篷上涨满时代的风的时候,这石头的船却和它所模仿的颐和园
中的石舫一样连一寸也没有移动过。这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军机大臣和
珅穷极奢侈的铁证。石舫僵在那里仍然有它的价值,至少给中国的当代
人和后代人一个警惕的信号。
越是黑暗,追求光明的眼睛越是明亮。在庄严肃穆的校史馆里,我
看到了严复的相片,当年时髦的八字胡子虽然给人一种古老、甚至陈旧
之感,但是,那微厚的下唇,极富福州人纯朴忠厚的乡土特色,而那锐
利的目光,透出那习惯于面向海洋的敏捷。从五四时期一代英豪那多少
有点模糊的照片上,发出了不仅是北大,而且是整个中国最灿烂的启蒙
的思想光华。从这里出发,再去看看校园内李大钊、蔡元培的胸像,纤
秀的纪念三一八烈士的方尖碑、块状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每一
个献身者的名字都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你不用去触摸,也可以感到英
灵们当年最后的目光是凝聚在未名湖水塔尖顶之上的。
作为北大校园景观的焦点,长期以来我不知道这个塔为什么没有名
字。原来捐资修建这座水塔的是一个美国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博晨光。
如今这座为燕园生色的水塔,终于把博先生的名字带了上去,称之为“
博雅塔”了。
这样的尴尬不但有北大校园的历史,而且也带着中国历史的特点。
想想罢,燕园本身,就是美国人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所修建的。而这
个校园既有中国南方园林湖光山色,又有现代西方建筑技术特点,中西
建筑文化是在这里和谐地交融着还是无声地争辩着?
走出燕园,不带着历史感是不可能的,但是光有沧桑感是不够的。
站在西校门口,我感到的是第二个一百年的挑战的压力比第一个一百年
的凶险更为强烈。 四 小城童话 孙绍振(1999.02.06) “文化大革命”浩劫时期,华侨大学解散了,像我这样的准右派,
只能到德化跟“穷山恶水”亲近。幸而还可以拿工资,当然,尾巴是要
夹起来的。当时的权势人物有点官僚主义,没有权势的我们,也有一点
兵僚主义,都把德化看成了《水浒》里只配脸上刺上字的犯人安身的“
远恶军州”。但是这几年,对德化的记忆,随着德化发现了金矿,提高
了含金量。
快到德化的时候,我不禁激动起来,当年寒伧的城关历历如在目前。
把唯一的一条街叫做“三角街”,表现了德化人的数学天才,不超
过五十公尺,称之为三角街,居然在十多万父老乡亲中没有任何争议。
最大的百货商店不过两层的土木建筑,在德化人心目中,尤其是那些远
在山沟里,几年才进一回城的,为了几尺红布而伤透脑筋的少女,绝对
不亚于梦中的南京路。一家饮食店是最阔绰的农民才敢进去的地方。古
老的干打垒的土墙和德化人一样留恋故土,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
肯从德化城市的历史上撤退。在大街上、在县政府,在德化政治、商业
中心,干打垒的泥墙和青砖墙与其说是互相亲热地紧挨着,不如说是互
相警惕地僵持着。在那靠比赛伟大口号为生的年代,德化人最大的苦恼
就是许多伟大的标语没有与之相称的砖墙。
惊人的奇观还要数微型的农具店,完全是手工制品:簸箕、牛绳、
锄头、扁担、斗笠,和童话中玩具商店的规模差不多,但是残破得妨碍
着童话的感觉。牛和猪没有童话里那么聪明,也没有童话里那么纯洁,
它们在街上自由地漫步的时候,没有仙女陪伴着,但是,却有一种不可
侵犯的庄严,就是汽车喇叭在后面使劲鸣响,它们也不改团级干部的从
容,说不定还留下一堆冒着热气的纪念品。德化人见怪不怪,悠哉游哉,
脚底像长着眼睛似的,看也不看,就惊险地从上面掠了过去。德化人大
山一样沉稳风度,守着古老的安贫乐道的传统的小日子。他们不欣赏三
明人刻薄地调侃自己的小城的民谣:“小小三元县,只有三家豆腐店,
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德化城关人的生活节奏和他们四周相依为
命的山一样:把平静和谐融化在街上行人自得其乐的步伐中,一点也不
为生活在这个闽南最微型的小城而感到委屈;就是比城关小得多的,连
一条街道都不具备的上涌小村,也被称之为“小上海”……
接近城关的时候,公路正好在山坡上,司机特地提醒我们从远处眺
望新德化的全景。
这个小伙子有着德化传统的美好的自豪感。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
全球之时,德化却岿然不动。正值傍晚,辉煌的落日的余辉照在高低错
落的玻璃钢筋大厦的立面上,傲然显示一种大城市的繁华。高层楼群的
窗户上铝合金的窗框,蓝色的玻璃,坦诚地表现着德化人和大城市一比
高低的决心。当年街道上的主角———牛和猪当然是消失了。随之远逝
的,还有那种古老的节奏。想凭吊一下当年的最高的二层建筑———百
货商店,可是却被野心勃勃争夺高空的楼群淹没了。车流如潮,胁迫着
我们的耳朵和眼光,摩托车像小蝌蚪一样,风风火火地在人缝中乱钻,
街上的行人,也和摩托车一样,失去了世代祖居的老黄牛那样的从容。
喇叭声急,车轮声更急,德化的节奏变得紧张了。
到处都有一点乱得美好的感觉。银行、保险公司、外贸公司、酒楼、
歌舞厅,好像在争夺陌生客人的目光和惊叹。吃过饭,天色已经黑了,
星空亲切地低垂下来,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闪烁着,好像在和夜总会
的卡拉OK一比高低。可以感叹一番的事情太多。无意间发现河对面,当
年最为“豪华”的电影院,在许多大楼的挤迫下,就是门前的广场都显
得十分寒伧了。每一座新楼,每一扇落地窗户上即使没有任何广告,也
都写着两个字:炫耀。但是这并不俗气,我在窗户背后看到了驱赶贫困
的自豪和自信。
晚上,和县长谈话:举座皆欢。他告诉我们,德化去年经济不但没
有萎缩,而且大有增长;原因是打开了西欧市场。县长的口气略带“地
瓜腔”,自豪、自信、自尊,带着山里杂木、青草气息的纯朴和石头的
坚定,一点没有沿海城市领导常有的那种斯文。但是,要说他们土气就
错了。后来,我在德化瓷器博物馆里看到一系列的出口欧洲圣诞瓷器:
花篮、储蓄罐、西洋娃娃、圣诞老人,把我的想象带到西欧圣诞节的欢
乐市场中去。参观了几个民间瓷雕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那陈桂玉女士
的玉兰座中一个少女。上海人选择了玉兰为市花,这个在德化并不算很
出色的艺术瓷雕竟意外地征服了上海人。
我从这里找到了当年童话的色调。不过已经不是老黄牛为主角的那
种古老色调的,而是充满了大山外面、大洋彼岸那种现代化的明快,从
陈桂玉一系列瓷雕上,从那流畅的线条上,我感到了比之童话更为神奇
的音乐:那飞流直泻的弧线,令我想起了京戏中急急风的节拍。童话式
的微型小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童话世界,却再也容
纳不下他们的雄心了,他们的眼光已经越过山山水水,用景德镇所缺乏
的艺术家的雕刀,挑起了上海市场,甚至欧洲市场低垂的红色丝绒帷幕。
|
五泉州状元街上的风 孙绍振(1999.07.30) 两年前,我在福州环境艺术学会的年会上说过:城市建设发展得如
此之快,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看惯了玻璃立面上的天光云影,以至于,
一到台北,居然有一种很旧的感觉。这自然很令人兴奋、鼓舞。但是,
细思一番,也不免有所忧虑。许多城市的大楼的风格,趋近于雷同,从
深圳到上海从福州到广州,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好像同样一张图纸从深
圳一直照抄到哈尔滨。不要说与欧洲各城的建筑相比,就是和美国那些
假古董建筑相比,也显得缺乏民族和地方风格。我还说过,德国的民居
是花园文化,美国的民居是草坪文化,香港的建筑是海洋文化,我们福
州的建筑的性格是什么呢?至今仍然处在自发幼稚的模仿阶段,福建建
筑学界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两年以后,我到泉州,两次造访泉州的东街、尤其是状元街,我看
到了闽南建筑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感到真正的鼓舞。这才是福
建建筑学界的光荣。
难怪街上立着一块“八闽第一街”的石碑。
泉州自然也有福州、厦门一样的玻璃立面的钢筋大厦,但是泉州人
不满足于与其他城市雷同的东西,他们像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一样,
发挥了红砖文化的优长。但是,又在闽南民居的红砖的基础上,把花岗
岩作为边缘的装饰:显示了闽南红砖文化的神采。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车子开进泉州东街的时候,我并没有思想准
备。突然那扑面排闼而来的闽南传统民居和现代科技水乳交融的神采,
好像一阵精神的巨风给我的视觉以冲击。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乡人,
突然涌起了在闽南度过十多年生涯,熟悉闽南民居、民俗的自豪。
泉州人真是好样的。好就好在在全国的建筑都陷于模仿,失去了建
筑话语的自由的时候,泉州人创造了奇迹,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充满了
传统自豪感的建筑语言。光用乡土的自信和自豪感来解释是不够的。厦
门人的乡土自豪和自信并不亚于泉州人,但是他们的高楼大厦似乎并没
有从强势的西方建筑权力话语中解放出来。在建筑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
勇气方面,他们似乎应该向泉州人学习。光看东街,我还有些的担心,
也许趣味更高雅的人士可能有时代色彩不足之感。一到状元街,这样担
心就一扫而空了。到了这里,不但传统的感觉更加深厚了,而且现代精
神更为强烈了。
每一家,与其说是商店,倒不如说是一座文化浮雕,那参差的飞檐,
每一家都不甘愿有所雷同,那红色的廊柱,那古色古香的窗饰,好像把
泉州往昔的繁荣浓缩在你面前。虽然商业性那么强烈,但是,陈列书画、
瓷器莫不古色古香,充满了文化气息。尤其是那把整个街道划分为三个
段落的牌坊:那牌坊上的风化了圣旨的匾额,真切地显示出岁月的沧桑。
而那粗拙的石檐,繁复的间架结构,不啻高耸的立面,令人回忆起那东
岳山下几十座永远消失了的牌坊:旌表状元及第的,颂扬贞节烈女的,
每一座牌坊都是泉州的精神化石,睿智和保守在那文雅的对联上交织着,
悲剧和喜剧在匾额上交响着,成为今天泉州乡土文化的不朽的注解。只
有能听懂这无声的交响的人,才能理解现代泉州人的性格,才能感到在
碑坊上面看到自然沧桑感和文化沧桑感的交织,看到现代文明先锋和历
史传统的对比,而且在那中段露天的广场的茶座上,感到现代人所特有
的对于室外无方向的、自由的、即兴的风的偏爱。
当我在那榕树下露天的白色圈椅上坐下的时候,扑上我面颊的风,
也许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也许来自布满鲜花的巴黎,或者来自到处是露
天咖啡座的汉堡。
除了默默聆听这无声的音乐之外,我无心做任何别的事情。 |
六精致的澳门风格 孙绍振(1999.12.18) 好像是亚里斯多德说过,人的手长在躯体上的时候,功能是很伟大
的,但是一旦它脱离了人的躯体,手的功能就不但不复存在,而且变得
很可怜了。大师的铭言,包含着母体与肢体的辩证关系的哲理,很使我
震惊。可是,更使我震惊的是一个当医生的朋友的话,她有一个奇怪的
发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当它从属于人体的时候,是可爱的、美丽
的;但是一旦从人体上割离出去,就不但失去了它原本的美妙,而且会
变得相当可怕。我想到了:手臂、舌头、眼睛、乳房等等;可是我不敢
想象头颅。朋友的说法似乎比之亚里斯多德更为令人惊心动魄。这显然
是一种哲理,它帮助我们理解了许多现象;对于我们这个在近百年来饱
受分裂之苦的民族来说,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痛苦都可以从中得到阐释。
在台湾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时常感到过量的客气,还有本来可以省
略的礼貌。这固然表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传统源远流长,可是,在自
家人面前如此彬彬有礼却掩饰不了疏远和挥之不去的隔膜,何况,还有
不时提醒自己的语言上分寸的斟酌,某些敏感话语的回避,即使在热闹
的开心的祝酒中,也无法驱逐潜在的惆怅。空间阻隔和时间的断裂,民
族躯体的惨痛不在有声的语言中,却在突然无法找到共同语言的沉默中。
这也许并不值得过分担忧,久别的亲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心理的
距离的。也许这就是规律。但是我到达澳门的时候,对这种规律的普遍
性却产生了怀疑。接待我们的朋友虽然素昧平生,却没有生疏之感。不
论是在福建同乡会的联欢会上,还是在签订望厦条约的石桌前小坐片刻,
常常有一只手很自然地扶着我的肩膀,常常有眼光心领神会的交流,情
感在无声之中积累,心理距离在默契中缩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
种不过分讲究客套,说话没有忌讳的氛围就形成了。澳门人说普通话说
得诘屈聱牙,和香港人一样;听的人却能以同情的微笑来暗示鼓励,敢
于提示、纠正那刁难舌面和上颚的音节。甚至还调侃起澳门人的广东官
话来了。明明是在做客,却没有多少心理的陌生。最难忘的不是宴会上
的珍肴美味,而是在陌生人中间不拘形迹。还居然谈起政治;而且,心
灵音响发出了和谐的共振。不论是在黄昏携手游览市容,还是清晨独自
散步,每一步都有和谐的节奏,每一步,都成了回忆的乐谱上的音符。
当然,也有我们陌生的东西:
在葡京大酒店,有疯狂艳舞。虽然节目、演员和巴黎红磨坊相同,
但是在巴黎,光怪陆离的灯光使我心烦意乱,而在这里,我欣赏着从舞
场出来的人,他们的脸上有的是安详,没有任何神经不正常的痕迹。
当然,赌场里冒险主义和偶然性的搏击,在香港都是禁止的。但是,
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的感觉同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老虎机面
前的感觉完全不同。在那里我是在猎奇,在看美国人的疯狂,而在这里,
却是感受着热闹。计算着从这里获得的税收,使我感到欣慰。
从离岛酒店看联结三岛的大桥上华灯初上,当然是一种视觉的宴飨。
蓝色的海面逐渐变暗;暮霭亲切地挨近,星空温柔地低垂,海啊,大楼
啊,和初见朋友的情感一样,距离在次第消失。不用登高,不用披风当
襟,从酒店的落地玻璃窗看过去,就是完全平视也能望到那桥上灯火,
弧形的双曲金线粲然飞跃而来。此时不知是身在澳门,还是在海市蜃楼。
多少美好的诗句也显得平淡了。
在祖国大陆,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海,这样的山;拱形大桥上的灿若
星汉的灯火,在黄浦江、珠江乃至闽江上也都是常见的景观了。但是澳
门仍然精彩。它是精致的,连山也小巧,海也玲珑,而大桥却在对比之
下,有一种逼人的宏大的气魄,显得特别辉煌。小巧的山和玲珑的海把
气质赋予了澳门人;而大桥却展示了澳门人心灵的壮观。
也许,只有澳门人的精致和玲珑,才能在回归航道上,显示出如此
的坚定、宏大的气魄。
|
|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1/65104.html
更多阅读

在张晓风为席慕容的诗集《七里香》写的序中,我们可以稍微畅想一下席慕容那身处养着羊齿植物和荷花的画室中诗情画意的创作生活。《七里香》的序里讲到:席慕容小的时候曾迷恋一种蓝色的鸢尾花;初到台湾,会对有着玫瑰图案花边的窗帘痴迷;即

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

席慕容 著名诗人、画家。现著有《七里香》、《时光九篇》、《以诗之名》等七部诗集。诗歌风格兼有南国的细腻和草原的辽阔悠长。 一生,或许只是几页,不断在修改与誉抄着的诗稿,从青丝改到白发,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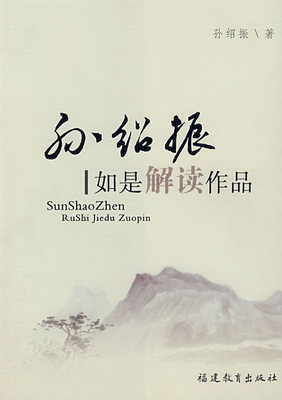
原文地址:孙绍振在厦开讲作文作者:polarstar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学系任教,1973年奉调至福建师范大学。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

席慕容的诗(选摘)一代的心事卷一 请柬请柬 ——给读诗的人 我们去看烟火好吗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梦境之上如何再现梦境 让我们并肩走过荒凉的河岸仰望夜空 生命的狂喜与刺痛 都在这顷刻 宛如烟火 一九八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