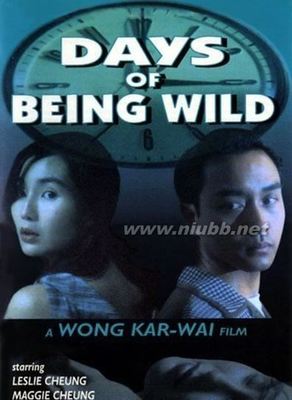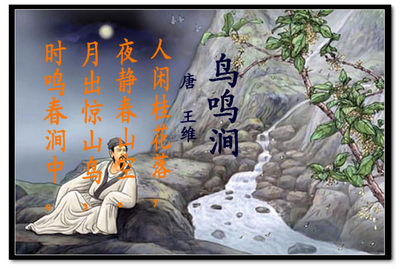一、绪论:电影与其自身独立性
一部电影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电影导演的“消失”。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自身的独立性。电影早在半个世纪前的西方已成为独立评论的对象,也即再创作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电影发行后多半与导演无多大关系。我们可以把诠释这个词等同于评论。
电影讲述了什么,多半是所有观者关注的主题。当然任何电影,除开那些狗血的不值一提的烂电影,都可以问出这个问题:电影在表达什么?这种观察的角度是近几十年,特别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切入口。它的内在依据是把电影当作一个多维视角的“文本”,一个可解读的映像、声音、文字载体。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兴许没有错,但它并不触及电影的“源初”,即作为纪录形式的映像。电影原来是“无作者的”,它仅仅是让映像自己说话,让现实呈现在胶片里。如果说作者真的有所表达,那也仅限于选材、定场景、调明暗、接胶片,然而这只不过是最初不得不履行的技术活。由纪录片的原始形式发展到独立电影的创作形式,当然意味着电影行业的发展。但是电影自述的形式永远没有在“创作”中消失,如果消失了,便不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只是变成毫无意义的伦理说教、意识形态反抗、矫情的抱怨。也就是说,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电影自说自话的,它看不到,至少不是很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它成为了普遍的东西。这个普遍者成了所有观众的心声,好似“我”也是如此过活的。这种状态称之为:同感,饱有你当下独立性的共通感受。一言以蔽之,电影的目标在于消融创作主体,让电影自己呈现自己。鉴于对电影这样的前见,我对《阿飞正传》作如下的评论。
二、主题摘要:“看见”死亡?
《阿飞正传》讲述了以旭仔(张国荣饰)为核心的四位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这种纠葛伴随着年轻的心对生命原始的理解、叛逆、追寻。这部电影的主题看似是爱情,其实是关于生死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尽管王家卫的初衷并不是如此。电影自1990年发行后,它一直在自我生长。时光网这样介绍此部影片:
电影以1960年代初期为背景,英俊不凡的旭仔(阿飞)(张国荣饰)是上海移民,他从未见过生母,自小由养母(潘迪华饰)养大,因此长大后他对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他先后与南华体育会售票员苏丽珍(张曼玉饰)和舞女咪咪(刘嘉玲饰)同居,但后来又相继抛弃了她们。旭仔从养母处得知,自己原是混着西班牙和菲律宾贵族血统的私生子旭仔决要找到生母,为此他只身前往菲律宾,可是生母拒见,带着怨恨离开。旭仔在离开香港前,将车子给予歪仔(张学友饰)。咪咪发现旭仔走了,问歪仔知不知道他在那里,歪仔告诉她旭仔去了菲律宾,并将旭仔的车子卖掉,将钱给她去菲律宾找旭仔。
一直暗恋苏丽珍的警察超仔(刘德华饰)目睹了苏丽珍与旭仔的决裂,并在母亲死后,决定改行去跑船。超仔在菲律宾唐人街又遇上了旭仔,不过他假装自己不认识他。不久,旭仔因为买卖假护照而在一场殴斗中身负重伤,超仔问他记不记得某年4月16日下午3时他在做什么,旭仔说要记得的他永远记得,但是他叫超仔告诉苏丽珍他已经不记得了。最后他守着死在一列异国火车上的旭仔。(时光网:http://movie.mtime.com)
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在阿飞临死之际的话语表现出来:
我最想知道的是我这一生,人最后一刻会看见什么。所以我死的时候,一定不会阖上眼睛。
而相反有另外一种声音:
一辈子那么长,好多东西我也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最想看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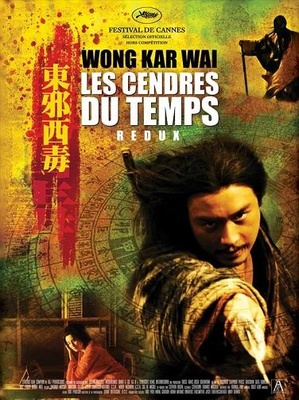
阿飞正经验着死亡,并在“领会”里期待:
想想吧!反正你跑船那么闷。一辈子不会太长的,想得来也该是时候了。以前,以为有一种雀鸟,一开始飞便会飞到死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那只雀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我曾经说过,未到最后也不知道我最喜欢的女人是谁。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死亡之际,留念着视线里的“物”:
啊……天开始亮了,今天的天气看来很好。不知今天的日落会是怎样的?
《阿飞正传》的精华尽在这最后两人的对话里。火车不停息地穿行在菲律宾的蕉叶丛林,所有的植被泛着绿光,湿漉漉的,看似生命的颜色,却在流动的镜头里显得有些颓败。至少窗外的生命已不再与“我”相干。暗黑的火车厢,一个将死的男人与另一男人在有气无力的对话。他们看似构成对话与交流,实则都是每一个人都在自说自话,在独白。镜头很少把两个人同时纳入,听见有人在问,却看不到他的脸庞。多么孤独的个体!“他们”在死的时候,孤独还伴随着,还在与孤独为友,还在与此挣扎。阿飞最后死去了,死在了行进的路上。这条路是一条渴望去“看见”生命的“最终”的路。而看见“最终”意味着不可再见。“最终”被看见,也就意味着“最终”的消亡,自我的消亡。
三、理论:死亡为生命的显现方式
整部《阿飞正传》的内容全包含在它的英文译名Days of Being Wild里了,即:成为蛮荒的时日。Wild既是开拓的对象,也是死亡之墓地的最后形态。它杂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罕至,却又诱惑满溢、放荡不羁、没有规制的自由自在。它是生的希冀,也是死的归宿。快乐与痛苦在这里,生与死也一并在这里。正如旭仔在那辆火车——行进在雨林中,所说“以前,以为有一种雀鸟,一开始飞便会飞到死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那只雀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一开始便已经死”意味着什么?它与“成为蛮荒”、“(废尽)时日”有何关联呢?成为蛮荒是因为不加照料之故,还是自我放逐之故?也就是说,成为蛮荒到底是有意为之,即把原始的野蛮自在当作追求目标;还是不得已而使有秩序化的心灵成了荒芜,即不再有能力经营自己这块精神田地而造成荒废。
在自我的蛮荒里追逐,实则是放逐。“追”和“放”的本质并不在于是“我”的主动与被动,一旦“追逐”、“放逐”与蛮荒系在一起,它本质上就成了荒蛮原野中的一部分。“我”必然消融在这种无垠的原始性之中,这种消融在视觉意义上的体现,即沉沦于时间(沉沦于无目的性、无秩序性的自我,自我=空洞的时间=虚无);在人自身价值上的显现,即在生命里死去。原则上或者实际中,任何人的死都是在生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的。也即我们都是在生的时候,去死的。也就是说,“生”是“行…死”的必要前提。然而“在生命里死去”却并不表达一种时间流的观念,也不表达“生”是“死”的前提性。它仅仅表达一种原始的同一性,毋宁更深层次地讲来:它体证的可能以及表达的可能才使得它的实践成为可能,反之亦然。旭仔最后的“遗言”(如果遗言被理解成:一个即将死去之人最后的话语)似乎表征了他在生命最终时刻的体味,但是这种体味恰恰是建立在“在生命里死去”这种表达的可行性上的。这种表达的可行性,不仅体现在这一单一的语词结构里,而且更显现在主人公所有的“成为蛮荒的时日”里。他时刻领会着这种生死交贯,蛮荒与秩序的冲突,也就时刻领会着“在生命里死去”的煎熬。领会和表达互证着彼此。它们得以成立,是因为它们得以嵌套。它们得以嵌套,却成了“我”得以理解的理由,而非相反,嵌套之下还有一个必须给出的最终原因。嵌套如果说得上是一种原因的话,那它仅仅出于自身是一种存在的结构和方式。方式并不因出自或不出自而瓦解,它仅仅因显和隐、明和晦而被触及、观察、操作。一种“方式”是不能像纸币那样从口袋里拿出来,而只能以事物特有的形式显现给你。正如“方式”从口袋里拿不出来,但无论你如何拿,总显现出一种拿的方式。死亡也是这样?
死亡这个词有其对象吗?死亡仅仅是生命的边界吗?死并不指示一种具体的对象,像普通意义上意谓的“生命的消失”,即死是对生命的否定。诚然这种理解会被广泛的日常经验所验证,但它却意味着一种空洞、抽象的常识。这种理解除了带来恐惧情绪以外,并不能增加任何对生命有所裨益的东西。死毋宁且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展现方式,即显现生命真谛的方式,它才取得了它应有的崇高和神圣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死才不是什么秘密,而只是人人都会经历的经验,不是听从于别人的经验,而是可成为自我经验的东西。这里的“经验”,不是“经过验证”,而是历经体验,并且是历经生命煎熬的考验。死是不需要经验的,它是经验的边界。“在生命里死去”向我们讲述的就是生命自身煎熬的过程。死亡不是对象化的活动,它是一种生命的自我展现方式。旭仔他采取了满足肉体欲望的形式(与两个女人同居做爱,最终“抛弃”她们)来破除这种煎熬或准确地说是实现这种煎熬(尽管并不出于他的初衷,从生命自身的形式立场上看是“实现”的)。当然阿飞到底是不是在满足自我的欲望,这一点很难说,也许他只是想找些事来做,好不让自己显得无聊、空乏。做爱仅仅是他要做的事而已,无事做便生空寂。在这种意义上放逐自我,与性爱、欲望无关,它仅仅关乎自我沉沦于时间之流。也就是说,它跟一个女人,两个女人,三个女人,甚至女人都无多大关联。在女人那里产生不了拯救,那里只有创生。旭仔所要试图指示自己的是:源出与最终。他努力探寻自己的生生母亲和想要知道自己最后一刻“看见什么”证明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的关键词有五个:时间、自我、欲望、爱情、死亡。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我如何消沉,并走向它的终点,即死亡。自我的消沉和解脱往往系在一起,同属于同一颗煎熬着的心灵。电影的胶片放映长度不过94min,故事时间跨度不到1年(1960年4月16日-1961年4月12日)。然而经历的时间似乎是整整一生。时间不存在于胶片的长度里,也不存在于墙上所挂的闹钟里,它仅仅存在于自我的挣扎中,存在于死亡的领会中。我们只要稍微用点神,就能注意到王家卫的众多电影都在讲述一个主题:什么是时间?如《东邪西毒》(英文译名:时间的灰烬∕AshesOf Time)特为典型。爱情、功夫只是表象,真正显现的是:人如何在当时、当境处理他的一生,处理他所拥有和所失去。鉴于以上的所有“理论”铺垫,我试图回答上面提及的三个问题:1、“一开始便已经死”意味着什么?2、它与“成为蛮荒”、“(废尽)时日”有何关联呢?3、成为蛮荒是因为不加照料之故,还是自我放逐之故?
四、评论:何以一开始便已死去及其它?
“一开始便已经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未曾真正地活过。旭仔的生活里始终有两个内面牵引着他:自己的源和自我的意义。他的生活表象是:与两个女人(也许更多)做爱。然而在这里,或者这种论说里只能看到两个端——始、终,而看不清任何与“成为蛮荒”、“(废尽)时日”相关的东西。两个端,即始、终构成了线性时间的必备要素,却没有构成自我的内在时间。有了对原始的追求和渴望,以及对终点的探寻,便有了物理意义上时间的规范和边界。在这样的范围里,我们变得可以诉说和表达,死亡的方式才能向语义开启。
自我生成于厌倦。“我”向内“看”的时候,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时,自我便生成了。自我既成了对象,更成了本质。这带有黑格尔的思维倾向和观察角度。然而“我”之所以向内察“看”,一定是建立于某种区别之上。一种“我”与世界的隔阂之上的。与世界大同,是没有思虑之心的。能很好地起到建构作用的是人的生存本身状态,即厌世。旭仔心里始终装着这两个端的问题,时有模糊,时刻为之折磨。他需要找到具体的解救之方,找到具体的实践途径——付诸行动。这条路便是从女人的温柔,不值一名的柔情里剥落出来,去寻找更为普遍的普遍者——他的生命之源。旭仔说“我只不过想看看她,看看她的的样子。(见见生我那个人的样子而已)”。这是原始的诉求,寻根的需要,它与欲望无关,即不被欲望牵引,但它却是欲望本身,常伴人的一生。自我的疲倦可以通过性来发泄,但绝不能通过性来拯救。自我的追根不是欲望的发泄,却是欲望之光,时刻照耀着冲动与克制的自我,毋宁说自我就是这光本身。旭仔想在死亡之际,明白自己“最后一刻会看见什么”。会“看见”什么?人存在在光里,什么也不会看见的。自我化身成欲望之光,那里没有黑暗、光明的对比,没有深渊,有的只是空洞的永远的一刹那。绝对的光明,也是绝对的黑暗,无所见,无所不见。旭仔“看不见”自己的“死”,也看不到任何东西。空洞的永远的一刹那,只是陨落。在我们看来是陨落,他却认为是解脱,一刹那即为永恒。看来无法对此给予价值评价,有的只是看清它曾经在时间里驻留、存在着。谁能说清它的本质呢?
厌倦造就了时间。既然时间不是悬挂在墙上钟表里的时间,时间会是什么呢?不,不能如此粗暴地对待时间,不能如此地向时间发问。时间不是“什么”,时间只是如何地去存在,并且存在于何处。旭仔何时意识到时间的呢?是在楼底与丽珍进行调情的时候吗?因为那场景里明确提到了时间,一个个仰视镜头拍打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并且旭仔和她在直愣愣地盯着手表,默数着一分钟六十秒。
苏:你到底想要怎样?
旭:没有,我想跟你交个朋友而已。
苏: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朋友?
旭:看着我的表。
苏:干嘛要看着你的手表?
旭:一分钟吧!
(滴答…滴答……)
苏:时间到了,说吧。
旭:今天几号了?
苏:十六号咯。
旭:十六…四月十六日。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时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一个事实,你不容否认的。因为已经过去了。我明天会再来!
苏:他有没有因为我而记得那一分钟?我不知道。但我一直都记住这一个人。后来,他真的每天都来。我们就由一分钟的朋友,变成两分钟的朋友。没多久,我们每天最少见一个小时。
(……缠绵于床上)
记得“时间”。时间本身成为对象?时间是不能单独地成为对象的。或者根本说来,时间不能通过对象性得到理解和领悟。时间只有与物相连才能被记忆、回想。毋宁说,记得的是物与时间的关联性。如果我们仅仅在:我记得“床前明月光”是出自李白《静夜思》一诗上使用“记得”这个词。如果出于知识论的立场,那么“记得”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身居时间,才能让我们去记得,而非相反。谁能把时间本身当作对象,而不添加丝毫事物呢?谁能说我要“征服明天”,而从不涉及明天之所行呢?
可问题恰恰在于:处在时间之中所谓谓何?正是孔子一句话点明了旨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全体,而全体又被贯通在一起,彻头彻尾,彻上彻下。我以为“在川上”是整句话的重中之重,最为核心的东西,而非“逝者如斯”或“不舍昼夜”,抑或两者之关联。“在川”之“在”不仅是时间之“在”,更是整个此在之“在”,整个生命历程的全部浓缩之“在”。因而这一个“在”字,不仅被形象表征为时间:逝者;而且被表征为空间:“川上”之“不舍昼夜”。记得时间是一个错误的表达,却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真理,即深深地被时间缠绕,会造成人的厌倦和失落。
旭仔在与女人交往中是没有时间性概念的,他难以在时间上或者没有在时间里谋划。他只是看似在时间里消费自己的身体。当身体走在了领会根源性的前面,反叛往往会爆发。他会出走,游离,逃逸,甚至自杀。必须结束这个身体,似乎才有所安顿。这就是承担错误的真理必须付诸的代价。厌倦不是厌倦时间,时间不会被卷起,时间只会从你身体里穿过。厌倦的是无序的自我,没有被时间格式化的自我。
以上便是“一开始便已死”在时间意义上的涵义。
“一开始便已死”与“成为蛮荒”、“(废尽)时日”有何关联呢?这个问题就决定了应当如何度日。度日如年、光阴如梭,都在某方面道出了时间在节奏、缓急上的含义。它其实与时间本身没有多大关联,更为相关地被认作是心理学范畴。持这样的观点,是在客观立场上看待时间,认为它是独立自存的现象。旭仔最后的死,是偶然,但同时也是必然。也可以说是,在偶然的不确定性中必然地爆发了。偶然只是陈述着事件可以复杂多样,也可单纯不变;但事实却是必然如此发生。这就像在舞台上舞蹈,舞起生命之殇。舞台便是偶然,起舞则是必然。我们通过这些事实的理据,看到了生命某种轨迹式的东西——挣脱不确定的自我。在不确定里挣脱,无所谓挣脱;在确定里挣脱,是不必要的挣脱。
“成为蛮荒”、“废尽时日”只是一种现象之表征的语词表达,然而这种表征并不诉求一种所谓背后的本质,它不能。表征表达出一种理解的结果,却不能自行表达出自己。“成为蛮荒”、“废尽时日”表征着放荡、堕落、颓废如此等等,然而处在关联性之中的中介——表征却没有表征出自己来。毫无疑问,“成为蛮荒”、“废尽时日”都需要“荒唐”的行动来完成,然而“表征”却没有一种行动。它存在于理解里。说旭仔是按照理解去活着,必然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这种理解,理解不了旭仔的“想”和“行”有什么具体的事实相关。这种理解背后的观念,毋宁是以这样的支撑为根据的,即认为“想”指导并且通过“行”得到释放。如果这样的话,理论永远跨越不了现实的鸿沟。
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便已死”既不是所谓的“想”的价值原则,成为了某种理论指导的东西;也不是单纯地某种情绪化的焦虑之感,成为了某种驱使的心理学动力。它毋宁是存在的现实状态,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理解它如何发生。它的存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但使得我们能被理解,包括旭仔的行迹。凡事都需要点切己的工夫。而“成为蛮荒”、“废尽时日”既不是所谓的在“想”的前提下“行”的结果,成为了价值观的牺牲品的东西;也不是单纯地个人人格化的表征,成为了反面典范的人物特征。它毋宁是一种指示和路标,逼迫旭仔在路上去表达自身,他试图尝试着突破受限制的自我。只是他不知道在蛮荒之地,本无路标,走过人生之路,才发现自己就是那路标。路标需要以死亡来换取。
以上便是“一开始便已死”与“成为蛮荒”、“(废尽)时日”不可能有的关联。说不可能有的关联,只是道明这种关联的天然性,而非存在着一种待评论者揭示的关联。
成为蛮荒是因为不加照料之故,还是自我放逐之故?都不是。“成为蛮荒”本就是一种自我照料;而“放逐自我”本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是A=A,而是人=世界。至少这个“=”是盲目的勇敢。盲目是在观者眼里看来如此,勇敢是指我们绝不可能如此效仿。
我最想知道的是我这一生,人最后一刻会看见什么。所以我死的时候,一定不会阖上眼睛。
“我”一定不会阖上眼睛,他真的没阖上眼睛——直到死去。到死,都还要在生的余烬里奋力地抗争。这种抗争是温柔的,既不见血,又不见挣扎。他对生命有所认同了,因为他的生命本无任何认同。有很多诠释者把《阿飞正传》这部电影看做反映90年代香港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迷惘、浮华、躁动不安,不一而足。然而,并未诠释出迷惘、浮华、躁动不安是谓何?把电影看做“反映”式是思维最初级的阶段,是慵懒者的思考,因为他们只是在“看”电影。“成为蛮荒”不是因为不加照料自我、自我放逐造成的。这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是人的生存结构如何搭建的问题。木头和砖瓦必然能造房子,但永远不是房子本身。可木头和砖瓦,却能独立成为房子本身,如一块大木之下就可蜗居,一批土砖之下即能开灶。这就是“反映”式解读所达不到的地方。也是把成为蛮荒理解为不加照料和自我放逐之故的思考形式。然而这样的理解根本上是错误的。旭仔虽走在了一条错误的解脱之路上,但他的错误本就是真理,因为他用死换来了路标。尽管他自己没有看到。超仔其实不是不知道他自己最想看见什么(当然他不会知道),实则是他不想去看。
附影评稿:
时间、自我、记忆、回忆。死亡。静物书写、镜头跟踪、长焦纵贯、短距晃动。偶然、不确定性、意义、虚无。爱情。影子。拯救。逍遥。身体。存在。欲望の翼(日本译名)。
超出原有的表达。
野蛮。蛮荒。开拓。降服。屈从。挣脱。再创作。死寂。羽翼。话语与表达。死亡与方式。语义开启。表达领会。殇。
之昶书畅春新园
2013年11月21日深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