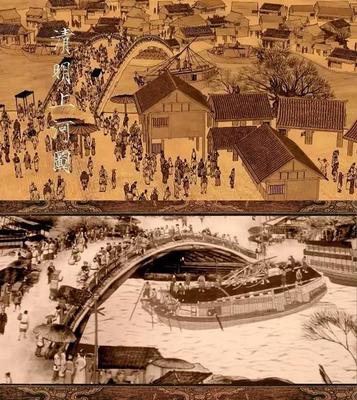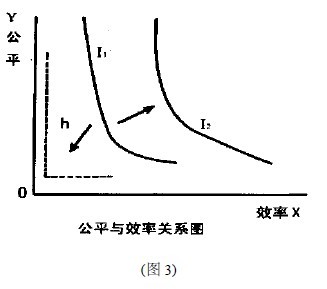几年前正月某个上午,太阳正好,我回到故乡。走在曾读高中的县城街道,望见熟悉的资江在井口潭折弯北上,看到身边一个个人走过,没有一个人注意我,当然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一刹那间,我强烈地感觉到:我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这种惆怅,在贺知章的诗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中流露过;鲁迅也曾在文章中感叹“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但毕竟,我正站在故乡县城的街头,那感觉和身处云南某个村寨、东北某个小城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父母把我降生在故乡,在这里有我的祖坟、老屋、族谱和年迈的父母,这里曾留下我十八年的时光。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出身地、成长地和祖籍地重叠在一起的,实在是一种奢侈;能回到故乡找到祖坟、老屋和族谱的,算得上城镇化大潮中的幸运儿。
我很幸运,我的祖籍、出生地、成长地,都在湘中的邵阳市下辖的新邵县。在那块群山起伏、资水奔流的土地上,我的宗族繁衍了六百年,族谱清清楚楚地记载各房开枝散叶的过程;七世祖以下的祖先坟墓还都能在某座山上找到。对我而言,“故乡”二字的指向是如此的明确。
我什么时候开始有故土情结?大概应该从二十五年前离乡那一刻起。
在十八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故乡的山村以及读中学的小镇上度过的,离山村25公里的邵阳市,在儿时我的心目中那可是繁华的大城市,去过的次数屈指可数。喝着故乡的泉水、吃着自家田里所产的稻米,我懵懵懂懂地长大,尽管我阅读的课外书在同龄伙伴中算是数量较多的,和他们相比对山外世界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憧憬。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无法真切地感受山里的故乡和外面的世界,在地理环境、居民气质、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等方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似乎我们那样生活才是天经地义。世界,应该是那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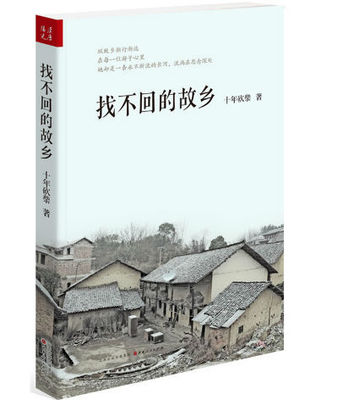
1989年的9月,我揣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裤衩里缝着妈妈塞好的700元钱,搭汽车到邵阳市,坐火车到长沙,然后换火车走京广线到郑州,在郑州再倒火车顺陇海线往西,历经三天两夜,在一个阳光很灿烂的秋晨抵达了距离故乡近2000公里的兰州。从此,我开始了漂泊在异乡的岁月。
第一次离家远行,心情是激动而又忐忑的,觉得外乡有无比精彩的人与事等着我,又担心处处有危机和陷阱。坐在火车上,脑海中那点史地知识不断地被激活:渑池、临潼、华阴、马嵬坡、新丰镇、天水,这些以前只有在书本上看到的地名,眼下出现在车窗外的站牌上,那样遥远而又亲切。
我所上的那所学校在民国时便是国立大学,读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域里成长的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会有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我所在那个宿舍7名兄弟,4位读中文3位读法律,分别来自湘、鄂、苏、陕、甘、吉,吉林那位还是朝鲜族。那年月能考上一本的都是所在学校的尖子生,从小都有某种不甘于人下的优越感,住在一起自然相互比拼,包括学习成绩、组织才能、口才以及吸引女孩的指数。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晚上熄灯后夸自己的故乡。于是,在老家时并不太在意的乡贤,此刻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做过的业绩似乎讲述者也与有荣焉。
我和不少第一次出远门的湖湘子弟一样,在与外省朋友闲谈时,将清朝咸丰、同治以来一个半世纪所出的湘省牛人挂在嘴边。--时隔多年后,想起大学宿舍里唾沫横飞的夸耀真有些汗颜,那些人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功过自有历史评价,碰巧只是自己降生在湖南,自己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现在释然了,这就是成长的经历,一个年轻人出远门,除了万丈豪情还有什么呢?故乡那些人与美景,能给他增添些许的闯世界的信心吧。
因为要向外省同学夸耀,于是在大学时便有意识地读一些有关湖南的历史、地理书籍,对自己的故乡算是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譬如说了解到我所就读的那所大学与左宗棠有一段渊源。由于陕、甘两省乡试长期合并在西安举行,左公督陕、甘时怜惜甘省赴考生员诸多不便,便上书请于兰州萃英门另设甘省贡院,独立举办甘省乡试,朝廷准奏。然甘省独立乡试时间很短,就到了1905年废除科举,1909年官府在原贡院兴办了“甘肃法政学堂”,此乃兰州大学建校之始。我也了解到抗战胜利后才正式有了“国立兰州大学”的名号,而时任校长的辛树帜先生是湖南临澧人。了解这些历史,似乎遥远的大西北--虽山川、风俗与故乡相差甚大,但不觉得寂寞与陌生。因为同乡先贤们在这块土地上颇有建树,对来自湘省的晚辈后学如我者不无激励。
1993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在这座城市迄今已待了二十一年,超过了我在湖南的时光。我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算是扎下根来了。湖南,仅仅成为“籍贯”所在地,成为了“故乡”。然而,在五方杂处的京师,人与人交往,介绍自己或问对方“哪里人”,决非法律意义的,即身份证上所标识的地方,而一定说的是其文化上的归属地--即故乡是哪里的。就算我在北京再活五十年,我仍然是“湖南人”而非“北京人”。北京至长沙的高铁开通后,我第一次坐高铁回家,看到长沙南站的广告牌上写着“我从北京回来,但骨子里还是个湖南人”,便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但激动归激动,随着离开故乡年头的增加,每次回乡我都觉得故乡和自己的疏离,尤其是现在的故乡究竟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村里那些小孩一天天长大,离乡去南方打工,他们的人生和我已没有任何交集,即使有一天在街上相遇,也互为陌生人;而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们,一天天老去,辞世。故乡,好像越来越像一个符号。
不甘心自己与故乡相互遗忘与疏远,于是我试着去追寻故乡的过去,打捞故乡的旧影。
在追寻故乡往昔的过程中,我惭愧自己以前并不很了解故乡。当年对故乡的夸耀,所依据的无非是所共知近现代史上的湖湘人物和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撇开这些,我发现故乡的往昔有着更多生动的故事、美丽的纹理和一个个被大人物遮住的、有意思的小人物。这些,或许更能代表故乡过去的风貌。
在追寻和打捞中,我觉得自己和故乡的距离更近了。常在夜深人静时,我在北京的小书房里,翻阅着乡贤们的文集或湖南各地的方志,故乡的往昔是那样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高山峻峭而森林茂密,大河曲折而湍急,人们多情而侠义尚勇。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不论他们死后名垂千古还是籍籍无名,他们的人生故事都很精彩,写下来都是一本好看的书。可惜,太多人的故事没有被记录下来。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宝庆府的先贤邓显鹤先生的事迹很让我感佩。湘皋先生“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我没有湘皋先生的幸运,能在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故土,有搜集乡贤嘉行、整理故土风俗的地理之便,也没有湘皋先生的大才和坚韧之志。我只能在谋生之余,身处浮华的京城,一点点搜寻那方水土和那里人物的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我无法呈现故乡往昔的阔大和连绵,只能凭自己的努力打捞些许的旧影,书写自己对故乡的认识与情感,于是有了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
与灿若群星的湖湘先贤和时贤相比,我对故乡的认识无疑是浅陋的。但每一个湖南子弟的眼中都有一个湖南,我眼中的湖南就是这个样子。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对故乡,每个游子都有说不完的感受。这本书,只能算我对故乡万千思绪中撷取的一些片段。对我的湖南,我还将继续认识并书写。
最后,感谢故乡前辈周玉清和于建嵘两位先生为我所作的序言。周先生身居高位,来到北京多年,然而一直关心家乡,对在京的家乡子弟关怀与照顾更是不遗余力。尤其令我感佩的是,他与我们这些同乡晚辈交谈,仍然是“宝古佬”加读书人的本色。此书稿得到其谬奖,我感到高兴而惭愧。于建嵘先生按年龄上是我的兄长,但他的学识见识和忧国忧民之心,让我一直以老师看待。认识他十多年来,他对我助益多多。他们看重这些文字,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要给热爱故乡、愿意追寻故乡往昔的晚辈一种鼓励。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1971年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作、编书、卖书。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网络红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