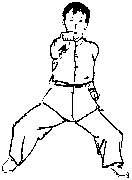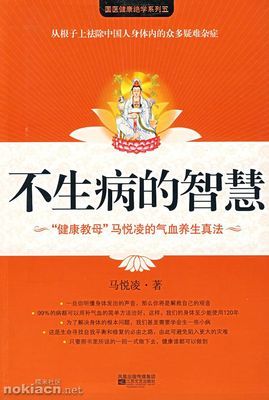《作品》2013.8期/牛红丽
农历二月,石角街到处弥漫着嫩树叶和青草的新鲜香味。在这香味里,我背着皮书包,由二婶牵着手,走在通往新学校的油渣路上。
皮书包在学校吸引了众多围观者,我大度地由着同学们赞美,闭口不谈皮料来源。二叔曾割下垃圾箱里一只旧沙发所有的皮子,除了给我做书包,还做了两个挎包,他跟二婶一人一个,在当时的石角街,简直时髦得不像话。为了配皮包,二婶特意换了身干净衣裳,有晒过的肥皂香味,母乳一样让人留恋。她走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听到老师点名,好学生秦小阮,转学第一天就挨了板擦。
放学的时候我哭了,不是因为人生第一次板擦,而是因为迷了路。石角街的道都是斜的,整个豫南,你再找不出这么考验记忆的地方。石角街人懒,年年守着老祖宗的产业,瓦都懒得换一片。清一色的鱼鳞瓦单匹墙,背靠背或者嘴对嘴,凑成网状的小巷。不熟悉的人一旦绕进去就出不来了,要么进了死胡同,要么就回了原地。我钻了好几条胡同,结果都在同一巷口被吐出来,于是,抱着膝盖蹲地上哭起来。
你是赵荣家亲戚吧?我正哭得来劲,随着苍哑的女声,身后伸过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细而弯曲的指甲,让我想起二婶的泡鸡爪,我不敢再哭。鸡爪没有抓碎我的骨头。那是一张白得发青的脸,下颌尖得像准备写字的铅笔头。我没见过下颌那么尖,表情那么刻板的女人,挣一下肩膀,没有挣脱。
她喘了口气,说,要想回家,就乖乖跟着。说完歪歪斜斜向前走去,踩出的每一步都是虚的,让人看不清到底走了还是没走。
我跟了上去。
她把我送到家门口,交代说,学校门口是解放路,顺解放路往西,中间的巷口都不要停,见菜场朝南,到城关火神庙……她说话的时候对着我的脸喷出一股股冷气,好像嘴里含了冰。我抬头看看天,大好的太阳竟晒不化她嘴里的冰。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指示,先菜市场,接着挂毛主席半身像的火神庙,再然后就到了甜水井。紧挨甜水井两间半新的大瓦房,门口一棵疙疙瘩瘩的老枣树,那女人端着一只搪瓷碗,就坐在树下喝药。头戴白帽,身包宽大的男式对襟灰棉袄,脚下一双突兀的大头棉鞋,整个人就像树上的一个老疙瘩。她没有发觉我在看她,白帽子按碗里喝得起劲,喝完瞪大眼睛看,似乎检查喝干净了没有。
我经常撞见她喝药,坐门槛上或枣树下,喝得慢条斯理源远流长。仿佛她喝的不是药,而是不能辜负的日子。豫南春天短,这边刚脱掉冬棉袄,那边太阳就毒了。虫意儿飞了,枣树叶子肥了,罩着铅笔女人绿汪汪一大片。埋在树下的药渣,把虫子养得又肥又胖,二婶的小毛鸡在老母鸡带领下总是叽叽叫着往她院里跑。每天傍晚,我都要把围着树扒虫的鸡赶回家。她闭眼坐在那不见我,我也不多话,三天两头的竟是谁也没搭理谁。
事实上我并不讨厌她,只是感觉不舒服。比如我喜欢穿裙子,纯白的亚麻布裙,辫稍扎两根红绫,天还不够热的时候就早早把裙子拿出来,显摆整整一个夏天。而她却突然让我对裙子产生了怀疑--在我光着手臂小腿汗流不止的时候,她还包着老鼠灰大棉袄,没一滴汗。我断定她没有汗毛孔,眼瞅着她顽固地坐在树底下喝药,喝完拉长脖子,冰糖放嘴里咯咯吱吱地嚼,嚼得我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感觉到了寒意,脖子、胳膊、直到小指头。我怀疑自己季节判断失误,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直望到灰疙瘩化成一坨软泥巴,方才替她感到惋惜,也或者,彻底化到泥里倒干脆。
放学回来她还在睡,肥大的袖管紧捂着膝盖,生怕灌了风。我背着书包站旁边看着,真怕她就这么睡过去了。她白帽子周围没有一根头发丝,联想到之前的不出汗,我猜想她可能光头,便弯下身,又往前迈一步,不想踢翻药碗,药渣里拱出一条软塌塌的蚯蚓。我咯的一声转身就跑。
她在后边追,慢,慢点!破竹筒里抽拉出来的声音,简直要把人榨出油来。我捂上耳朵回头张望,大棉袄好像寒风里的一把干芦苇,还在飘飘忽忽前移。我立马住了脚,我怕她真的会像干芦苇那样咯吧一声断了。再说石角街巷子窄,常年不见阳光,青砖路面早爬满了青苔,湿溜溜不拿脚。我刚来的时候曾经很奇怪,二叔二婶的鞋子怎么都是绿的?后来我发现我的鞋子也是绿的,石角街所有的鞋子都是绿的。外边的人喜欢盯着我们的脚,玩味地问一句,石角街的吧?我经不起调侃,回家拿刷子使劲刷。二婶说,小阮,别刷了,刷也白刷。真是白刷,那绿毛顽固得碱面都刷不掉。我们的生活快被青苔给埋了,但我们粗壮、肥大,倒是那霸着巷口宽敞地的女人,整日晒着太阳还晒不掉大棉袄。难怪街坊们叫她“药罐子”。
发现“药罐子”的秘密,纯属偶然。
源于对音乐和画面的天生敏锐,我喜欢琴。附近每晚都有人拉琴。我静静躺在床上,听着听着眼前就飞出了一群小鸟,在蓝色的月光下嬉闹、蹦跳。便忍不住悄悄溜下床,扭开门走出巷口。月亮又滑又亮,甜水井只不过是一个静默的黑点。虽说甜水井的水是甜的,街坊们点豆腐也只认甜水井,但是,真的会从一口井里飘出琴声吗?
一曲终了,余音散去,只剩下风吹着月亮,洒下满地婆娑。
我发现有一个人在“药罐子”门口像我一样悄无声息,海棠红高领毛衣,绣花流苏披肩,兰花指小碎步,眼波流动,款款盈盈。看样子她在唱戏,无声戏。我刹那间明白了所有属于女人的美好。后来我知道,那叫“风情”。
女人“唱”了一会儿,坐椅子上,手里多了把琴。我看到她铅笔一样的脸型在月光下柔和许多。
原来她是有头发的,绾在头顶。
她又拉琴了。寂静的群山、薄雾、彤红的云,溪水边第一声鸟叫,唧——荚——荚!
植物开花了,芽儿努嘴儿了……
山道上扯出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骑马的新娘,红嫁衣……
夜风掀起披肩,女人哆嗦了一下,一双吊稍眼流露出白日见不到的媚气和喜气。我一下子喜欢上了那双眼睛,虽然,我不知道尾稍上翘的眼睛就是丹凤眼。这有点像古桥上的恋爱,我想我喜欢上了一个女人,喜欢上了她的琴,还有琴声里的小鸟。
风停了,琴声戛然而止。鸟儿扑啦一下飞走了。
她脖子边赫然挺着一把雪亮的刀。
拿刀的人蒙着脸,叫人看不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等终于明白他要杀了“药罐子”,是个歹人时,却只迈出左脚,再迈不出右脚,如娇小姐一贯的那样,窝囊得只会淌眼泪。眼泪也会淌出声音,我忙用手背擦去。
别动!
她不动。放下琴,铮的一声响。她慢慢直起身子,忽然恶狠狠向刀尖横过脖子。我的心唰一下凉了,然而,却清楚地看见,男人后退两步,刀子当啷落地。
我从地上爬起来,拎死蛇一样把刀扔进井里,跑回家拿条线毯盖她身上。
她在毯子下发抖。
我懵了头。男人临走骂她是破鞋,还说会再来的。她真的是破鞋吗?刚才,为什么不呼救?为什么白天黑夜两个样?我越琢磨越觉着她就像人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么她就不是一个好女人,她对不起我的喜欢。我有点恼火。
谢谢你,小阮。她说。
我刺猬一样竖起满身刺,严厉地对她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不准叫我小阮!又觉着有必要为了所受的蒙骗再做些什么,就使劲朝她脸上啐了一口,臭流氓!然后,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抖着心,飞快地跑了。
我认定了她是坏女人,却忽略了所有坏女人的常规。坏女人不会管迷路的孩子,不会把好衣服留在夜里穿,也不会拉琴,更不会把自己的日子糟蹋成烂抹布。我可以不理她,但不能不理琴。每晚临睡前我都把耳朵打结,耳朵自己偷偷解开,我再系上,它们再解开。我就没办法了,我说你们是最不听话的耳朵。可是三天没有琴声了,想到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想到死亡。那样的人,即便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吃惊。
没有了月亮的石角街就是紫色的,飘过来的药味也是紫色的。一团一团的乌紫里都藏了暗鬼,随时准备扑出来,把人拖走。我东张西望跑到甜水井。有一只萤火虫趴在药罐子的门鼻上,明明灭灭,奄奄一息。刚要抬手拍门,我听见里面的床吱呀响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那只熟悉的曲子了。真是啊,她怎么可能不拉琴呢。
据说“药罐子”是青衣和官员的私生子。官员怕影响政途,留下所有积蓄,打着支援边疆的旗号溜之大吉,对她们母女,就像甩掉脚后跟的一坨臭泥巴。“药罐子”自幼跟青衣“师傅”学戏,凭着天生好嗓子,自然红了。但她始终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生母。有一年下乡淋了雨,回来她就开始发烧,打针吃药都不管用,连烧四天四夜。再开口说话,就像地狱里跑出的恶鬼了。青衣不停给她洗冰水,才保住一条命。后来青衣给她一把祖传的胡琴,在剧团改了伴奏。冰水给她种下了病根,她越来越怕冷,正拉着琴,忽然冷得坐不住。后来青衣不在了,她被好言相劝回家养病。团长承诺说病好了还可以回来。她拿出多年积蓄,在石角街挑一处向阳宅院,就在甜水井旁边住下了,每天把喝药当任务,等着病好了回剧团呢。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自幼跟瞎子拉弦子唱戏,偶然被团长探到戏班,才有了后来的发烧破嗓。
我辨不出两个版本的真假,但我真诚地替她委屈。无论哪个版本,她都不能活得更加明白些。
她后来也收养了一名小叫花。孩子随她姓叫何家欢,门齿奇大,两齿间距离遥远,留下的齿缝装得下一颗绿豆。
人家问,家欢,几岁出来的?
他踢一只坏土豆。
又问,家是哪的?
他冲人龇龇大板牙,吐出两个字新疆。
“药罐子”笑了,说你那两颗牙,上辈子有仇。
人又说,送你回新疆去。
何家欢摇摇头,咬着下唇,故意把鸿沟齿缝再突出一些,逗得“药罐子”直咳嗽。
“药罐子”咳着咳着就忘了喝药,每天慢腾腾兴奋奋地洗衣做饭、灌油买菜,忙得不亦乐乎。那么多蚯蚓没白喝,她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了,穿着海棠红毛衣,竟是完全康复的样子。那年费翔的“一把火”烧红了半边天,烧得青年男女找不着北,报上说是“奇迹”。依我看,他最神奇最值得称颂的不在于此,而在于烧掉了“药罐子”的大棉袄。
脱去大棉袄,我们才发现她比谁都干净。我们洗菜到水房或者护城河,她不,她用井水洗。一把小白菜一碗米,糟蹋半桶水。她不会摆水。摆水是技术活,绳子系着桶袢在井面上来回晃,越晃越快,直晃到桶身倾斜,一抖绳,桶就懂的一声扣下去,顺势灌满水拉上来。她呢,站井台上只会磨桶袢,吱吱扭扭,磨得旁边的人着急了,还听不到懂的一声响。遇上了大家都会搭把手,她不知道稀罕,洗菜淘米也就罢了,洗手也用井水。一双手在盆子里洗啊涮啊搓啊,完了用指甲抠,手心手背指甲指缝手指肚,抠得人冒汗。
“药罐子”走路腿不跟心,往往身子没到,额头先伸了出去。为给儿子改善生活,她整天提着编篮怪模怪样走在去菜场的路上,脚步迟缓而急切,遇到年轻人手拉手骑着自行车,都下意识地躲避,生怕自己的慢阻碍了年轻人的脚步。
有些人注定是走在前边的。前两年护城河起了淤泥,有人种上莲藕。这年夏天,浮起三两只瘦荷,到了黄昏,有很多蜻蜓在花间忙碌。也有女人在河边淘米洗菜,刷车子。“药罐子”扎着黑亮的马尾,穿着海棠红毛衣,也去了。
她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大着胆子走到她身后说,对不起,我不该吐你。这句话酝酿太久,说出来连舌头都僵硬啦。
她噗的一声笑了,说,傻丫头,六姨跟孩子记仇啊。
啊?噢!嘿。我语无伦次。她反应之快让我吃惊,接着恍然大悟(她知道我跟着呢),再接着,又开心又不好意思起来。
虽然第一次搭话,但我坚信她跟我一样,早熟悉了彼此。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让叫六姨,就叫了,六姨,你喝那么多药不苦吗?
没办法,捏着鼻子灌,吃床腿似的。
病好了还回剧团吗?
回不去喽。
怎么回不去,他们答应过不是嘛。
呵!你没少做功课啊。
我嘴上没说,心想比这知道得都多呢。那首曲子叫什么?挺好听的。
曲子啊,没名。当年,师傅最喜欢的就是它。日子过得越难缠,师傅拉得越欢快。
师傅是谁?
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没人正面回答我,后来就不问了。
她说着话,开始往回走。我跟上,那琴听起来不一样呢。
是啊,那是马骨琴,快绝迹了。都是忙着往前走,走得越快,丢的东西越多。早早晚晚,把自个都丢了才算圆满喽。
我听不懂,说,何家欢的名是你取的吗?
合家欢。呵呵,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看见人家结婚就心痒,心想,我要是长大了,要么不结婚,要么,就踩着高跷去结婚。
踩着高跷啊?那,那你结婚了吗?我惊异地问。
结黄昏哦,谁要个病篓子。
你那么漂亮有本事,肯定有人要。要是没人要,我要。
呵!小妮子。
六姨,我喜欢你,还喜欢你的琴。
回头我教你。
第一次去六姨家,她戴着荷叶边围裙正折腾一条鱼,菜刀在鱼身上试探着,好像忘了从哪下手。
她对着挣扎的鱼叹了口气,哎,谁让你做了鱼哟,忍忍吧,我给你个痛快。说完闭上眼,把鱼高举过头顶,啪!摔下去,鱼就不动了。
如此宰鱼。
她指着地上的死鱼对我说,你早点来就好了。这东西,拿捏死我了。
早来又怎样呢,从小到大,我跟她一样没杀过鱼。鱼没少吃鱼汤没少喝,唯独没有对一条鱼下过手。
何家欢拎着棍子冲过来叫,六姨六姨,树上有马鸡鸟。
马鸡鸟?好,好好,我给你摘。马鸡鸟就是知了,六姨丢下鱼,探着额头磕磕绊绊去了。
太阳光把六姨的家切成一明一暗两个板块,暗影里放着五斗橱,两把椅子,对门一张梳妆台,摆着些贝壳做的蛤蜊油,霞飞护肤霜什么的。左边涂满了阳光,墙上的物件便有些不大真实。有一挂永远停在三点一刻的钟,还有一把纤秀的二胡。二胡顶端的马头栩栩如生,弯着脖子,分明是一只害羞的小母马。
六姨取下琴递给我说,这就是马骨琴。
原来不是二胡。我拿着琴不敢乱动。
六姨说,琴筒是马的大腿骨做的。
残忍呢。
残忍?呵!不。六姨让我坐,接着说,马骨琴又叫马骨胡,壮语叫“冉列”,是壮族拉弦乐器。琴筒是马或骡子腿骨,一端蒙蛇皮,鱼皮或蛙皮。弦是牛肠弦或丝弦,马尾竹做弓。声音清婉嘹亮。
很早以前,我们壮乡有个姑娘叫阿冉。阿冉和阿列从小青梅竹马。阿冉家有一匹枣红马,四蹄雪白,叫“四蹄雪”,被土司重金强行买下。又见阿冉貌美,连人带马一起抢回山寨,关进后院。土司乘兴试马,摔得头破血流,一气之下杀了“四蹄雪”,剥马皮剔马骨,丢在阿冉面前说,再不答应,要她像马一样。阿冉悲愤地拔下长马尾,收起一条大腿骨,请土司长工捎给阿列。阿列用马腿骨做琴筒,马尾做弓毛,制成一支马骨胡,用琴声向阿冉传递营救时间和办法。夜晚救出阿冉,射死追赶的土司,连夜离开了山寨。
后来,夫妻俩在琴上雕刻了马头,走遍壮乡村寨,专门传授马骨胡。为纪念阿冉和阿列,马骨胡就叫“冉列”了,流传至今。可惜,懂马骨胡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抚摸着琴弦,仿佛触摸到了“四蹄雪”。
里间传来,《霍元甲》的嗨嘿对打,还有何家欢蹦跳呐喊的助威。
整个暑假,我一直跟六姨学琴,直到有一天,六姨家来了客人。来人拎着一兜点心,张口说请六六出山。
六六?我诧异地望着六姨。
六姨眯了眼问,您是?这一声问,竟撕裂了那人手里的点心包,点心掉下来碎了一地。他不相信地打量着六姨,似寻找声音出处。
此后,六姨长了心事,再去菜场,必绕道南街红星剧院停上一会儿,摸摸镂空的门窗,再摸摸溜光水滑的大红圆柱子。离开的时候,便是连额头也伸不出了。红星剧院的圆柱子凭空给她长了二十岁年纪。可是还有何家欢呢,她没时间伤感,很快恢复脑袋前冲的姿势,继续慢吞吞匆忙忙劳碌。
我去市二中后,县里建了客车站。解放路扩宽了,两边栽的杨树划开蓝天,像两条齐刷刷游向远方的青龙。这种速度的暗示,让慢吞吞的六姨也开了窍,邀我周末学车。她托人买了辆苹果绿自行车,说,何家欢不乐意骑。我暗笑她的私心。宽敞的水泥路面上,六姨骑着苹果绿自行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我喜欢看青灰路面上划出的绿弧线,喜欢看她抓着车把紧张的样子。在何家欢示意下,我们一起松手,轻轻往前一送,连人带车就出去了。随着一声尖叫,再看六姨,已是一头汗。
丫头小子,害我!
帮你呀。这么宽的马路,车没有一辆,人只有几只,你怕什么呢?我说。
六姨放倒车子,扇手喘气,冲已跑远的何家欢喊,你等着,坏小子,晚上没你饭吃!那一脸红, 一脸油汗。以前,她是从不出汗的。
我托着腮,蹲下来看她,笑。
六姨伸手打过来,还笑!我顺势接过那只手,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结合对她的了解开始胡诌。她却听得认真,说,你说得对,我就是,就是。
弯弯曲曲的纹路在秋阳底下闪着光,让我想起迷路的春天、指甲奇长的手、还有铅笔脸白帽子、疙瘩树、老鼠灰大棉袄……这些零碎,多像镜框里拼兑的黑白照片。
有了自行车,身子永远跟不上脑袋的女人从此在马路上飞了,石角街也灭了一个慢腾腾的身影,似乎离繁荣更近了。

兜点心的那个又找过六姨一回,是冲着马骨琴。她没去。她说我要去了,何家欢怎么办?扩路把甜水井扩没了,一停水好几天,到时候他连水都喝不上,总不能再回去讨饭,等初中毕业再说喽。
说这话的时候,距离何家欢毕业还有四年,稀有的马骨琴四年以后什么样,我们谁都没去想。
上医专那两年,水泥厂纺织厂环城公路南山体育馆相继在石角街冒出了。唯一没变的还是那些小巷,安分地交叉、静默,细致地长苔,只是我们的鞋子不再是绿的。绿鞋子永远从石角街消失了。皮革的鞋面不怕潮,也染不绿。后来的某一天,已经长成半大小子的何家欢,甚至踩了一双锋利的旱冰鞋,嗤一声从面前亮闪闪划过。见到我他没有停下,顺着能并排跑四辆卡车的解放路,潇洒地冲向广场,身后摩托车汽车,喇叭齐鸣。我张张嘴,像当年六姨追我一样向他追去,然而他已跑远了,回头做着“√”的手势。阳光下,我没有看清那条鸿沟齿缝。
我在护城河边找到六姨。那儿没有青蛙王子,也早没了碧叶荷花,连只活物都没有。河道里堆满纺织厂菜场的垃圾,引不来一只苍蝇。连续五个月的干旱,周围污水腐蚀的土地龟裂了,绿油油的秧苗被蜘蛛网裂口所代替,寸草不生,光得如陈列馆里的龟壳。我敏锐地捕捉到六姨的沙哑里又多了一层新的东西,眼角眉梢的皱纹、鸦青,那都是属于年龄的。
水泥厂的浓烟从头顶翻卷而过,裹着太阳,像裹着一只没有着色的白草莓。我问六姨,红星剧院怎么成了影都饭店?
时代发展了,有些东西就留不住。人啊,就是这么一边走,一边丢,直到哪天,连自个都丢了,才算圆满了。
第二次听这些话,我仍没懂,我说我不想丢。
你认为丢了的,不一定真丢。就像阿冉,失去“四蹄雪”,但她得到了爱情和马骨琴,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失去什么。琴在,马儿就在。
琴,还用吗?
怎么不用,用。她肯定地抱抱胳膊。
我说六姨,咱回去吧。
她露出喜气,走,摘枣儿去。今年的老枣树争气哦,一嘟噜一挂,树枝都压断了。
还吃药吗?
不吃了,石角街没有顶用的药罐喽,不经烧,一烧就破。人家也不喝中药了,嫌麻烦。全是颗粒冲剂,一副药半碗水,一冲一调,三十秒速成。我呀,习惯了火炉子上熬药。喂上新煤,蓝色的火苗舔着砂锅底,不一会儿冒出软乎乎的白烟,看着就暖和。一个人熬个小半天也不着急。如今这三十秒的药啊,说实话,我不敢喝。小阮,甜水井没了,护城河也没了。听说,马骨琴都成了文化保护遗产了。
六姨,你看,蓝天也正消失呢。
那次谈话不久,六姨给何家欢换了新摩托。
何家欢载着六姨灌粉浆,路上,摩托黑亮的外壳化作了锋利的翅膀,斜斜插向天空。落地的一瞬,六姨看见何家欢的衣服皱巴巴铺在地上,像一道符。
这是后来六姨反复描述的画面。
我赶过去的时候,一根细薄的警戒线把六姨生硬地隔开,她堆地上一声不响。
周围站满了人。
咦哎,娘哎!这惨!
那是孩儿娘,多可怜。
咋不哭?
是哑巴。
哑巴也会哭。
我挤进人群,瞄了一眼: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拉链上衣,一条同样辨不出颜色的裤子,还有一双,红白相间的网球鞋。我在找,找……一声尖叫,被我活活闷死在胸口--我再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发不出任何声音,颤抖着,抱住了我的一声不吭,脸上涂满鼻涕和眼泪的六姨。
她移过目光,做梦似地说,家欢的头……
六姨。我更紧地抱着她,想把她裹进我的身体,可是我不够宽大我包不住她。
六姨委屈地对我说,小阮儿,三轮车,逆行,他把我挤到了路中间……卡车太快了,太快了,我都没来得及。来不及你知道吗阮儿……他们怎么可以……像碾西瓜一样啊?!
六姨突然提高的嗓门,如同裂竹,终于让围观者纷纷后退。我看清了六姨眼里的恐惧,也看清了围观者的恐惧。
六姨昏过去了。
六姨躺在床上,小腿到膝盖都打着石膏。我只好买来她不喜欢的中药颗粒,一碗一碗冲给她喝。调着褐色的药汤,我拿不准粉碎的蚯蚓能不能在汤汁里复活,在她身体里钻穴打洞,疏通寒凝血脉,驱散经年累月的寒气。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尖下颌、白帽大棉袄、疙瘩老枣树,六姨接着喝她从前的日子,只是手里多了乌杖,如烟花散尽,冰凉焦黑的空花筒。
她就这么从一个年轻的六六,喝到我和何家欢口中的六姨,最后变成了女儿的六婆婆。那些药织起来,能汇成一条河。
2009年石角街老屋平了,原地盖起一排排小洋楼,有人干脆买了电梯商品房,剩下为数不多几家老人守着巷子,陪六姨。其中就有二婶。二婶没有生育。我出嫁后,经常一家三口回娘家,看二婶也看六姨。空空的巷子照样长青苔,只是不再潮润,干燥的褐黄,远没了从前的生机。墙壁上排列整齐的青砖也扭曲了,如老人弯曲的指纹,印在那里迟迟不肯擦去。
过不久,墙也会塌的吧?该劝二婶搬家了。我想。
寒症让六姨的腿关节不断僵硬肿大,彻底变形,就像两根强力拆开后无法再复原的麻花,挪了这一步,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挪出去。而她总是心急的,脖子前冲,脑袋上挑着白帽,如同晒干的老丝瓜在吓唬小家雀。自从何家欢去了以后,六姨每天都穿着大棉袄站在院里敲瓢,倚着歪歪扭扭的老枣树,敲一下瓢唤一声,叨!家欢,回来喽!叨!何家欢,回来咯!苍哑的声音,如同生锈的锯齿,执拗地切割着石角街的黄昏和炊烟,切割着街坊们的神经。大家都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偏那一年石角街供了暖。六姨身上长了肉,两腮松松耷下来,一笑挤满褶子,就像抹了浆糊没抻平的贴纸。
大家都说,还是六婆婆经熬。
熬到又一年春,六姨照样拄着拐蹭街口,跟老太太们聊天,嘎嘎地笑,一坐大半天。这样的日子,不胖都不行。
枣树衍花的时候,口儿爸考上了研究生,我们带口儿一起去他的工作地。我应聘到一家名头很响的私立医院,做了外科医生。冰冷的器械和随时发生的死亡,让我变得力求语言准确,思维敏捷,不留存一丝一毫感性。我迅速成长为当地有名的“阮一刀”。
手术总免不了意外,死了一个人,我不哭;死了两个人,我还是不哭。
夫君说你变了,你不是石角街的秦阮儿了。
我说你娶的不是秦阮儿,是“阮一刀”。
二叔打电话问我,春节回来吗?
回不去,排了手术。
五一临近,二婶打电话,阮儿,五一放假不?
她爸单位组织旅游,我们报了名。我放慢语速,六姨,现在怎么样?
唉,一天不如一天。神神叨叨地半夜躺在床上唱戏,怪吓人的,说是跟着师傅讨了五年饭,本事不能废了。
讨饭?
那么,又是谁替她杜撰的青衣呢?如果我告诉她,现在有个叫互联网的东西,能让人一夜走红,她信吗?
最后一次见六姨,在敬老院。
夏天的午后,屋里光线很好,足以看清每一根皱纹和白发。她百炼成钢了,肥胖、衰老、浮肿,赤裸着上身,鼓着肚子躺床上,如同腐败发胀的水母。她胖得三个护工都搬不动,只好把床掏了窟窿,下边接着便桶,异味源源不断从那里散发出来。
六姨。我叫,挥手赶开吸在她脸上的一只苍蝇。
谁啊?她疲耷地应了一声。
是小阮,她来看你啦!二婶高声说,拉条被单给她盖上,瞧瞧身上光的,冷了一辈子,瘫了瘫了她倒不冷了。
哦,小阮,阮……坐,坐。急切的语调,说明她记得我。
我陪她说了会儿话,前言不搭后语。
她示意我打开老棉袄盖着的木箱,取出一套壮服。连二婶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备下了寿服,衣服袖口绣着五彩花纹,裤脚膝盖镶着蓝红绿棉织阑干,还有一方折成玉兰花瓣的头巾,一件墨绿小围裙。我把衣服一件一件摊开,想起那个要踩着高跷去结婚的女子,心里一疼。
这一疼,便割去老茧疼到骨子里。
箱子最下层躺着马骨琴。我把它托出来,细细打量。我们都老了,它还是老样子,害羞的小母马一点都没有长大。
琴,是师傅的,老棉袄……也是师傅的。小阮,把琴带走。
师傅是谁?
别问我。我不知道。她有些烦躁,我只知道,人人看不起的师傅,在艺术面前……比谁都高贵。
我坐下来摩挲着马骨琴,垫指、滑音,一个人的伴奏。时空隧道。
鸟鸣。泉水。朝霞。山道。
骑马的新娘。
不,不是马,是高跷。
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一波又一波红色的焰火,如潮翻涌。
吭!六姨咳了一声。
我放下琴,慌忙找纸,还没送到嘴边,噗!她已无比爽快地把痰射到了墙上,像吐出一枚坚硬的子弹。
我赫然发现,整整一面墙全是她的子弹,满墙明晃晃的子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