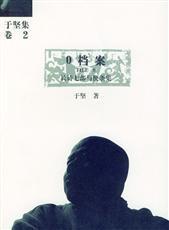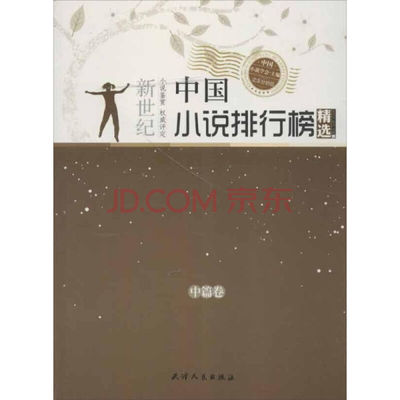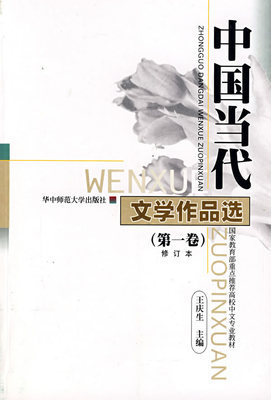和多少个并不算短的文学时期,在后人--如我们今天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仅仅是一笔带过,
甚至连一笔也没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
不同于以往文学的新阶段。“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几代人,从天真、童稚的幼年时
起,就一直浸泡在共和国文学的空气里,呼吸着这样的空气长大成人。我们对文学的最初感
觉,是从这里得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之际,记者约请了国内部分学者、评论家
对这一段文学的历史进行梳理和回顾,至少可以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些资料性的价值。
对中国当代文学50年的印象、看法或总体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义先生说:我们这代人(50岁左右)是和共和国一块
成长起来的,和共和国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学时我最喜欢数、理、化,成绩也很好,但
后来转过来搞文学,除了古典文学的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是建国10周年时,出版了许多好
的小说,于是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将我引进文学之门,
当然也包括俄苏文学,包括《牛虻》等的影响。我从当代小说里,认识了中国现代革命史、
近代革命史,以及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农民的斗争过程,包括从《红岩》中得到的对生命
价值的认识。50年代的这些阅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新时期文学非常繁荣,但因为我研究过小说史,我认为80年代并不是文学的高峰,可
以说它是“五四”以来最活跃的时期,是才子的时期,而不是出大家的时期。文学形成一个
高峰,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在80年代当代作家表现出才华,也显示出缺乏深刻和大气。
现在的问题更加复杂,有一些有分量的作品,也有精神探索性的作品,作品是丰富的,但在
怎样建立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这点上缺乏自主性。西方文学发展到今天有它自己内在的逻
辑,有西方文化的命脉,邯郸学步总是学不到位的,如何能激发我们民族自身的东西?在文
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今天,文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可想象的,但没有原创的灵感源泉也是不
行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先生说:我认为50年来最好的文学时代是80年代,最
不好的是“文革”时期,而“十七年”文学可以作为分析社会、文化思想的材料,因为文
学性较差。我理解的文学是自由精神和自由创造,以此为衡量,80年代以后的自由度越来
越大。自由写作的结果应该是多种多样,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初文学是最多样的,199
3年以后多样性减弱,这不是由于文学受到了政治干预,而是作家的创作和社会上一般的流
行思想太近,看起来很个人化,实质上是社会流行的思想和观念,这影响了相当多的作家的
创作,丰富性和多样性由此减弱。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原因又是如何?这都可以讨论、分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先生说:我刚刚编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对不少问题的
看法和以前相比发生了改变。通常流行的观点是:一部整个20世纪文学,30年代辉煌,80
年代繁华,而1949至1978年这一段文学比较单调。实际上,这些观点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
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公开发表的作品才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其实每个时
代的精神都是丰富的,50年代以来斗争的残酷,使很多语言被掩盖了,比如那些已经创作
出来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像沈从文1949年以来所写的大量札记,写他与那个时代的
隔离而产生的想法,内涵丰富,非常漂亮。还有另外一些老作家、胡风分子、右派、“文革”
后老、中、青几代人包括食指他们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果把这些人都放进文学史,那
是非常丰富而优秀的。至于那些能够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比如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受西方
文化影响较小,对中国民间文化感情很深,反映了农民的审美形态,如《林海雪原》之类小
说中“草莽英雄”的形象,赵树理小说中的“落后人物”、“中间人物”的形象,是作家站
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说话和服务的产物。我认为当代文学由三个纬度构成:公开发表的作
品;知识分子的隐形写作;民间话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说:“文革”前的诗歌比较单调,是一种单一的模式,
抒情式的颂歌,比较僵硬。“文革”结束后,一批诗人从流放地回到创作队伍中来,他们所
创作的诗被称为“归来的诗”,艾青、公刘、牛汉等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灾难,重新写作诗歌,
改变了过去颂歌的传统。同时,在知青中,酝酿着新诗潮、“朦胧诗”,他们写在“文革”后
期,反思“文革”历史,艺术上采取、借鉴西方诗歌,以意象为变革,一时间诗歌界、读者
不能适应,为此展开了大的论争。“朦胧诗”和新诗潮改变了中国当代新诗的格局,产生了
大变动,与以前不同之处在于回顾、反思“文革”历史,具有很大的批判性。思想的解放带
来了艺术的解放,“归来的诗”、“朦胧诗”带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繁华先生说:中国当代文学50年,80年代之
前同现实生活的关系过于密切,文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表意形式,这种状况和文学生产方
式、生产机制以及主流话语对文学性质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主流话语对文学性质的理解形
成了当代文学相对稳定的生产机制,这种机制形成了文学“一体化”的生产形式。当代文学
在80年代之前,作为社会文献的价值远远大于文学自身的价值。1985年前后,当代文学
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体化”走向“多样化”,当大家纷纷对
这种现象表现出欢欣时,我有所保留,在多样化、个人性写作已经可以诉诸实践时,文学越
来越丧失理想、浪漫、真诚、激情,我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在获得多样化和个人写作的同
时,我们也负出了相应的代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说:做文学史研究,一般把当代文学50年分为两个阶
段--“文革”前和“文革”后。如果放在整个20世纪来看,是“一体化”现象到“文革”
后“多元化”变革过程。以前的流行说法是,从“十七年”到“文革”这段时间问题较多,
文学逐渐走下坡路和衰退,新时期文学开始复苏,但现在我对这种看法有了调整,因为“十
七年文学”是“左翼文学”的延伸,对“左翼文学”不能轻易抹杀,要好好研究。
上海评论家蔡翔先生说:当代文学50年有不同阶段,经历比较坎坷。前30年由于各
种原因和束缚,一般说起来文学性较低,近20年来文学从“工具论”中走出,在创作手法、
表现高度等方面都留下了好作品。当代文学50年的成绩不少,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白话
文、现代汉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有必要对“十七年文学”重新研究,“十七年文学”
是“五四”文学和80年代文学之间的直接联系,不能省略掉。像赵树理、柳青作为优秀的
作家,凭着作家的直觉和思考,对当时流行的“左”的思想还是有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先生说:50年是一个时段,文学需要整体地
看,文学有自己的季节、风景,有自己的起伏。现在研究当代文学史将它分为繁荣期、消退
期、空白期、浩劫期、复兴期等,我不同意这样的分法,把一个完整时段按政治运动切割得
非常碎。文学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文学的起伏波动无非是文学作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灵
生活的一种曲折活动,有时表面看起来繁荣,其实是文学观念浮在表层的现象;有时看起来
是萧条、不景气时,也可能地火在运行、积累。应该用整体的观念看文学。
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评论家李庆西先生说:从全球化来看,20世纪后半叶以后已经
没有文学了。欧、美西方国家80年代经济高度发达,后现代、后时期没有文学。
到1949年为止,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战争构成的。文化是一种综合体,
战争文化心理从语言、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思和曾发表过一篇《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的
主要观点是: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
客观上的成绩是明显的。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
城市,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人们所能估计的深远得多。当带着满
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时的印痕。战争文化心理作
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文学观念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包括文学的批评领
域和创作领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军事词汇:战役、斗争、重大胜利、锋芒直指、
拔白旗....一部作品发表后获得成功叫“打响了”,作品有所创新叫“有突破”。这种文化心
理不但表现在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
当代文学中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里,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往往从战争的回忆中得到鼓励(当
时的作品中让复员军人来担任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公屡见不鲜)。随着60年代阶级斗争的
扩大化,即使和平建设的题材也充满了火药味和战争氛围,例如《艳阳天》,支部书记萧长
春(也是复员军人)仿佛是个运筹帷幄的统帅,整天想着调兵遣将,明争暗斗。这样的小说
读起来扣人心弦,因为作者把军事斗争的一套战术都用到了政治斗争上去,但作为对和平时
期生活现实的反映,却是一种严重弯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情绪支配着所有参与、支持或同
情革命的人们,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个个英雄事迹被写成了文学作品,以完美的
形象鼓舞人们奋不顾身地建设今天的生活,战争没有结束,战场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将永远地
延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西方人的则是对
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这种思潮影响到前苏联,就有了《一个人的遭遇》和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优秀作品。但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是这种情调,而是红旗插在城堡上
的欢呼,是英雄带着满身硝烟的微笑。这其中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二次大战加速动摇了
战前的乐观精神,从布满希望的天空突然坠落到灾难的深渊;在中国,战争则帮助完成了战
前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体现为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走向,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
孟繁华对此的看法是:陈思和这一发现是个重要的发现,将一种普遍性文化心理和创
作心理得到了揭示。我们不仅在文学上设立了两极对立、敌我对立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文
学作品中崇尚暴力的现象被普遍接受,这种现象长久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培养了读者的欣
赏趣味,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塑造来说其负面的东西远远大于正面的东西。因此,对
战争文化心理的揭示,从一个方面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
洪子诚认为:强调“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斗争,这和冷战有关,把世界看成是敌我
对立的,矛盾要通过斗争来转化。对文学、对文学遗产都是这样的“两分法”,中间部分是
动摇的,把中间地带隐藏着的复杂部分都忽略了,把汉语里委婉的、细微的情致都抹杀了,
喜欢使用极端的、非常激烈的语言,这种影响深入血肉,非常深远。文学在这样的长期浸染
中,很难摆脱这种语境,老一代作家好一些,年轻作家很难避免,而且许多作家在这一点上
都不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国文学专家、研究员童道明先生说:战争文化心理
在中国和俄国作品中的表现如此不同,抗战时,我们是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代表作是“夜莺啊,夜莺啊,你不要唱,让战士们再睡会儿吧....”;“一
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西蒙诺夫的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但是要真正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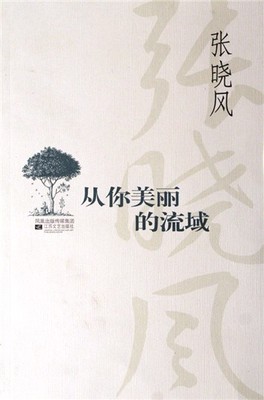
着....”。他们的战争歌曲在我们的青年人谈恋爱时也可以唱,显示了俄罗斯人道主义的传
统,抒情的、对人性温暖那一面的渴望。俄国有句著名的话是:“大炮开口,缪司闭口”。战
争是非常态的,俄罗斯作家努力在残酷和血腥中寻找人性的光华,越是在战争中血腥的状态
下越是要挖掘温情。
似乎常常听到人们谈起当代作家的素质问题。受访的学者、评论家感到中国作家身上最
缺少的是什么?最富有的又是什么?他们个人比较欣赏的作家有哪些?
陈骏涛说:当代作家特别勤奋,但缺少大家风范。成为大家的条件有两个,原创性;
作品内涵丰富。现在不少作家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技巧,然而思想含量不够,厚重的作品少。
我认为80年代小说的高峰是陈忠实的《白鹿原》,90年代小说的高峰是阿来的《尘埃落定》。
至于谈到喜爱的作家,有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莫言、舒婷、铁凝等。王安忆
在不断超越自己,一个阶段不同于另一个阶段。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先生说:当代作家最富有的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苦难;缺
少的是对这种苦难非常有历史性的思考。我喜爱的作家有王蒙、张贤亮、汪曾祺、韩少功、
莫言、王安忆、余华、史铁生等。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美学保留得比较充分,理解得比较透彻,
而其余作家对苦难思考得比较多。
陈思和说:当代作家富有的是,像丰子恺--在“文革”那样的时代还保存着完整的童
心,他是为艺术而存在的;像曾卓、绿原、牛汉在逆境中还有不息的抗争精神,一直潜在地
写作,没有这样的诗歌,当代文学史就不是完整的。还有王安忆,90年代以后的创作都很
好,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
张炜的《九月寓言》,在整个20世纪里都是最优秀的作品。
王晓明说:中国作家的优越之处在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社会生活长期动荡,社会现
实对人的刺激是非常丰富的、不平淡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对作家的创作是有利的。作家是社
会的人,也一定会受影响,精神弱、想象力不强、伦理感差,对利益之外的关怀和热忱、敏
感、震撼力在不断削减,创作总是处于自我克服、自我搏斗的状态中,怎么能出大作品?王
安忆、张承志、史铁生、余华、李锐等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作家不一定要充当社会、道德的
良心,只要他忠于自己的内心,真实地感受生活、想象世界,把这一切充分表达出来就够了。
李庆西说:中国作家缺乏的是勇气和耐心。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10载,现在的作
家能披阅10个月就不错了。同时也缺乏勇气,其实中国当代作家并不缺乏创作资源,他们
富有的是民族的苦难和经历,与此相比,美国作家精神资源是缺乏的,在文化上又以老大自
居,心态是很封闭的,也缺少中国人的忧患和沉痛,但是美国作家很有想象力,东西也很精
致,不过美国70年代以后已没有好的文学了。中国人的内心思维还是比较活跃的,只是没
有利用好。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莫言等都是我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有生活底蕴的,他
们都是80年代的风云作家,90年代以后没有喜欢的,因为不能进入他们的作品。至于王蒙,
我一直遗憾他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没有人尽其才,从理论上说,王蒙那一代作家应该说不
逊于韩少功那一代作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谢冕说:当代诗人富有开放的心态,有比较广泛的借鉴,对外国诗歌很熟悉,技巧成
熟。但他们也有很多欠缺,80年代后期个人化写作的潮流,应该说使诗歌回到了诗歌自身,
然而个人化走到了极端,就缺乏对周围环境、对社会、民族的关注,只会抚摸自己,与社会
产生了隔膜,大众对诗歌失望,也缺乏关注。诗歌应该关心更大的问题、公众关心的问题,
应该与社会有联系。有些东西--传达美好的情感永远也不会过时,千百年前的诗歌与我们有
亲近感,当代诗人的作品反而离我们遥远。我希望借诸报纸表达出我的这种忧虑。
在新时期文学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一度非常密切和互相关注。不过,目前似乎彼此都
在抱怨,为什么?
李庆西认为:80年代时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比较健康和正常,90年代以后,有部分评
论家对创作感到失望,退出批评界。而现在的批评更接近传媒和炒作,也缺乏权威的文学评
论刊物。
陈骏涛认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从来就不合谐,作家贬低批评家的有很多。1949年
之后,批评家一度居高临下,充当枪手,而80年代是最好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批评家
和作家有了疏离。其实,批评和创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一个是理论思维,一个是形象
思维,各说各话,宏观上进行平衡,具体操作上互相不能左右。
杨匡汉认为: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为了文学而存在的诤友,应该建立起一种正常的互相
了解的关系。作家和批评家各有各的事情,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得
到批评家的认可和宣扬,事实上有时达不到,应该允许批评家有自己的理念和对作品的看法。
批评家一入批评之门,就要和作家保持距离,而现在特立独行的批评家比较少。
孟繁华认为:今天指责批评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批评是什么,他们以
为解读作家、作品就是文学批评,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而90年代究竟有多少作品值得批
评家注意同样是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另一方面,批评家也要通过批评的方式
表达他对文学、社会乃至人生的普遍的看法,不是说离开了当下的文学作品,批评家就不能
存在,对文学史的写作,同样是批评家的工作内容之一。不过看起来90年代的作家、批评
家的关系肯定出现了问题,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共识的破裂。在两个人的对话都成为困难的时
候,作家和批评家成为现在的样子是不足以大惊小怪的。
蔡翔认为:80年代是作家和批评家的蜜月期,当时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在年龄、艺术
观点、对生活的看法上比较默契,互相能对话和启发,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批评家本身也有
锐气,批评文章也好看,是美文,也有生活积累。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被学院化了,自
由职业批评家少了,学院批评派多了,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文章数量也不多,缺乏
足够的阅读。和80年代相比,那时作家、作品论特别多,90年代的批评有它的深度,但阅
读面不够,批评家本身都是教师,有教课、科研任务,对作品缺乏第一反应,对生活的理解
能力也是个问题。没有第一手阅读,又没有全面的阅读热情,人云亦云,作家、作品论少,
宏观论多,宏观论的基础在哪里?这是一个学风问题,缺乏大量的期刊阅读,缺乏个案的分
析,文章缺乏个性,美文又太少,这都是批评界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批评有两面:一面是传
媒的炒作,另一面是学院式的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一直都在阅读外国的经典著作,培养了较高的眼光和欣赏趣
味。无论他们是否自觉,中国当代文学50年在和他们所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相比较时自然
会凸现某些特点。
童道明说: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前“十七年”,苏 联文学界有
什么倾向和大的作品都能反映到中国文学界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和我们
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主张差不多,除了他们50年代兴起的“人道主
义”思潮我们没有接受。在60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之后,苏联文学依然是引起中国作家最多
关注的文学,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前苏联的社会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中国作家接近俄苏作
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我从中国戏剧了解的情况而言,前苏联50、60、70年代最重要的
剧作家对我们的中、青年剧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万比洛夫,是中国新时期
最早出版的一个外国戏剧集,中国的剧作家几乎都读过他的作品。前“十七年”中,戏剧文
学不是特别景气,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是那个时期戏剧最重要的成果。“文革”10
年是个空白。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新时期拓宽了戏剧家的戏剧
观念,反对“无冲突论”,反对庸俗社会学,提高戏剧作品的哲理品格。新时期是个了不起
的时期,出现了完全新型的作品,像《绝对信号》和《狗儿爷涅》等。90年代戏剧创作
的突破,是在现实主义的深化之下,像《地质师》、《虎踞钟山》和《厄尔诺报告》等。不过,
这时候戏剧的活跃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总之,前“十七年”受苏联戏剧“无冲突论”的
影响太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国文学专家、研究员郭宏安先生说:对中国当代文
学作品看得少,评论性文章看得多些,对全部情况并不了解,也不一定客观。我觉得一个作
家不应该过于关心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是应该关心内心世界和对外部世界的感触。从二
战以来,法国“左派”一直占主导地位,作家们并不关心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无论支持或
反对现存政策都有自己的标准,不求闻达。而中国作家对自己的身家性命关心得太多,也许
中国作家太聪明了,另外,在创作中,争文坛霸主的心理似乎很严重,例如诗歌界。在法国,
写诗的人很多,也不求发表,读诗的人少,写诗只给朋友看看,都是业余诗人,很难想象职
业诗人是什么样,这对诗歌的发展很有好处。小说有两种,一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直面人
生,群众喜欢;另一种是探索形式的。现在国内对后者的评论文章很少,所谓新派批评在国
外早已不新了,而在国内却很不发达,这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法国的批评家也有两种,一种
是实际批评家,主要在报刊发表,一周一篇,要有大量的阅读;另一种是学院派批评,就是
学术著作,只是同行看看,作家和读者也很少看。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中国作家地域性不
强,法国作家地域性强,不求在首都如何,不耻于承认自己是个农民,对自己的家乡感情很
深,愿意以此为创作基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专家、副研究员陆建德先生说:我不是中国
文学专家,但平常比较注意看一些作家的作品,由于自己本身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常会有一
种比较的眼光。中国当代文学前20年所受的各种--比如政治运动--的影响就不用说了。美
国诗人弗洛斯特将文学分成两类,悲哀的文学和抱怨的文学。前一类是关于人类永久的生存
状况,后一类带有某时某地的文学痕迹,也许真切、动人,但和前者相比较,不是伟大的文
学。我们的文学后者相对多些。这段时期,国内正在纪念歌德,我不免想到歌德的《浮士德》,
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歌德作为一个西方作家,指出了人生不能没有追求,但追求本身也会成
为堕落。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很多西方作家都写过,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难处:对人生
的追求和对追求本身的怀疑,这种两难处境的揭示成为西方一些作家创作的源泉。在我看来,
中国作家只有歌德所描述的前半部分,但常落入后半部分的结果,这不是简单的人性颂歌。
当然,中国作家有很多优势,比如生活底子丰厚,但肠胃消化不好的话,吃进去太多,
对创作毫无用处。经验丰富本身,不一定是长处。中国作家对于人本身容易堕落的东西注意
得不够,常常陷于批判和谴责什么之中。近十几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可喜的多样性,这多少
得益于对叙述体裁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成熟的标志,但过强又容易变成一种病态,与此
同时,不能像所谓“后现代主义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