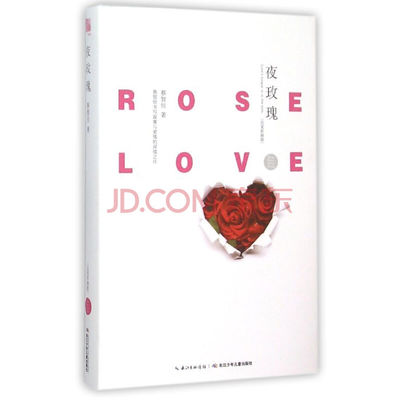为“支那”一词正名,可说是当下极为敏感的一个话题。按照近年来流行说法,这是近现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于是乎,新浪网曾因使用“sina”作为域名而遭到穷追猛打的声讨与拷问,重庆某即将开业的火锅店因取名“支那”,其老板被迫下跪含泪致歉,香港作家张继春夫妇的小说《支那人高阳泰》重新出版,也被迫更名为《千岛情缘》……网络舆论对于此词的深恶痛绝而大张挞伐。偶有不同凡响,大多“口将言而嗫嚅”,亦不免虎头蛇尾。
然而,传播媒介与网络舆论则大相径庭:央视《百家讲坛》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曾就《玄奘西游记》而口口声声大谈特谈“支那”高僧;随着近现代文化史的日趋深入,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一书业已重新出版;现代佛教史的研讨中,“支那内学院”的学术论著方兴未艾……同为“支那”一词,何以产生出双重标准:既然专家学者称得,何以平民百姓称不得?既然日本人称不得,何以其他国家能称得?既然佛教典籍称得,何以网络称不得?这不免让人费解。
究其所以然,一则缘于近十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高涨;二则基于日本右翼修改教科书及其首脑参拜靖国神社,国民的思想感情受到极大地伤害;三则主要在于网上泛滥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支那人留学日本史》混淆是非的诱导所致;四则出于反映抗战题材的影视剧误导所致:一些既不懂史学又不懂日语的二三流作家,只需采用两个半日语——“咪西”是“吃饭”,“八格牙路”是“混蛋”,“支那人”是蔑称,就可敷衍塞责,包写抗战文学作品。由于日本学者专著、网络流言与影视作品的误导,“支那”即“对中国人的侮辱”,犹如盗版畅销一样,从此风靡网络。
其实并非如此,“支那”一词从古迄今并无贬义。
一、古代的尊称与普世性
追根溯源,“支那”一词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铁血帝国。居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古印度人,便根据秦国的“秦”这一音义,在梵语中译为“Cina”,即“统一、强大”之意。另据佛教《华严经音义》:“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原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这一国名则具有“文明、睿智”之涵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都以“Cina”来指称中国。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大军占领北印度,获知喜马拉雅山北麓存在着一个名为Cina的强大帝国,便形成希腊语Κ?nα音译。此后,希腊语Κ?nα传至罗马,拉丁语音译成Sina,,再至英语中的“China”,法文中的Chine。整个印欧语系中,除了斯拉夫语族的俄语Kитай来自“契丹”音译,其他各国无一不是从古印度梵语Cina演化而来。
若论梵文Cina音译成汉字“支那”,则为中国人自己翻译中的独创。佛教传入华夏,古代译经家在翻译时将梵文“Cina”音译成汉字,常译作“支那”、“至那”、“脂那”、“震旦”等。据大唐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所载,他在回答印度戒日王何为“大唐国”时,答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而中国人自称“支那”第一人,当首推大唐天子玄宗李隆基。他在其《题梵书》一诗中咏道:“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仅就十九世纪前的日本而言,他们一般称中国为“大汉”、“大唐”。“支那”一词的出现,缘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偶而为之。此词最早出现,在日本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1862年6月,日本志士高杉晋作曾被派往中国视察,所作汉诗直抒胸臆:“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文中“支那”,自然充满钦敬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学习兰学时,才采用了“China”一词的意译,以此替代了对中国的原有各种称呼。在日语中,该词汉字写法与中文一致:支那,假名为“シナ”。罗马字拼写法一般有两种:“shina”(平文式罗马字)或“sina”(训令式罗马字)。
由此可见,“支那”一词,音译始于古印度梵语,自译源于佛教经典,自称见于大唐天子,他称出于近代日本。对于中国而言,不过是出口转内销;对于日本国而论,无非与西方China链接而已。
二、近代的通称与革命性
从古代至近现代,“支那”这一外国对中国的尊称,也因国力的由强转弱,由盛转衰,逐渐嬗变为对中国的通称。
鸦片战争前,中文资料较早出现“支那”的,当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拉开后,此词仍时有所见:1884年,爱国志士姚文栋就在其《琉球说略》一文中,使用过“支那”一词;1890年3至6月,西洋传教士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是年,美国传教士阿瑟· 史密斯出版了《支那人的气质》一书……
1894年甲午海战,满清帝国竟然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痛定思痛的维新之士,大力倡导师夷之长以救亡图存。于是,清末派遣留学生,赴日参观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藉,一时竟蔚然成风。当时的留学生与国人,显然受到日语的直接影响,皆以“支那”作为对祖国的代称,从而成为一种时尚迅速流行。
早在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梁启超当年就在《时务报》中经常使用“支那”一词。1899年,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时,明确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此外,他还使用过“支那少年”这一笔名,并以“支那之怪杰”题签在其所著《李鸿章》封面上。
1901年4月,康有为先生之次女康同璧,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下:“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20世纪初,一大批革命家流亡日本后所采取的革命行动,一是剪去被称为“猪尾巴”这象征耻辱与被奴役的辫子,以此表明同满清王朝彻底决裂的决心;二是直接借用日本称谓而自称“支那人”。还有一些留日学生,干脆以“支那”标明出身国,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此词因而具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不久即风行国内。
作为国父的孙中山,1899年冬流亡日本时,绘制了《支那现势地图》;1903年在其《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加强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的宣传。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年代),并提出“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
1903年2月,中国神父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了震旦学院,后更名为复旦大学。
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华兴会机关期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易名《民报》。
是年,严复在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 ……
这一时期,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盛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都频频出现。出版业中,“上海支那出版社”名噪一时。书名更是屡见不鲜,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
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无数以民主共和为已任的革命家无不以“支那”自称。而崛起于东亚的日本帝国,除正式公文指称清国之外,朝野上下不屑称以满清王朝为国号的“大清”。就当时而言,假设日本人一口一个“大清国”、 “大清人” ,才会有辱中国民主共和大业。
三、现代的惯称与变奏性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均以王朝命名,国民固守着“王权即国家”的传统观念,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概念。直到1907年7月5日,章太炎在《民报》所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中,才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推翻满清后的新国号。
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一国号并未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因为当时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其统辖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直到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不忿称呼具有“居四夷之中”寓意的“中华”,导致一段时间内没有正式认同北洋政府。当时开明达观的新国民,亦因“中国”二字具有“盲目自大之嫌”,而代之出自西方“China”的日文汉字“支那”。
1912年初,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敦促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支那共和国”。
同年10月,胡适面对国内危亡局势,发表了著名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
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
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时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信中自称“支那”之外,“对支政策”、“支那革命”、“支那国民”、“支那人”语词,频频见用,比比皆是。
面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出于民族激愤情绪,在抵制日货时才对“支那共和国”的指称产生了逆反,一时进行了坚决反对。其思想动机,仅仅来自激烈的爱国情怀,并非因“支那”含有“歧视、侮辱”国人之意。
1915年9月15日,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文章称:“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
“五四”时期,国人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者,依旧为某些留日学生。他们往往出于激愤,不免恨乌及屋,认为这一称谓包含着民族歧视意味。有些则属牵强附会,人们能在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字狱”中见其身影,或在半个世纪后的“文革”中寻其幽灵。可此时此后国内之名家,他们依然故我。
1919年8月,鲁迅在翻译日本“反战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期间,周作人曾致函武者小路告知此事,其回信则由周作人译为《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并作为鲁迅这篇译作卷首文章。
是年岁末,蔡元培阅读了周作人翻译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还专门为其写作了一则跋语。
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政府,国土经北伐后已趋统一。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国民仍然称之“支那”,而中国文化精英可谓涛声依旧。
1922年7月,近代著名佛学居士欧阳渐在南京 正式创立中国第一所佛教学院和研究机构——支那内学院,历经历30年风雨,直至1952年才停办。
1923年10月24日,孙中山先生致函日本友人犬养毅,他在这封长信中宣称:“夫支那之革命,为欧洲列强所最忌者”,“是故支那之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故列强政府之反对支那革命无所不至者此也”。
1925年,留美归国的闻一多在诗作《我是中国人》中咏叹道:“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1929年10月,上海《申报》等报刊谣传毛泽东已死,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闻讯后写诗致悼:“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1930年,民国政府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鉴于此,日本政府从1930年底开始,其公文即停止称中国为“支那”。当时之所以要求日本国今后称呼中国不得“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仅仅因此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此举无非是出于要求日本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现政权已代表主权国家之形象的认同而已,并未涉及“支那”含有侮辱词义的内容。
然而,三十年代后的中日两国名流,则因文化及语言惯性使然,对此称谓并未因之而完全中止。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前,还在新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特别指出:“我至今还希望有人译出阿瑟·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
1937年,藤野先生在鲁迅逝世半年之后,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忆周树人君》,文中饱含深情叙述道,“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
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并未对“支那”一词予以排斥,只不过偶尔用之,可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人大三楼小礼堂参加文艺晚会时,在前排见到带着花镜专注于节目单的康同璧,走过去翘起大拇指,引用康老当年诗作名句:“我是支那第一人”。
地理专有名词“印度支那”(indochina、indochine),指介于印度与中国两国之间的半岛,即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支那”即中国,我国六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时期,新闻媒体一直采用这一专有名称进行的报道。
理性地分析人们对“支那”的误解,客观上出自日本国民对落后而被战败之国度的歧视及国民的轻蔑,主观上则来自贫穷落后的国度留学生的自卑心理使然。这与“支那”一词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最能代表这一观点的,恐怕是著名作家郁达夫于l936年发表在《宇宙风》中的自传体文章《雪夜》。
人们不难设想:置身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即使不称“支那”而称华人,难道就心安理得?旧上海租界公园门前被称之“与狗不准入内”的华人,就找不到被歧视的感觉吗?
四、当代的误称与自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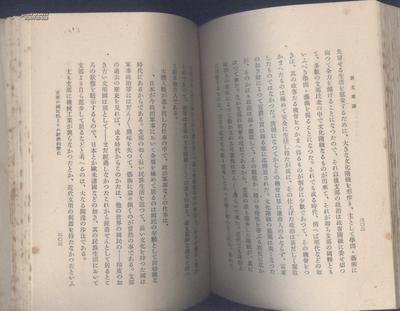
深层解读这一名词,从古代的尊称至近代的泛称,从现代的惯称至当代的误称,则可反映出一个国家其国力由强盛转向衰弱,其国民心态由自信转为自卑,其社会意识形态由凝重转到轻狂这一运行轨迹。本文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不惜笔墨地论证,无非还原其历史真实——“支那”自古迄今并非蔑称,以期激浊扬清,以正视听。
网络近年更有甚者,对自称“支那”的留日反清志士和民主革命先驱极尽辱骂之能事,或怀疑蹈海而死的陈天华之爱国情怀,或质疑国父孙中山之“卖国”动机……甚至于攻击“他们的自辱行为难道不算卑劣么?他们的自贱会得到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人的真心尊重么?”迫于这种轻狂诋毁的压力,产生了轻率的趋同心理,导致了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故事——
曾被鲁迅先生推介的美国阿瑟·史密斯所写的《支那人的性格》一书,近年重新出版时,均将原书名篡改成《中国人的性情》,不免令人齿寒心冷;
1982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了香港著名夫妻作家陈金兰、张继春的长篇小说《支那人高明泰》。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部作品近年不管是再版还是评论,竟然更名为《千岛情缘》。
深究国人误解的出处,原来均来自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支那人留学日本史》。在他的笔下,“支那”竟然同“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联系到一起:“当时的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之类的嘲弄”。“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支那这个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了”。
事实胜于雄辩。甲午战争后,清国留学生头后皆留着细长的发辫,日本小孩子见状戏谑地称之为‘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这明明是针对丑陋的蓄辫形象,可他不仅对此避而不谈,反而将“支那”与“猪尾巴”或“豚尾奴”这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别有用心地混为一谈。此外,明明甲午战争后所发生的事情,却硬把时间提前到距此达30年前的明治时代。于是,“支那即对中国人的蔑称”,这一荒唐的逻辑就这样炮制出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程兆奇先生认为:“在战前日本,称呼今天被我们称为‘中国人’为‘支那人’,与称呼德意志人为‘德意志人’是一样的,这样的词语本身,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朱文通教授也明确指出:“‘支那’一词传入中国和佛教在唐代的兴盛有关……‘支那’原意是褒义词,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蔑称有天渊之别。”
拨开历史迷雾,如果继续拾日本学者牙慧而置历史于不顾,继续置专家学者的观点于不顾,非得一口咬定“支那”是蔑称,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道古今自称“支那”的中华英杰志士,千百年来竟对此有辱国格的蔑称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乐于自取其辱吗?那无异于说,中华民族是一群弱智并快乐着的阿Q!
人们不禁要问:从甲午战争到抗战时期,国人一直将日本国旗蔑称为“膏药旗”,难道仅因中国人的蔑视,日本就摈弃自己的国旗了吗?二战时,纳粹党徒曾疯狂杀戮犹太人,并将其蓝色六角的“大卫王之星”看作卑劣民族的标识,而倍加歧视与亵渎。但以色列复国后不仅未因纳粹党徒的蔑视而自行否定,反而将其作为神圣的国旗图案。
孔子告诫人们:“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国家无论大小,真正崛起时就不会在意别国对其指称是尊称还是蔑称;国民不管贫富,真正自信后就不会计较别人对其称呼是是仰视还是藐视。只有自卑的人永远以为天下人时时在鄙视自己,心虚的人时刻警惕他人处处蔑视自己。鲁迅先生当年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