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苏北人罗望子中篇新作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童年的诗篇来自何方》,回忆我第一次“远行”的经历,《我们这些苏北人》可以说是我童年到青年的再现。《墙》写的是我的兄长间的纠葛,《苏北人》这部半自传体小说,则写的是我的父辈兄弟之间的纠葛,有爱无恨,有情无仇。
有关我的家,以及我叔叔的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甚至可以说有些淡而无味。但一个人的根常常与他的目标紧密相连,因而长久以来,不管我如何折腾,如何成败,挥不去的总是我的出生地,我的那些亲人们。
1
我只有一个叔叔,但我们从来都不管他叫叔叔,也从不管他叫二叔,正如我们不管父亲叫老爹,更不叫作爸爸一样。我们喊父亲一律叫“摆摆”,喊叔叔一律叫“牙牙”。叫摆摆没啥稀奇,我们这里的人都这么土气地喊,叫牙牙就怪了。一是虽然我们这里都管叔叔叫牙牙,俩字儿的读音却不一样,标准发音应该是“芽雅”,而我们喊叔叔的时候,两个字的发音都是“芽”。二是我们喊小姑的时候,也这么喊,也喊芽芽,而不是喊“亮亮”。这么着喊小姑,是因为父亲最严,小姑最亲,小姑也最疼我们。换句话说,喊叔叔“牙牙”,也就等同于“亮亮”了。
那么,我们和叔叔是不是也很亲呢。我看不见得,更不能和我们与小姑的关系相比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和叔叔家的关系,也就是父亲和他弟弟的关系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好到父亲年过半百才和叔叔分了家,坏的时候,坏得月黑风高拿铁锹动斧头,总的来说,坏的时候居多,至少打我懂事时起,两家基本不和,也不怎么往来,年酒几乎都不请了。再往前推,那时我还小,但我仍能感觉到,分家前已经有不少隔阂了。要不然,为啥割家割了几十年,却在奶奶生前就散伙了呢。奶奶是个瞎子,是瞎子就爱唠叨。奶奶最后的那几年住在叔叔家,却一直唠叨着叔叔的不是,逢人就夸我父亲的好。
我这个人打小就比较一根筋,就这个称呼我曾多次请教过父亲,也请教过叔叔。父亲爱拿背脊对着我,叔叔总是笑笑,绝对不是那种高兴的笑,又不是苦笑,却透出一丝淡淡的无奈。
我们还发现,我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喊我叔叔,从来不叫摆摆,却叫阿爸。注意:不是阿爸(坝),而是阿爸(拔)。这绝对又是一大发现,特大发现,但这个发现没有任何意义,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同,庄上的人都发现了。大概全庄乃至全公社,也只有我叔叔搞这个特殊化了。我们都叫摆摆,他却让孩子们叫他阿爸,真是邪门了。照理说我们庄上也有外乡人,嫁到庄上的外地媳妇也不少,人家都随俗了,可叔叔一家子倒好,硬在找别扭似的,要显出高人一等。我们不解,还有些愤愤的不平。
就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父亲和叔叔。叔叔还是笑,却笑得极爽朗,极豪迈。父亲呢,这一次答得倒是爽快:人家在上海滩混过的呗!
2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也从没听叔叔说道过。父亲倒是年年去上海的,一年要去三两趟。每次回来,庄上就像过节一样。父亲不是给这家带回了面盆,就是给那家带回了缝纫机。那时候,给女儿的嫁妆里,如果有台“洋机”,既能说明家底足,也能说明时尚新潮,风光得不得了了。最重要的还是钢丝车,当然都是组装的。一切都要凭票供应,自行车更是紧俏物品,想一想吧,我父亲竟然能够气定神闲的弄到手,而且是到上海去弄,就像能飞上天拔雁毛一样,庄上的人当然要刮目相看了。只有一次,他啥也没带,母亲却和他闹翻了。闹翻了就是那趟父亲打上海回来,母亲不像以往那样迎接,也没有给他做饭弄菜。
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了。
母亲这个样子,父亲居然没有动怒,反而掏出五块钱给我大姐,让她去买些烧腊回来。大姐买回来后,父亲又亲自切块,装盘,端上桌来。然后朝我们呶呶嘴,我和二姐一齐跳上了桌,又给大哥一巴掌打了下来。原来父亲是要我们去房里,请母亲来吃。我不得不佩服大哥,他对父亲的理解,比我们所有的人,甚至比我母亲还透彻。我们一个一个的进去,一个一个的出来,如同小蝌蚪找妈妈,找是找到了,可妈妈就是不想睬我们。所有的法子都用过了,哭的,笑的,跪的,甚至胳肢母亲的法子也不灵了。
父亲的黑脸白了,但也只是一小会儿。他放下那把铜质水烟袋,严肃地进到房里,砰的就给推了出来。父亲朝我们讪讪一笑,笑得白里透黑。桌上,烧腊肉香味弥漫,熏得我们直流口水。母亲不来,我们就吃不成。其实母亲从来不吃,每回母亲来不及伸筷,就让我们一扫而光了。我没想到的是,二哥比我还急,二哥说,摆摆,我们吃吧,妈不来我们还----二哥话没完就挨了一脚,这回是大姐,大姐从来不打人的,打了也不疼,这回却把我二哥整到桌子底下。父亲看了大姐一眼,大姐却不瞅他。父亲又进了房,还关上了房门。不久,房里头便乒乒乓乓的响起来,母亲压抑着在哭,父亲低声下气的在求。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们不敢动,我们看着大姐,怪的是大姐也捂着嘴,捂着脸,泪从她的指缝里露珠一样爬出来。二哥怯怯地跑到大姐身边,伸出脏乎乎的手指去拨那些闪光耀眼的泪珠。他以为是他惹气了大姐呢。大姐一把抱过我二哥,搂到怀里,哇的哭出声来,比房里头哭得响多了。
那时候大概我们所有的人都恨死了二哥,嫉妒死了二哥。我们多想让大姐抱一抱搂一搂呵,大姐是我们心目中的仙女。私下里,大哥早就对我们说过,将来他要找老婆,就找大姐这个样子的,而不是二姐那个样子的。惹得二姐连连追问,那我咋的了,我咋的了。
过后,我们才晓得,那次父亲去上海,不是没带东西。带是带了,就是没带家来。父亲其实提前一天就回了,只不过住在庄外,东西也送给了庄外的一个女人。能送给女人的东西,不外乎穿戴上面的了。消息自然是庄上的人传给母亲的,父亲也没想到会传得这么快,快得想补救也来不及了。其实就是他能补救也没用,难道他还能立马再去一趟上海么。我们倒是有些不相信,但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证明他心虚,他承认了消息可靠。这一点上,父亲倒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呢。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做错了事,向来都是能赖就赖的。父亲还保证,再也不找那女人了。情况属实,我们有些恨父亲,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工夫。我们感到痛快的是母亲解了气。向来都是父亲对母亲动手的,这一回,母亲出手如电,一下子就把父亲拿下了,真是百年不遇呵。
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经常碰到那个女人。也许是以前没在意吧,现在,那个女人老是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我们还晓得她有个好听的名字,阿霞。瞧见我们,阿霞有时还会停下来,笑眯眯的。她是那么高挑,苗条,白白净净的,一点不像乡下女人,更不像那种干粗活的农妇。她总是臂挽一只竹篮,篮子上罩一块花布。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花布下面到底罩着啥玩意儿呢!要不是大姐指给我们看,说她就是父亲送礼物的那一个,打死我也不信呵。
看见她,晓得她与我父亲的关系了,我们竟然一点都恨不起来。她对我们嫣然一笑,反倒是我们的脸红如鸡冠了。我们撒腿就跑,阿霞的笑声和香气便追赶过来。远远的,我们停下来,便觉得阿霞还在向我们招手呢,风摆杨柳一般。说实话,我们不仅恨不起来,还有点替父亲惋惜。父亲说到做到,让我们敬佩,也让我们失去了和这个女人接近的机会。真希望她是我们的姑妈或姨妈当中的一个呀。她要是能到我们家里做客----哪怕是坐一坐也好呀。她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像我们的大姐,但又比大姐成熟,那种感觉自然是说不上来的。可父亲说放手就放手了,以后,再也没听到父亲在这方面的传闻。母亲照旧任劳任怨,父亲照旧甩膀子,吆三喝四的,要不就是去上海,仿佛啥都没有发生过。
父亲如此轰轰烈烈,受人敬重,也不过是每年去一去,再怎么去也永远是上海的过客。可叔叔在上海呆了好些年,却悄无声息的,要不是父亲提拨,我们哪里想得到呀。这是真的吗,瞅空儿,我还是问了问叔叔。叔叔先是不理茬,后来见我缠着他,估计不答理我一下,我肯定不会走,便说:当然是真的了,你们不信我,还能不信你摆摆的话么。我立即感到不自在,我怎么能这么问叔叔呢。其实我没别的意思,但由叔叔亲口说出,心里才落个踏实。可这样一问,就好像我怀疑起叔叔的身份,叔叔当然不开心了。
讨了个没趣,我只得赶紧走开。叔叔又喊住了我,还把我抱坐到他的腿上。叔叔很胖,胖得像个和尚,身上还有股子馊味儿。我已经够脏够臭的了,用妈和大姐的话说,我是天下最臭的孩子,可没想到叔叔比我还熏人。他粗重的鼻息如同大象,几乎把我掀翻下来。不过,他的大腿圆滚滚的,坐在上面又舒服又柔软,很养屁股。看在他给了我一块宝塔糖的份上,看在他是上海客的份上,我挪了挪身子,躲过他的鼻孔,依到他的膀弯里。
叔叔说,他不仅在上海滩上混过,还在上海的小弄堂结了婚,生了孩子呢。养了伢,那你养的伢呢。叔叔呵呵一笑,呆子,就是你的堂哥堂姐呵。那小弟呢,小弟是不是在上海生的。叔叔皱皱眉,想了想说,也是也不是吧。我摇摇头。听不明白的事我就摇摇头。叔叔进一步说,小弟是你妈儿在上海怀上的,生是生在江北的。江北?我们这儿不是江北么,苏北人在上海就是江北人。那你在上海怎么混的呢。混生活呗。混啥子生活呀。叔叔瞅了瞅周围,然后压低嗓子说,我拉车的干活。我摇摇头。拉车,拉黄包车,你不懂么。我晓得的呀,你是人力车夫?我坐直身子,连说带比划的,忽然有些对叔叔肃然起敬了。是呀。就是《战上海》里的那种车夫?是呀。那时候你在上海么。在呀。那个人就是你吗。当然不是了,叔叔笑了,露出嘴里那两颗暗绿色的金牙。不过叔叔只承认是铜牙,我们也宁愿相信那不是金子。
叔叔又说,只是看上去,那小子有些面熟,咦,《战上海》你看了几遍呀。五遍。尽管我多说了一遍,还是没压过叔叔,我看了八遍呢,叔叔骄傲地瞅着我。那你去找他呀。到哪里找去呀,叔叔叹了口气说,人都散了,散就散了。都散了,都像你一样离开上海了吗。大概是吧,叔叔扬起脑瓜,好像麦秸垛和高高的树梢后面,就是外滩的码头。那牙牙,你干嘛回来,不呆在上海呀,上海不好玩吗。好玩是好玩,可哪是我们这些江北佬玩的地方呀。江北佬,你说你是江北佬。叔叔的说法很新鲜。是呀,我们都是江北佬呀,在上海,江北佬是最吃不开的,小瘪三闹你,上海人也瞧不起你哩。上海人有啥了不起的,我有些气愤。叔叔说,瞧不起也就罢了,反正他过他的,我活我的,主要是我拖家带口一大帮,全靠我一个埋头拉车,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呀。
那就回呗,我安慰叔叔,回来种地,还有咱们一家子呢。是呵,正好那辰光你摆摆捎信给我,说家里在分田,要我赶紧回来,晏一步就完了。叔叔说着搂紧我,紧紧的搂着我,我真的要感谢你摆摆呀,要不是他,我连站脚的地儿也没呀。他不是你大哥么,我大方地说,心里头也很为父亲自豪,而且你只有一个大哥呵。是呀,叔叔捏捏我的鼻子,我欠他的,一辈子都欠他的,我欠他一辈子呀。你欠他个啥呀。叔叔正想说下去,妈儿,也就是我婶婶在屋里头喊他了。一晃眼的工夫,我觉得妈儿悠长的呼喊再也不那么刺耳了。
叔叔回来后,父亲立即把房子让给他,还修补粉刷了一下。父亲自己则带领我妈和两个孩子,在河北砌了三间五架梁的元宝屋。叔叔住的房子是青砖青瓦,房梁和桁条还都黑乎乎的,仿佛还在诉说着日本鬼子的罪恶。这房子还是曾祖父传下来的呢,要不是鬼子在冬天放了一把火,我家会有数不清的房子的。叔叔住的房子,就是用烧剩的瓦片、木头心子重砌的。祖上在曾祖父这一辈最兴旺了。曾祖父的梦想是考个武状元,结果比武那天,他突然闹肚子,勉强上场,只一个回合就给人扁坐到地上,爬不起来了,兴许是他不愿爬起来,因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再给人扁一次。所幸瘦死的骆驼比马肥,状元没捞到,曾祖父在地方上的名头却依旧响亮。曾祖父一生就爱抱打不平,当然他的抱打不平是有收益的。用现在的话说,曾祖父靠一身武艺,专门替人讨债。再粗俗一点说,曾祖父是个打手,顶多也只个高级打手。所以,对那些有钱的主儿来说,我的曾祖父没有考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甚至还暗自庆幸呢。
父亲说,实际上他爷爷并没有真正打过几场架,那些逃债的只要一听说这事交给我曾祖父管了,往往立马抬着礼箱,递贴投拜。最传奇最怪烈的一次,就是给人拦截在独木桥上。面对着桥这边的鬼头刀和桥那头的链枪长矛,曾祖父反而笑了,笑声朗朗,惊得喜鹊和乌鸦齐飞,树林和河水变色。曾祖父拨开刀丛,跳离了独木桥。围攻的人越聚越多,殊不知曾祖父怕的就是人稀,只听他张飞般断喝一声,在敌人目瞪口呆之际,他虎背轻舒,熊腰徐展,抓住一人的双手,反扣到脊背作了盾牌,又抓住一人双腿作了武器护在胸前,大摇大摆的走进重围。我曾祖父天生眼如铜铃,手如蒲扇,加之披着独门盔甲,舞着奇门兵器,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收了两头的好处费,曾祖父没有买三妻四妾,而是置办了百亩良田,又大摇大摆做起太平乡绅来。据说每一任县官,都到我家求计问策过。要办什么案子了,这些县官也会着人过来,和我曾祖父“协商”一下。遇到少数不知深浅的,又恰是与我曾祖父有关的,他便骑上平原上唯一的一匹马,一直骑到大堂之上,举着“回避”的公差赶紧扔掉牌牌扶他下马,而“肃静”则接过马鞭拉过缰绳,紧跟着“赵五”看座,“王六”上茶,那可怜的县官一瞧架势不对,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的份了。
父亲是以训示的口吻,对叔叔说道这些辉煌的陈年芝麻的。估计叔叔已经听过千遍万遍,但还是硬着头皮听着,恭恭敬敬听着。父亲为啥一说再说,恐怕也只有叔叔晓得。再怎么着,老大把房子白送了他,他想去帮老大踩水土抹泥墙,老大都没要,老大的罗罗话不能不听听吧。事实上,叔叔不仅认真恭敬听,而且对我父亲言听计从。偶尔,叔叔也想抵抗,但是那种抵抗的想法总是躲在嗓子眼里,一发出就成了含混不清的声响,父亲严厉地问,啥,你说个啥?叔叔就赶紧埋下头走开了。
凶归凶,父亲对叔叔一家从来都是尽力维护的。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不要说逢年过节了,就是平常裹饺子吃面条,或者来了客人,总要把叔叔喊过来,喊一次不来,就喊两次三次。不管叔叔来不来,还总关照我妈送两份过去。也难怪妈妈有意见了,请就请了呗,请了还得送。不仅妈妈有意见,我们都有意见,只是不敢提罢了。可只要父亲一哼,妈妈还是乖乖地分送过去。妈妈一手端不下,就叫我们跟着送。我们也是自吿奋勇的。走在路上,尽管妈妈一直警惕地盯着,我们总还是有机会短两只饺子,或者吃一嘴盖在面上的肉丝的。可有一天让父亲喝住了,父亲说,一趟送不下,就跑两趟呗,又不是啥重活儿。大概父亲是看出了我们的名堂,又不想揭破吧。
要是叔叔,或者叔叔的孩子们受了欺负,父亲也总是要出头的。反过来,我二哥有次在河工上,让人打了,父亲连听也不愿听,妈妈一再在他面前说道,父亲倒笑了,打得好,打得好,咋没打别人?让人家教训了,还省得我动手呢。
所以我们从来没想过,叔叔会和父亲分家,而且赶在他五十岁之前。我们不知道,叔叔离开他大哥我父亲还能怎么过日子。叔叔五十岁生日那天,摆了七八桌,父亲却离家去了弶港卖蚕席。他一直对叔叔提出分家深为不满,怎么着要提也得他这个做老大的提呀。再者,他有啥对不住这个老二,老二又有啥理由提呢。他怕叔叔来请,到时他去不是,不去也不是。谁知那天,叔叔家里的人一个都没来,一趟也没来。午后,叔叔的屋场上,鞭炮放得噼啪响,震得我们只得关上门捂住耳。后半夜,父亲回来了。主动问起叔叔的生日。妈妈白了他一眼,你还说呢,人家找你了找了个遍。我不在,你们也可以代表呵。代表个屁,妈妈说,你是当家人,你不去,难道我们还去混饭吃不成!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妈妈撒谎。瞧瞧父亲的满足相就晓得,妈妈撒谎,比我们水平高多了。
3
一大早,我在红星河头摸鱼捞虾,给父亲逮住了。一顿痛打是免不了的,我故作镇静,小腿肚还是不住地的抽搐。父亲把我带到大树底下,放我坐到他的腿上。树上,一只带露的知了叫得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父亲一伸手,摘果子一样把它摘下来,递到我手里。笑眯眯地望着我,我却不敢看他。我知道父亲不会打我了,心里还是紧张得乱跳,只想早点离开他的腿。他并没有圈住我,可我就是动不了。
原来父亲是想打听,叔叔和我到底唠磕了些啥。他这么快就晓得了,难道是家里有人告了密!妈妈经常对我们说,不要和叔叔家的人一起玩,那自然是更不能和叔叔一起了。所以父亲虽然笑着问我,虽然给我抓了一只知了,我还是感到大事不好。幸好叔叔并没有说道父亲的不是,我可以如实相告。起初,父亲并不相信,他不相信叔叔会说他的好话。我说,牙牙说他欠你的,他欠你一辈子呢。父亲这才眉开眼笑了。他欠我个啥呀,父亲谦虚道,这世上哪个欠哪个的呀,再者他是我兄弟,我不拉他哪个拉他呀。就是嘛,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到底欠你啥子呀。
那他有没有提起,父亲追问道,他在上海的时候,我给过他金子呢。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得老老实实回答:这倒没有,你给他金子做什么。父亲没睬我,脸色又灰下来。我见父亲转眼间又不开心了,赶紧补充道,牙牙说了,要不是你捎信让他家来,他恐怕现在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你不仅让他有了田,还给他安了家哩。父亲一听反倒火了,一脚踢在树根上,踢得树皮纷飞,苔藓四溅:我叫他,我还捎信给他,他就是在掉在黄浦江里,我也不会去捞的。见我惊异地瞅着他,父亲冷笑一声,他呀,他是走投无路,躲藏不了了,给押回家的,这他也没有说吗。
押回来的!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同时我还发现自己紧张得鸡皮疙瘩后心凉,这么说叔叔是个坏人!叔叔一个拉车的,配得上押送吗。要我相信父亲的话,倒不如让我相信那颗金牙呢。可父亲啥也不说了,半个字也不愿意透露了,他推开我,拍拍屁股说,你实在想要晓得,那你还是去问你牙牙吧。父亲边走边回头瞅瞅我。他量我不会去问。他估摸我再也不会和叔叔一家子套近乎了。父亲猜对了,我是不敢打听,但不等于“押送”会让我从此远离叔叔。恰恰相反,我到叔叔家去得更勤了。我总是瞅空儿去,而在路上,碰上叔叔家的大人孩子,我又表现得心里战战兢兢,脸上满不在乎。
我判若两人的表现让家里人放下心来,叔叔一家子却感到莫名其妙了。说良心话,叔叔一家老小对我还是非常疼爱的。大概一来我是个孩子,他们没有必要和我计较,二来我在家里面,也是个老幺,他们疼我,也可能有希望和我们家改善关系的意思。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景,一见我的犟相,堂姐或者妈儿就会把我搂在怀里,抚摸我的额头,问我到底咋的了。有时候,堂姐还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一块纸包糖。我不喜欢堂姐,但糖,我是会收下的,手心攥紧糖的同时,我会一摇头,一耸身子,蚕蛹破茧一般,挣脱她们,撒腿就跑。其实我是多么迷恋她们的搂抱呵,堂姐长得不好看,可她身上的香和大姐又不一样,大姐的香是槐花般的香,而我堂姐和妈儿的香是百雀羚的香。她们搂抱我的时候,我能感到自己的战栗,我晓得再呆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我都有可能在那迷人的香气里昏睡过去。
现在想来,我的异常表现,全是源于他们是上海人,我好奇、敬畏,又嫉恨、恼怒,我始终不承认他们是上海人。就算她们是上海人,我也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呵。然而,下一次,我那迷了路的腿又不做主的拉扯着我,悄悄跑到叔叔家,依在他们门前,或者坐在他们家的门槛上。叔叔全家人一如既往,相当热情,叔叔会对我笑眯眯的哼一哼,而妈儿永远都能从房里找到好吃的,年糕呵,脆饼呵,麻团呵,诸如此类的搞子,哪怕我堂弟馋得流口水,或者做出奇形怪状的动作,也没他的份。总之,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对他们的不敬,叔叔一家也似乎根本就没在意我对他们的不敬。
不过每次妈儿给我零食时,叔叔总是有话要说的。叔叔说:“慢!”妈儿的手就停在半空中。一家人都能听到我的哈喇子在喉咙口咕咕的流,当然,小弟的哈喇子永远都比我还要多,还要响。
叔叔说:叫我一声吧,你来了半天还没叫人呢。看在妈儿的份上,我便“牙牙”一声。哪个大人不喜欢有礼貌的伢子呢,盐多不坏菜,礼多人不怪,舌头打个滚,叫人不蚀本。可叔叔听了,却急急的说,不是这么叫法的。那还有啥叫法子呀。叔叔放下筷子,耐心地解释道,叫芽雅,不是牙牙,然后他期待地望着我,抖动着嘴巴。你不是我的牙牙吗。是呀,是芽雅!叔叔点点头。叔叔重复了两遍,可我叫出声来的还是牙牙,叫得堂哥堂姐们都笑了,叔叔没笑,还有点气急败坏,他狠狠地剜了妈儿一眼。妈儿比叔叔小八岁,又白,当然不甘示弱了,她边朝叔叔对眼,边把手上的吃食递到我跟前。叔叔只好拿起筷子,朝我舞着说,哎,好吧,叫不来就叫不来吧,那你就叫我一声叔叔吧。叔叔?我为什么叫你叔叔!对呀,叔叔乐开了花,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哼,你耍我,这回轮到我气愤了,你才不是我的啥叔叔呢。我扭头就走,当然没忘了抢走那些好吃的,我听到小弟在我背后哇的哭起来。
我不知道“叔叔”是什么。我只在电影里头听到过这样的称呼。还是后来二姐告诉我,叔叔就是牙牙,准确地说,就是芽雅的意思。二姐在我面前,多少有点炫耀的成分,可我不问她,还能问哪个呢。怎么问起这个,二姐突然警惕地审视我,她似乎想起了啥。我也明白过来,绕来绕去的,原来叔叔还是称了心,怪不得他乐得不成人样呢。很快,全家人都晓得了这件事。我们坐在方桌边上,瞧着烟雾里的父亲。父亲捧着他的宝贝铜烟袋,定定地放在膝盖头,眯着眼,从鼻子里放出烟来,好像在找寻桌缝里干硬的米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听见父亲说,嘿嘿,这个二杀头,倒是真拽呀,还要伢子叫他叔叔,拽到天上了!啥呀,妈妈说,人家拽到上海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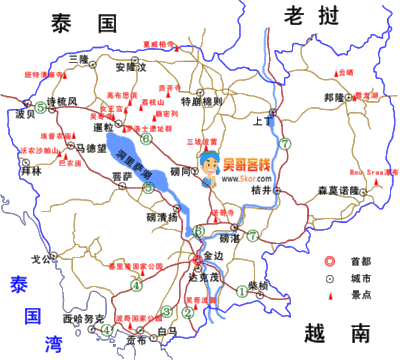
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不用怕犯错误,怕的是犯同样的错误。现在我终于有了体会,叔叔再也沾不到我的便宜了。不管叔叔怎么诱惑,我都没再上过他的当。我不明白的是,叔叔为啥如此看重这个叫法。叫牙牙不也是挺好的吗,再说我们也叫惯了,一时半会也改不过来呀。后来,叔叔再提要求时,我便说,牙牙呵,叫你一声并不难,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啥条件,你说,我就喜欢你这样讲条件的伢儿。叔叔既意外,又惊喜。我说,我还能有啥条件呀,我扫了扫堂哥堂姐,根本没把小弟放眼里。我说,只要你让他们改口,我也改口。改啥口呀,叔叔疑惑道。他们不是叫你阿爸吗,你先让他们叫你摆摆呀。说完我照旧扭头便走,不同的是这回我没要妈儿手上的零食,理直气壮,所以我也没听到小弟的哭,反倒是叔叔的饱嗝,舂米样的传出来。看来我的这个要求击中了要害。天,我怎么这样机智呀。
有时候,我也会扑空,叔叔家里的人都不在,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连小弟也不晓得野哪去了,只有我奶奶在东房里摸索,或者扶着门框,仰望门外的光线。“要下雨了,”奶奶望了一会儿就这么说。“天凉了,”过会儿,奶奶又说。她一个瞎子,我不晓得她凭啥这么说。奶奶的眼白有钱币那么大,奶奶说,那是云朵飞进了她的双眼。奶奶说,谁让我天天看天呢,天天看天,老天爷不乐意了,嫌我多事,就派来云朵挡我的路。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奶奶得的是白内障。奶奶不是瞎子,奶奶的眼睛完全可以治好。事实上,我父亲也准备给她治,哪怕去上海,也得给她治。可奶奶不领情,甭管咋劝法,奶奶就是不想治。奶奶说,我都七老八十的了,还花什么冤枉钱!老大,你是钱多的没处去么,奶奶说,钱多,那就买给我吃吃吧。再劝,奶奶便唉呀呀的叹口气,老大呵,你说,我就剩口气了,看好了做什么呀。父亲说,看好了眼睛,你方便些呀。我有啥不方便的,我有啥不方便的你说,奶奶气恼了,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么,老大呵,我也不是怪你,你说这世上,还有啥我没看过的么,我看多了,看透了,也看够了,看不见我还觉得安逸些呢。
安逸,在我们这里说成“唔依”。的确,奶奶除了走路要扶着拐杖、门框、凳子走,失明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她总是自己倒洗脚水洗澡水。她在窗户下支了一口窝,自己做饭烧菜。有一次,奶奶甚至跑到村口买回了盐,结果给老大骂得不吭气儿了。父亲不让奶奶出门,说她在出一家人的洋相。奶奶说,好了好了,以后我不出去就是了。不出去,奶奶照样不闲落,她总是让自己忙活着。不是忙着用铁元宝磨豆瓣,就是在床头翻她的小包包数角票。但只要有人现身,奶奶就安安逸逸的坐着,扶着她的拐杖。她装得没事人一样,其实我们对她的小包包了如指掌,小包包里也就一两块零碎钱。因为一旦有了几个钱,她又会分发给我们。父亲让她留着,她便说,我要钱做什么。父亲说,你身上有了钱,也好防而不备呀。奶奶更来劲了,我有啥要防的,大不了是个死,我要是死了还要钱做甚的。
看见我,奶奶很高兴,但是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三子呵,你来了,”她总是能看见我,看见所有的人。有时候,家里来了亲戚或者大队干部,大家坐到桌头,也把奶奶请坐到最大的位置,总是让奶奶猜一猜。奶奶一猜一个准,我们都有些怀疑奶奶到底瞎了没瞎。每次我到叔叔家,就是再悄手蹑脚,也逃不过奶奶,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总要给她吓一大跳。尔后我垂头丧气,乖乖隐进她的怀里。奶奶好的就是这一口,她喜欢我们摸捏她的奶房,最好是再吧嗒吧嗒咂两口。我的哥哥姐姐都咂过奶奶的奶房。奶奶永远露着上半身,让我们忘了季节。奶奶的奶房和队里的母牛有得一比。可不知是新鲜感消失了,还是奶奶的奶房越来越像水袋,且是干瘪的水袋,我们越来越没兴趣了。就算拗不过她的面子,也只是应付式的摸一下两下,就草草了事。
我抱着奶奶,我的头埋进她的奶房之间正正好。奶奶的喉咙里,竟然也和我一样,咕咕咕的流着哈剌子。正想着瞅空逃跑,奶奶说,你这就走吗,二丫头在房里呢。
二丫头叫雯雯,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也从没当她是堂姐。一听这名字我就来气,庄上的女孩子不是叫芳呵云呵就是菊呵兰的,凭啥二丫头叫雯雯呵。听雯雯说,阿爸拉车拉到衡山路,碰到另一个拉车的,那伙伴告诉阿爸,说他老婆生了,在家嚎着呢。阿爸没歇脚,只是问生了个啥。丫头宝!那工友说着话,连人带车呼的就过去了。阿爸的步子反而慢下来,慢得车上戴礼帽的四眼狼不耐烦了,嘀咕着催。阿爸等的就是四眼开口,四眼一开口,阿爸说,他今天不收车钱。四眼说,你这么慢,还不如我跑呢,你是不该收。阿爸说,他只想讨个吉利。四眼笑着说,是我讨到了吉利吧,我天天得坐车,要是天天有人不要我车钱才好呢。阿爸说,老婆生了个丫头,先生,你给送个名儿吧。
叔叔这才有了个丫头叫雯雯。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