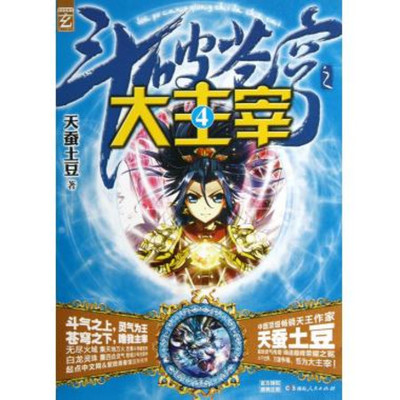正在修改我的书稿,曹雪芹“十八易稿”,我是没出版以前,会一直“易”下去的,“可能八十易稿”。网友会说,“你除了刘炽和你的那些破事儿,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啦?”当然有,但我现在已经是古稀老人了,时不我待,我必须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与刘炽有关的几本书上,也就不说其它的事情了。今天是我的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我把《活着,只因为有爱》书稿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活着,只因为有爱(书摘选段 五)
囹圄半月记
1989年4月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妨碍公务罪”拘留我十五天,25年前的今天,是我出拘留所的日子。我查阅了当年的日记:
1989年3月28日星期二
刘炽被传,由一青年陪他到正义路的中法。回来后脸色极难看,我侧面问了一下这个青年,他说:“情况很不妙,那位女审判员对刘老师态度极坏……”
1989年3月29日星期三
刘炽烧至39度,吃了点扑热息痛和螺旋霉素,又请来村里私人诊所的阎忠瑞大夫给打了针,仍不见好。
晚饭后,大约九点来钟,突然敲门声。开门,闯进来一女三男。后听刘炽说,女的就是那位审判员陈XX,男的是书记员肖XX,一个穿着公安服,听他们叫他刘XX,是当地派出所的,还有一位就不知道叫什么了。是我去开的门,陈问:
“你是谁?”
“李容功。”我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在这里?”逼问。
“照顾病人。”我不卑不亢。
“为什么用你来照顾!”态度相当蛮横。
“热爱共产党,为共产党爱护老干部。”我理直气壮。
四个人冲进屋里,既没出示证件,也没有传讯单。就在这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逼着正高烧着的刘炽起来,任凭我阻止也无济于事。刘炽在他们的强制威逼下,恹恹地拖着病体,坐在桌边的凳子上。他们把我撵到外间。
审完刘炽,不准刘炽上床休息,让刘炽到外间。又把我喊了进屋,对我进行提审。唇枪舌战,我毫不示弱,对陈等人夜闯民宅非法审讯提出强烈抗议,并偷着用小纸条在腿上记下了其中三人的名字,审问的要点。被发现,四人一齐围上来,要抢我的记录,我拒不给。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刘炽进屋来相劝,我乘机把纸条放入口里嚼碎咽下。但那三个人的名字已深记在心里。
这一夜,我几乎没合眼,陪坐在刘炽身旁。刘炽对我说:“小妹呀,你回大连躲躲吧,他们不会放过你,要出事的。”看着可怜兮兮的刘炽,惊惧无助地望着我的眼神,我坚决地摇摇头说:
“不,我和你共存亡!”
刘炽一把抱住我,眼泪哗哗流下来,流在了我的脸上、衣服上……
1989年3月30日星期四
家里一拨一拨的人来看刘炽。大家知道了昨夜的情况都非常担忧,也劝我暂时避一避风头,他们帮助我照顾刘炽。我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刘老师这个样子,我是决不离开他一步的。
果然,晚上六点多钟又有人敲门,该来的全都来吧,我毅然地开了门。刘炽的大女儿带着一个男打手冲了进来,伸出戴着不少戒指而金光闪闪的拳头直捣向我。正好薛里(文工团乐队队长)和两个青年来看望刘炽,还没走。刘炽的女儿被大家拦住没打着。
由于薛里护着我,我冷静地看了看这个刘炽的骨血,脸上画了浓妆,我在想,她能是刘炽的女儿么?来打架杀人还这么精心化妆?化妆画得有点水平也罢了,脸上画得五马六道的。
我的心灵里,与刘炽有关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刘炽的狗也应该是绅士派的狗,刘炽的猫也应该是双眼皮的猫,刘炽的女儿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她东一拳西一脚,打不着我。她发了疯,嘴里骂着粗话——刘炽的女儿竟能骂出这么难听的话?!然后她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砸得稀里哗啦,一地碎片,又操起菜刀。客人小韩也跟着进了厨房,竭力阻止,夺下菜刀,小韩的手被割伤了。大家把她推了出去,她拣起砖头一顿猛砸,把门窗的玻璃砸得稀里哗啦……
她在文革中,刘炽尽管被批斗,还是尽力找了各种关系,把她送到新疆部队打篮球,逃过了上山下乡。由于是打篮球的,所以命中率特高,前前后后的玻璃无一不命中。因为她是刘炽的女儿,薛里他们也就不好对她动粗,只把她推出门外。
男打手一进门就被两个青年制服,然后推出门外。后来我了解到,那男打手是蹲过八年大狱的刑满释放人员。
刘炽啊刘炽,您的女儿怎么和这些人鬼混在一起啊!

因正是下班后,楼下围满了人群,水泄不通。只听刘炽的女儿在楼下对围着的人群又哭又叫,中间还夹杂着脏话……
我听着外面的臭骂和哭嚎,望着围得满满的人群,再看着瘫坐在床边的刘炽,脑子一片空白……
刘炽女儿打够了,骂够了,房子全部玻璃砸碎了,看看我家有人拉架,她打不着,只好走了。走时,还大喊大叫:
“以后,我天天来,不把你这个大流氓、老王八蛋,还有那个骚货、婊子打死打瘫,决不罢休!大流氓、臭婊子,你们等着……”
三月季节,乍暖还寒,这第14处住房被砸得不成样子了,不能住了。天黑了下来,外面的哭闹声早已没有了,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安静得出奇。刘炽被青年小韩带到他北京的亲戚家去,我回到姐姐家。
当我引用这些当年记录的材料时,我想,这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边远山区的屯儿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怪。可是偏偏发生在刘炽这样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家里,真是难以让人置信!女儿骂父亲“大流氓”“老王八蛋”,砸父亲家,拿刀杀父亲,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名人家里,前不见古人(后是否有来者难说)的一出最大的闹剧丑剧!
1989年3月31日星期五
一夜都未合眼,我为刘炽担忧。昨天他女儿的一通打砸,刘炽能经受得住吗?
一早到小韩的亲戚家,小韩也急切地盼着我去。他说刘老师状况很不好,昨晚他们也很害怕。刘炽果真支撑不住了。我给他量脉搏,早搏次数多;量血压,不好;试体温,有点低烧,可能早上降下来了吧,他说昨晚他很难受,感到身上很烫很烫。立即招呼小韩和我一同陪刘炽去朝阳医院。诊断:冠心病,大叶肺炎。当即住进了高干病房310室。
我一步也不敢离开,让小韩出去给刘炽买了洗漱用具和饭碗之类。
目前这种情况,我在医院护理刘炽可能要惹麻烦。于是我拨通了瞿弦和团长的电话,报告了刘炽的病情,要求谈谈,由组织派人来护理刘炽。答复是明天到医院见我。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刘炽,他拉着我的手可怜兮兮地说:“小妹,你真的要把我交给团里呀?”我说团里来人总是好些,我会天天看望您的。我再没深说下去,我知道,如果我天天按时这样来护理他,迟早在朝阳医院门口会被他的家人堵住,又会发生一起血案的。
我听来人说,一早团里几位主要领导,还有主管老干部工作的刘祖发,以及、洼里派出所的人都到刘炽的临时住所去了,调查昨天被砸情况,还拍了照……
那个审判员陈XX也去了,她怎么知道昨天刘炽女儿去打砸的???!!!
岳国政(现改名岳楚渔)经理也来了,送给我防身用具,让我进出医院要时刻小心,不要让他们掌握规律,医院的门有好多,不要老是从一个门进出。他说,刘炽家里的老婆孩儿、亲戚已扬言,不打瘫我誓不罢休……
直陪刘炽到晚上八点多钟,才依依离别了奄奄一息的刘炽。小韩怕我出事,送了我好长一段路……
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一早就起来,给刘炽炒了榨菜肉丝,炸了他爱吃的油辣椒,熬了绿豆粥,还把我姐夫的衣服拿去给刘炽换洗。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书的女儿小红陪着我来到朝阳医院。
一边守护着刘炽,一边等着瞿弦和来,一边抄写刘炽口述的,关于中法审判员陈XX夜闯民宅,威胁病中的七旬老人刘炽的《举报信》,让女儿小红回学校时帮着寄出。
时针已指向下午4点30分,仍不见瞿弦和的面。这时,一个穿白大褂自称本院医务处的人来到病房,问谁是刘炽家属,医院要向家属谈谈刘炽的病情。我告之我们都不是家属,一会儿团领导来,和刘炽的组织上谈吧。这个“白大褂”就是不走,磨磨蹭蹭,吞吞吐吐,说刘炽的病……
我发毛了,十分恐惧,68岁的人了,受这么大刺激,是不是……我迷迷糊糊就跟着这个“白大褂”走出病房,让小红看护刘炽。我只想知道刘炽的病情,他到底怎么啦?是否有危险?“白大褂”领着我走出病房,走下楼梯,又带着我走出住院部的大门,我好像一个木偶似的听他指挥着。刚走出大门,一辆轿车停在那里,从车里走出一个女人来,就是大前天到立水桥夜审刘炽和我的陈XX——刘炽离婚一案的审判员。
“你被拘留了!”递过来一张纸。我接过来看,是一张拘留证,其罪名是——
“妨碍公务”。
我转身想回楼进病房,告诉我被抓的消息,并取我的手提包和风衣。
“不许去!马上跟我走!”陈凶神恶煞,似和我有前世冤,后世仇。
“为什么?什么大案要案,连包也不让取,衣服也不让拿?”我据理质问。
“就是不许去!”陈蛮横得脸都变型了。强权即真理,我毫无办法。
只好上车,车上还坐着书记员肖。我冷漠地望着窗外,仔细辨认着路线,我要知道他们究竟想把我带往何处。车行了不长时间,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下来。我下车,看到大门旁挂着一块大牌子:
崇文区公安分局。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我记住了这个时刻,1989年4月1日下午5点10分。
我和一群卖淫女关押在一起
一番例行的手续。我到很简单,无包可检查,也无钱可存放——因为我的手提包丢在了刘炽的病房里。我一贯不穿系鞋带的鞋,也不系腰带,裤子从里到外全是松紧带,被拘押的人是不允许身上有任何带子的。只是把手上的手表取下交上,填了单子。然后是一个女狱卒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全身。于是我成为合格犯人被投进了女监。
这时晚饭已经开过了,一个看守递给我两个窝窝头,说菜没了。我没接,我没有胃口。
只见屋里挤满了被拘留的人,一个大通铺,人挨着人,已没我的地方了,只好先蹲在靠门角的水泥地上。
一片乱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也有上前向我询问的,我不看,也不答话,一门心思心急火燎地想:刘炽正病着,我突然失踪,他肯定会急疯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
果然刘炽疯了!毅然拔下输液的针头和鼻子上的氧气管,老岳包租了一辆车,和小红陪着刘炽满北京城寻找着我。先到朝阳医院询问,问谁谁不知。一再找关系才打听到,那个“白大褂”并不是什么医务处的,而是医院保卫人员,是陈某让他把我从病房骗出,人已被抓走了。
刘炽“病急乱投医”,让老岳把他拉到煤炭部于洪恩部长家里求救,于部长哪里能管这些事情,打了个电话让下面的人问问情况也就把刘炽支走了。刘炽再去到原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家,刘炽在辽宁歌剧院时期,与宋任穷的关系极好,到北京后刘炽也与之有走动。刘炽去后,一讲是关于“第三者插足”的事情,宋任穷没有露面,让秘书过问一下就把刘炽打发走了。
刘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跳楼,要自杀,说我没有了他也不活了!被老岳和小红劝住,一再安慰他说会把我找到的。刘炽不听,带着病写了向全社会的《呼吁书》。
记得在离婚大战中,不知道哪个人给他出的主意,让他给中央主管政法的彭 X写信,我坚决阻止了,一再对他说:
“不要找任何人,谁也帮不了我们。尤其不要找那些你过去熟悉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不会管您的。万一他们做个不利于您的批示,那谁也不敢判离了,您就这样被拖死了。我们自己死扛着,是活是死认了!”
刘炽确实乱了方寸,忘记了我曾经一再的嘱咐。他给看着他在延安长大成才的,对他一直不错的康克清、邓颖超、王震、习仲勋等中央首长写了求救信,一定要小红和岳经理发出去。
我出去后知道了这些情况,对刘炽说:
“您违规操作了,您也太天真了!您不是没有经过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谁要是出了点问题,或是被揪出来,保持沉默不往井里扔石头就算是好人了,‘哪个鸟儿敢作声’?那些您认为爱您的中央领导,谁会出面管您?朱德的孙子在1983年被枪毙,康克清都没有为孙子说一句话。”
在我被拘留的第二天,岳经理带着小红到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找陈XX,这是个星期天,陈XX不上班。问值班人员陈X X的住址,说不知道。直到4月3日,才听到,我被押在了崇文区公安分局。刘炽马上派小红为我送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小红骑着车到崇文区公安分局,不收,说人是中法寄押的,中法的人说了,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必须要他们开条子才能办理。小红又跑到中法找陈和书记员肖,两个人推来推去,咬住说不必开条。小红被支来支去,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跑,东西就是送不到。
4月4日晚上,我突然被叫出监房,来到一间房子里。一个高高大大穿着法院制服的人问我:“你认识赵XX吗?”我想,这是干什么?又扯上了别人?我马上摇摇头。他又提了另外两个我熟悉的人,我还是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认识”,“不知道”!
他笑了说:“我是陈 X的弟弟,是这里的预审科科长,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可以帮助你。”
陈 X是某部的团委书记,来过刘炽立水桥的家,我这才相信了他,我急忙问他:“刘老师怎么样了?”他说:“刘老师身体还好,没危险,你放心。”我对他说:“我要手纸,要手纸,要手纸!”我连着重复了三遍。停了一下,我又说:“要牙刷!要生活用品和换洗的衣服,尤其多带几条内裤!请你让我姐姐赶快送来!”我告诉他我姐姐家的电话。
1989年4月5日——清明节,也是我被拘的第五天,我才得到了家里送来的我最最急需的手纸、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我出来后才知道,刘炽找了所有他认识的人,最后,李坚(刘炽的合作者)找了他学生的朋友陈X,陈的弟弟——就是那个预审科科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把东西送到我到我手里。
我后来看了看刑法条例,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被拘留的人,在24小时内要通知家属。可是,陈 XX这个执法者却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执行。
东西是我姐夫送来的,但不准我姐夫见我,姐夫只好拜托陈的弟弟、这位预审科长替他交到我手中。拘留所管这个事的人,当着预审科长的面,把包里的东西全部扔在地上,这是这里的规矩,这是告诉犯人,你不是人!
我只好弯下腰来把东西一件件从地上拣起放进包里。有两件衬衫,四条内裤,好几卷手纸,毛巾牙刷肥皂香皂等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当我拿着这些东西进到监房,无数双倾羡的眼睛投向了我。
那些天,最痛苦的是手纸问题,正好我来例假。这间监房一半以上是卖淫女,有着程度不同的淋病(梅毒者方被隔离)。我一一弄清了她们的身份后,才挑了两个诈骗犯的手纸用。我对这两个人说,我家里会送东西来的,到时我一定加倍奉还。这些天我是尽量憋着,但手纸不够,裤子被血浸透了,顺着腿流下来,连我坐的水泥地都有血。现在想起那滋味来都起鸡皮疙瘩。
监禁的生活是可怕的。这里确实是社会最底层。被关押的人也分三六九等,听说在我来之前,还实行进屋三闷棍,进去先把你狠揍一顿,再把你带的包翻个底朝天,东西被洗劫一空,这叫“煞威风”,使你不得不老老实实惟命是从,我进去时此风已经被制止了。但里面一帮帮一伙伙抱成团,他们一个眼神一声咳嗽都是暗语,就有“事儿”,你就得小心。
我住的那间监房大约十七八平米,长不到五米,宽约四米多。从里面墙到四米处垒了一个大通铺,这十几平米的地方住人。我进去时,这通铺上已挤了16个被拘押的人。地上三四平米,靠墙是抽水马桶、水槽,犯人可以在屋里大小便、洗漱和洗衣。
当时,正是开人大会期间,北京整顿社会治安,扫黄严打。于是这屋里便人越挤越多,只进不出。最多时押了26人,铺上爆满,地上只能挤着坐。我整整坐了15天!有的人结案去劳改或是放了,我也排队依次熬到了上炕的资格,却毅然放弃,宁愿坐在这又潮又凉的水泥地上。因为我不敢混迹在那群卖淫女中,怕被染上淋病。为此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落下了腰腿疼病!到现在我走路,熟人总说,李老师,你怎么走路摇摇晃晃?
东西送来了,大家看我得到家里送来的这么多生活用品,而且都是高级的,羡慕之极!她们中许多人是外地流窜来北京而被抓的,没有人送东西,有的也没有钱买。我俨然成了“囚犯贵族”。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15天,也是备受屈辱的15天!正是在这摧残肉体与心灵的15天中,我看到了社会阴暗的最底层的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我在这里读了“博士生”!
在这一堆卖淫女中,一个比一个漂亮,最漂亮的要数从沈阳窜到北京的那位小张姑娘。她比我晚进来一天,当然也是“睡地族”,她是从匈牙利大使馆出来时被抓来的。当她睡觉时,我看着她,好漂亮的姑娘啊,简直像个“睡美人”!我想着,她为什么要走这条人生路呢,就凭她的姿色,找个有钱有势的好男人是不成问题的呀。
还有两个新疆来的女孩儿,都是十七八岁,也长得不错。听说被两个“大款”(香港来的老头)包房,就是现在说的“包二奶”,再说得好听点,就是“性服务工作者”。每月包吃包住,还给每人每月一万四千元的零用钱,条件是随叫随到,也是“打黄扫非”期间被扫进来的。小姑娘烫着长长的钢丝发。她俩告诉大家,烫这个头发得140元(1989年称得上吓人的消费了)。闲得无聊,就翻出包里的衣裙穿给大家看,扭一扭,转转圈,摆弄个舞姿,美得不行。只是吃饭时皱着眉头,因为“大款”包吃,可比这拘留所的窝窝头强多了!
最使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位第一次让我知道“毛阿敏”芳名的的东北女人,听其他被拘留者小声告诉我,她是在建国门外掏包时被抓的,也是在这间监房里关押时间最长的。不管怎么审问,她都一口咬定自己叫“毛阿敏”,与当时的红歌星同名,决不说自己任何有关的情况。由于结不了案,她就在里面被拘着。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默认她叫“毛阿敏”了,称之“大毛”、“毛毛”。她是这里的一霸,每次吃饭,她总是推开别人,把饭碗从人头上伸过去。犯人轮流出去取饭分饭,不管谁分饭,首先把干的、上面带油腥的盛给她。否则,她就要打人。不光打一个,一打打一串。她可能在拘留所里呆的时间太长,已适应了这里的窝窝头熬菜汤,她很能吃,每顿两个窝窝头,一大碗熬芹菜或是熬白菜萝卜,全下肚。吃饱了无事可干,闲得无聊,就要找茬骂人或打人,她把全屋的人都制得服服帖帖。
我坐在地上从不看她一眼,几次她想对我挑衅,我始终未给她机会。后来我终于找机会干了我平生第一次干的,也是我最厌恶的事——向看守我们的李班长打小报告,谈了毛阿敏的所作所为。在她又滋事欺负小哑巴时,被李班长用电棍捅得呜哇乱叫,从此她收敛多了。
就这么个女人,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谁不说俺家乡好》,还有刘炽的《一条大河》、《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出拘留所心情平静后,告诉刘炽这件事,我说,老爷子,您还有一个知音在拘留所里呢,您应当去看看,表示表示您的感谢。刘炽笑得不行,说:“她真抬举我了,这么个女人居然唱我的歌,看来,我的歌,连罪犯都爱唱,我得谢主龙恩了。”
从她会唱的这些歌来看,她起码是“文革”前的中学生,也许是个老知青。从她的口音判断,她当是鞍山、辽阳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暴露身份,可能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吧。
还有个叫杨仙花的河南女人,名字很美,人却脏兮兮的,有点呆傻。在北京站卖淫,一碗面条就跟人睡觉。监房里谁也不准她靠近,被撵得踢得无处栖身,太可怜了!我让她挨着我,晚上我让她的头枕在我的脚上。我常常发现她把头放在地上,紧紧抱着我的脚。我知道了,她是怕把我的脚压麻了。这是我靠得最近的一个卖淫者,同情心使我战胜了对性病的恐惧。
一天半夜,这个杨仙花突然又哭又叫,在地上直滚,把大家吵醒了。有人开骂,有人要打。我奋不顾身地护着她,问她怎么啦?她说肚子疼得不行。我急得直用拳头砸门,喊“报告”!——监狱里要有什么事必须喊“报告”。于是,女囚们又冲着我开骂了,我不顾她们的臭骂,继续砸门大喊“报告”。正闹得不可开交,外面值班的看守吼着:“半夜三更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总算是有人来了,我大喊:“报告!我们这里有人病了,病得很重!”后来杨仙花被人架了出去,再后来听说她子宫大出血,如果再晚一点性命就难保了。
最招人喜欢的是小哑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叫那学丽,才19岁,细瞅瞅还是个透着稚气的孩子。她很依恋我,后来也挪到我身边,坐在靠门的墙边上,依偎着我。她是在北京站掏包掏了14元钱被拘的。她一直靠着我坐着,白天时光太难熬,我就让她教我哑语,当时我还真学会了不少。小哑巴性情刚烈,爱憎分明,只有她敢于和欺负她的“毛阿敏”平打平造。
小哑巴先我被放出,走时直拉着我的手比比划划,嘴里哇啦哇啦。我的哑语学得还不行,没弄懂她说的是什么,但依依不舍之情从她脸上看到了。
这15天里,我结交了一 个难友,她是在我被抓的第二天进来的。是个六十来岁的女干部。她一进女牢,就说:“同志们,我没有问题,我是清白的!”
我心里好笑,但没笑出来。都什么年代了,她还来这一套,跟这些人说这个废话干什么!这些卖淫女、掏包女、诈骗犯能是你的“同志”吗?看着挤得满满的牢房,我挪了挪屁股,终于腾了一点点空当,示意让她坐下。她坐到了我的身旁,后来我和她自然接近了起来。
她对我很坦率,告诉我她是山东人,当年的南下干部,后来以调干生在人民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在国家计委工作。她和中央某领导黄XX 侄孙女婿办公司,被人检举拿回扣而被拘审。她说她根本没拿什么回扣,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她看到女监里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还动员我和她为核心,做做可以教育的在押人的工作,向“毛阿敏”这样的人进行“斗争”,使牢房里风气好起来。
我笑了,对她说,这是共产党的拘留所,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你也别妄想学渣滓洞的江姐。面对这群地痞流氓无赖小泼皮,有什么工作可做?别扯啦,把自己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出去就万事大吉了。
她的家里不知是没有人通消息还是什么其它原因,一直没有人给她送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我得到家里送来的东西后,就分了一些给她。但牙刷只有一支,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刷了牙后,就用牙膏把牙刷使劲搓搓用水冲刷干净,给她用。晚上她先用,用完后再如此一番我再用。一直到我出狱,我们都是这么循环着共用一个牙刷,一条毛巾。
到底熬到15天了,我出狱了,我把我的全部用品都留给了她,我对她说:
“这些东西你就用吧,你出去后,把它们烧掉埋掉或扔进护城河里。让这些东西不要再在我的眼前出现也不要让它存在。”她答应了。
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北师大教书,女儿也有很体面的工作。我一听他儿子在北师大,觉得无比亲切,我姐姐、姐夫也是在北师大啊。我出狱还见了她的女儿,给她通风报信,让她设法给妈妈送生活日用品。她很委屈地对我说:由于她上班去了,法院把通知送给了她的邻居转交,后来又送到了她的婆家,大家都知道她妈妈犯法被逮捕了,使她在邻居和婆家抬不起头。我告诉她,“进去”的不全是坏人,我就是“进去”了,又从“里面”出来的,你看我是坏人吗?。一再嘱咐她,给妈妈送些日用品去。
我想起女儿小红,她陪着刘伯伯满世界找妈妈的情景,又是到法院,又是到拘留所,真太难为她这个大学生了。后来的日子里,刘炽一直对小红宠爱有加,而且一再跟我讲,小红当时天天骑着车跑朝阳医院,还让我姐姐给他做点饺子什么的带去,寸步不离他身旁,怕他出事。刘炽和小红的感情已远远超过了父女关系,他们还是忘年的朋友、知己。女儿有什么话不跟我说,跟刘炽说,因为,她觉得刘炽非常善解人意,比我通情达理。他们常常互相称呼“一帮的”,还说“加强帮性,一致对敌”,当然,这个“敌人”就是我啦。小红在外贸系统工作,工资较高,常常出国,大到发烧音响、电视冰箱,小到剃须刀,刘炽录资料用的磁带录像带,都是小红在国外买来送给“刘伯伯”的。还有那件红色的毛衣,刘炽上电视总是穿它,人们称为“刘氏服”。是小红到上海出差,跑了好几家商场买的,作为刘炽七十大寿的礼物。
看来,女儿和女儿差别也太大了,有打杀父亲的“狼女”,有父母出点事就觉得丢人而躲之不及的女儿,也有对父母不离不弃的像小红这样的孩子。
女儿不都是父母的“小棉袄”。
1989年9月,我的这位难友出狱了,来后,从报纸和电视里知道了我和刘炽的消息,给我往煤矿文工团写信,我们又联系上了。我还抽出时间到她三里河的家里看望过她,是小红陪着我去的。她告诉我很多我走以后的情况:那位“毛阿敏”不了了之,放了;两个新疆姑娘和漂亮的小张姑娘也放了;狱里又来了不少新的拘押犯。当谈到那段经历时,我俩唏嘘不已。她其实没什么问题,九月份也放出来了。
我出拘留所时,大家都请我给家里捎话,我在剩下的一块小肥皂上用手指甲刻上了他们家人的联系电话。我已经不那么厌恶她们了,出拘留所后,我都一一照办了。
牢狱的15天,我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我和刘炽的挚友、我们尊敬的大学者文怀沙先生,尽管80高龄,仍拄着拐杖,东奔西走,为救我出狱,找了各种关系。最后,和看管我们女监的李班长联系上了,由此我得到了相当的照顾,李班长常威严地把我吼出去,到她办公室“单兵教练”,然后和蔼地对我说:“出来透透气散散心吧。”女牢里很多情况是她跟我聊天告诉我的,她是军队下来的,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去看望她,当面感激她,这是我珍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但我终究没有去,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个地方,那“崇文区公安分局”的大牌子。
最难熬的是无书可看,我晚上从来都是捧着书看才能入睡的。那15天里,我几乎是瞪着眼坐到天亮。一天,一个在押犯接到检察院的公诉书,她看不大懂,就主动向她要来《公诉书》,我如获至宝,读给她听。一面读,一面给她解释。一遍又一遍地读,逐字逐句地解释,比给学生上课都认真。
这下可看到字了!看到带字的纸了!
她是因为其弟犯盗窃罪被捕,后来其弟有病住进公安医院,她帮助其弟逃跑而被抓进来的。她是我认为比较“干净”的犯人,也是借给我卫生纸的人。
15天过得是那样漫长,我心中惦记着病中的亲人,我想念刘炽,我渴望自由,在窒息中我倍感自由的亲切与重要。
我想起高尔基作词作曲的《囚徒歌》,那是我在大学时就会唱的。现在我坐在这拘留所墙角的地上,搂着小哑巴,靠着墙一遍一遍小声唱着这首《囚徒歌》:
太阳出来又落山罗 / 监狱永远是黑暗 /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 / 哎咳哎咳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 我决逃不出牢监 /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 / 哎咳哎咳挣不脱千斤锁链。
歌声传出,慢慢监牢里怪声浪调没有了,大家静听着,沉默着……
终于熬完了十五天,1989年4月15日,我被释放了,耀邦也在这天仙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