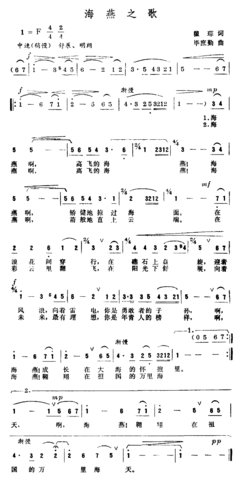(其一)
之所以选择阅读《拉奥孔》,最初还是被书名所吸引。想看看这个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祭祀究竟和美学有什么关系。
1766年莱辛开始着手创作,《拉奥孔》的另一个标题是“论画与诗的界限,兼论《古代艺术史》的若干观点”。在这部不朽的美学著作中,莱辛通过对经典艺术作品古希腊雕塑群像《拉奥孔》和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的比较分析,全面地探讨了诗歌和雕塑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区别及从这种区别中产生出来的特殊规律性。
一、美与丑
我们知道,在莱辛之前,有人曾就“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这个问题争辩不休,由此也得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温克尔曼的解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虽然拉奥孔在忍受最激烈的痛苦,他并不象在维吉尔的诗里那样发出惨痛的哀号,是因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在表情上,它们都显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很明显,温克尔曼把理由放在希腊人的智慧克制着内心感情的过分表现上。
而莱辛来认为,雕塑群中的拉奥孔之所以不哀号,只是因为要遵循造型艺术的特别规律而已。他说:“在古希腊人来看,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他们为了避免在表现痛苦时显示的丑态,有时往往完全回避激情或加以冲淡,为的是不影响美。”莱辛认为雕刻家要在既定的身体苦痛的情况下表现出最高度的美,身体极度痛苦情况下的扭曲变形同高度的美是不想容的,所以雕刻家不得不把身体的苦痛冲淡,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
在《拉奥孔》的第二章,莱辛通过描述提曼特斯在其画《伊菲革涅亚的牺牲》和三位雕塑家在群雕拉奥孔中如何避免或冲淡丑来表现美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须服从美。即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
二、最富于包孕的片刻
莱辛在《拉奥孔》第三章提出“造型艺术家为什么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
他把希腊名画家牟玛球斯和另一位画家的作品(二者都是以“杀亲生儿女的美狄亚”为画题)进行比较:牟玛球斯画美狄亚,并不选择她杀亲生儿女那一顷刻,而是选杀害前不久,她还在母爱与妒忌相冲突的时候。莱辛认为这一点的选取可使观众不是看到而是想象到顶点,比起画家如果选取杀儿女那一个恐怖的顷刻所能显示出来的一切要深远得多。而那另一位画家够愚蠢,他竟把美狄亚极端疯狂的顷刻画出。
他说:“人们从大风暴投掷到岸上的破船和残骸就可以认识那场大风暴本身”。“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他不能向上超越一步”。
由此,莱辛提出了“最富包孕性的片刻”一说。即造型艺术家应该选用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入手进行创作,使观众不是看到而是想象到顶点从而赋予艺术以持久性。
三、诗与画之界限
莱辛以前西方的大多数学者都强调诗画的一致性,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持续到莱辛时代。诗画一致说被理论界奉为金科玉律。而莱辛则在本书中向这种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莱辛首先指出,诗和画固然都是摹仿的艺术,出于摹仿概念的一切规律固然同样适用于诗和画,但是二者用来摹仿的媒介或手段却完全不同。这方面的差别就产生出它们各自的特殊规律。
莱辛认为一篇“诗歌的画”,不能转化为一幅“物质的画”,因为语言文字能描叙出一串活动在时间里的发展,而颜色线条只能描绘出一片景象在空间里的铺展。
就其艺术功能上的区别而言,绘画宜于表现“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或情事。针对于造型艺术,“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时刻”,所以除了选取最宜表现对象典型特征——比如维纳斯的贞静羞怯、娴雅动人而不是复仇时的披头散发、怒气冲天——之外,还应选取最能产生效果即“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也就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而诗则不然,这些对于造型艺术而言的限制条件对于它来说几乎都不存在。莱辛还列举了诗人可以描绘女爱神在要向凌辱她的楞诺斯岛人报仇时的形象而艺术家却不能的事实,以此来说明只有诗人才有一种艺术技巧,去描绘反面的特点,并把反面和正面的特点结合起来,使二者融成一体。
总之,莱辛认为,诗与绘画雕塑属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规律,他承认诗歌和绘画各有独到,而诗歌的表现面比绘画的“愈加广阔”。
总结
作为一部被誉为“现实主义美学里程碑”和“启蒙运动思想武器”的理论名著,《拉奥孔》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以上三点,只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我自己体会和理解最深的部分。但由于我在美学领域的知识面是无法达到莱辛那个广度的,他对古希腊文学和艺术的诸多引用和说明看起来都相当吃力,所以书中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理论,还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去细细揣摩。
(其二)
无可否认,莱辛的美学名著《拉奥孔》,无论是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建立,还是对整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诗人歌德在回忆《拉奥孔》所产生的影响时写道:“必须变成青年人,才能理解莱辛以他的《拉奥孔》使我们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他使我们的大脑从模糊直观的领域转移到了光明自由的思想世界”。
为了更深刻可地理解此书,我参看了朱光潜的《莱辛的<拉奥孔>》和钱钟书的《读<拉奥孔>》。一部作品,两种读法。朱光潜的读法是兼顾的,补充的,吸取式的。相比来说,钱钟书的读法则更为深刻、有着更多的比较和批判。他的研究有别于其他学者,即不是去找例子来论证《拉奥孔》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有所发展地对它作出了解释,补充,并匡正其谬误。我对《拉奥孔》的第二次阅读受钱钟书先生的影响很深。一边阅读,一边对比,一边思考,自觉受益匪浅。
一、关于诗所描绘的画面不能转化为绘画的画面问题,莱辛在《拉奥孔》中解释道:诗的描写是在时间中展开,而绘画的描写是在空间中展开,前者动,而后者静。钱钟书基本上同意莱辛的看法,但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莱辛的见解没有错,但是,对比着上面所引中国古人的话,就见得不够周密了。不写演变活动而写静止景象的“诗歌的画”也未必就能转化为‘物质的画’。”他指出:其他象嗅觉(“香”)、触觉(“湿”、“冷”)、听觉(“声咽”、“鸣钟作磬”)里的事物,以及不同于悲、喜、怒、愁等有明显表情的内心状态(“思乡”),也都是“难画”、“画不出”的,却不仅是时间和空间问题。
二、莱辛认为,从摹仿对象上看,绘画长于表现物体,而诗长于表现动作,诗若直接描写物体,常常是捉襟见肘,达不到绘画描写的效果。对此,钱钟书不以为然,认为莱辛的说法值得怀疑。在钱钟书看来,即使是对静止物体的描写,诗也有强于绘画的地方。他说:“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自己的彩色碟破产,诗歌里钩勒的轮廓、刻划的形状可能使造型艺术家感到自己的凿刀和画笔技穷。”他以苏轼咏牡丹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为例,分析了诗的物象描写具有绘画难以企及的虚实相生的效果。例句中的“红”是实色,而“翠”却是虚色,并非真指绿颜色其实是鲜明的意思。他认为表现一种颜色而虚实交映,制造两个颜色错综复杂的幻象,这是文学的特点,造型艺术办不到。他说:“设想有位画家把苏轼那句诗作为题材罢,他只画得出一朵红牡丹花或鲜红欲滴的牡丹花,他画不出一朵红而‘翠’的花;即使他画得出,他也不该那样画,因为‘翠’在这里并非和‘红’同一范畴的颜色。虚色不是虚设的,它起着和实色配搭的作用。”
三、一幅面只能画出故事的一场情景,所以莱辛认为画家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因为一达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钱钟书认为,莱辛所谈到的这种“画格”,它可能而亦确曾成为文字艺术里一个有效的手法。诗文里的描叙是继续进展的,可以把整个“动作”原原本本、有头有尾地传达出来,不象绘画只限于事物同时并列的一片场面,但是它有时偏偏见首不见尾,紧临顶点,就收场落幕,让读者得之言外。换句话说,“不到顶点”那个原则,在文字艺术里同样可以应用。对此,他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作为例子进行论证:契诃夫有许多“以不了了之”的巧妙手法,其中之一是避免顶点,不到情事收场,先把故事结束,使人从他所讲的情事里寻味出他未讲的余事或后事。莱辛在《拉奥孔》中试图说明诗中不该有画的因素,诗画是对立的;而钱钟书却恰恰认为诗画有许多共同点,“不到顶点”的手法既适宜于画也适宜于诗,就是一个明证。
钱先生自己在《读》一文的最后直言自己对于诗歌的偏爱,“也许……是我偏狭、偏袒、偏向着它。”不知为何,或许是由于与文学一直结下的不解之缘,又或许是由于我不懂画,看到这句话时,觉得自己的感觉与钱先生达成了默契,遂感到温暖而愉悦。纵然在第三次阅读《拉奥孔》时,在更加理性的视角里自己也发现了莱辛诗画理论中一些自己难以完全赞成之处。但就从纯感性地角度和个人喜好而言,我亦是偏向于诗的。莱辛说得多好:“生活高出图画那么远,诗人在这里也高出画家那么远。”
(其三)
不能不承认,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读<拉奥孔>》,我对他严谨而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试图在阅读中实践这种西方所推崇的criticalthinking。第一次读《拉奥孔》时候,处于对名著普遍怀有的敬畏心心理,对于莱辛的理论我几乎是全盘接受的。而在第三次读《拉奥孔》,我力求做到独立和公允。或许真的是“态度决定一切”吧。在这种阅读态度的指导下,竟然也发现了一些我个人认为的莱辛理论中的偏颇之处。
首先,我认为由于时代和个人艺术实践的局限,莱辛对诗与画的界限划分不但过分绝对,而且有明显的偏见。他提出“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并强调说:“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服从美。因此,他将现实中一切丑的,乃至所有看上去不能“引起快感”的事物,包括人物的激情,都排除在造型艺术所能表现的题材之外。诗人可以表现丑,造型则不能。这样他便从根本上否定了造型艺术全面、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莱辛以“摹仿自然”作为艺术本质的美学体系中,“真实”是比“美”更高的理论范畴。因此,他把美作为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而把真实看作是诗所追求的目标,这无异于说诗对于自然的摹仿,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造型艺术所永远无法企及的。用莱辛自己的话说:“生活高出图画那么远,诗人在这里也高出画家那么远。”可以说,莱辛为造型艺术制定的“最高法律”人为地使得诗的优越性得到彰显,而夸大了画的局限。这种对诗与画带有明显偏见的划分,不能不说是莱辛的一大理论缺陷。
单就诗学方面的成就而言,在西方美学史上只有少数的古典名著堪与之匹敌。俄国杰出的美学家和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谁也没有像莱辛那样正确和深刻地理解了诗的本质”,因为莱辛把人生看做“诗的唯一基本题材和唯一主要的内容。”但是,若就造型艺术来说,《拉奥孔》的观点却是十分保守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说莱辛通过画与诗的划分为诗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开辟了通往现实的道路的话,那么这种划分对造型艺术的发展来说则是理论的藩篱。
可是,既便如此,即便《拉奥孔》真的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它在文学史以及美学史上闪烁的熠熠光辉却是永远都无法被掩盖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