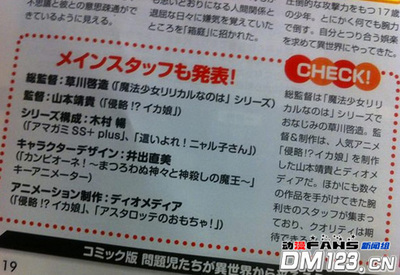不过在我记忆深处更多的还是和这首歌曲有关的一部短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我刚读初中那会儿,中国大地上正流行着街头小报,地摊杂志文学。父亲偶尔也会买一两本杂志看看,我记得有一本杂志叫《淡水》,里面有金庸的《倚天屠龙记》记的片段,(也是后来才知道那是金庸是谁和那部倚天屠龙记),在杂志的后面部分就有这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似乎父亲并没特意把这本杂志收起来,而当年的我还是抱着偷吃禁果的心态来翻阅这本《淡水》杂志和看这个充满暗示《...最后一夜》这篇小说的。憧憬着这篇文章里会有一些露骨煽情的描写。
然而当年的我看完这篇文章时,发现里面并没有太露骨的描写,读完了竟然有些忧伤。隐隐觉得这是一篇深邃的正文,而不是一篇情色艳文。
去年的一天,我特地在网上翻出这部短片小说重看了一遍。读罢小说再听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附《最后一夜》歌词:
踩不完恼人的舞步喝不尽醉人醇酒良夜有谁为我留耳边语轻柔
走不完红男绿女看不尽人海沉浮往事有谁为我数空对华灯愁
我也曾陶醉在两情相悦象飞舞中的彩蝶我也曾心碎于黯然离别哭倒在露湿台阶
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它告别曲终人散回头一瞥嗯……最后一夜
附:小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大姐——-。 化妆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舞娘走了进来,向金大班叫道。金大班正在用粉扑扑著面,她并没有回过头去,从镜子里,她看见那是朱凤。半年前朱凤才从苗栗到台北,她原来是个采茶娘,老子是酒鬼,后娘又不容,逼了出来。刚来夜巴黎,朱凤穿上高跟鞋,竟像踩高跷似的。不到一个礼拜,便把客人得罪了。 童得怀劈头一阵臭骂,当场就要赶出去,金大班看见朱凤吓得抖索索,缩在一角,像只小兔子似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实在憎恶童得坏那付穷凶极恶的模样,一赌气,便把朱凤截了下来。他对童得怀拍起胸口说过:一个月内,朱凤红不起来,薪水由她金兆丽来赔。她在朱凤身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舞场里的十八班舞艺她都一一传授了给她,而且还百般替她拉拢客人。朱凤也还争气,半年下来,虽然轮不上头牌,一晚上却也有十来张转台票子了。
“怎麼了,红舞女?今晚转了几张台子了?”金大班看见朱凤进来,黯然坐在她身边,没有作声,便逗她问道。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朱凤一句话也没说,眼皮盖一直红红的,金大班道,朱凤平日依赖她惯了,这一走,自然有些慌张。
“大姐——-。 朱凤隔了半晌有颤声叫道。金大班这才查觉朱凤的神色有异,她赶紧转过身,朝著朱凤身身上,狠狠的打量了一下,煞那间,她晃然大悟起来。
“遭了毒手了吧?”金大班冷冷问道。
近两三个月,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侨生,夜夜来捧朱凤的场,那个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金大班冷眼看去,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她三番四次警告过她:阔大少跑舞场,是玩票,认真起来,吃亏的总还是舞女。朱凤一直笑著,没有承认,原来却瞒著她干下了风流的勾当,金大班朝著朱凤的肚子盯了一眼,难怪这个小娼妇勒了肚子也要现原形了。
“人呢?″“回香港去了,”朱凤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答道。
“留下了东西了没有?”金大班又追逼了一句,朱凤使劲的摇了几下头,没有作声。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为朱凤可惜,她是为著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好不容易,把这麼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似的,眼看著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朱凤的身价。
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著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那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
“哦——-”金大班冷笑了一下,把个粉扑往台上猛一砸,说道:“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拽抓住半根!。
“他说他回香港一找到事,就汇钱来,”朱凤低著头,两手搓弄著手绢子,开始嘤嘤的啜泣起来。
“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金大班霍然立了起来,走到朱凤身边,狠狠啐了一口,“你明明把条大鱼放走了,还抓得回来?既没有捉男人的本事,裤腰代就该扎紧些呀。现在让人家种下了祸根子,跑来这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一点叫我瞧的上?平时我教你的话都听到那里去了?那个小王八想开溜吗?厕所里的来沙水你不会捧起来当著他灌下去?”金大班擂近了朱凤的耳根子喝问道。
“那种东西——-”朱凤往后闪了一下,嘴唇哆索起来,“怕痛呵——-,。 “哦——怕痛呢!”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她一手扳起了朱凤的下巴,一手便截到她眉心上,“怕痛?怕痛为什麼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朱凤双手掩起面,失声痛哭起来。金大班也不去理睬她,迳自点了根香烟猛抽起来,她在室内踱了两转,然后突然走到朱凤面前,对她说道:“你明天到我那里来,我带你去把你肚子里那块东西打掉……
“啊——-”朱凤抬头惊叫了一声。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的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互护住,一脸抽搐著,白的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愣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的端详著她,它看见朱凤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她鸡蛋的人拼了命似的,她爱上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惜道,要是这个小表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儿了。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的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哭地的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
姆妈好狠心,倒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型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媛,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著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他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干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也一样是肉做的呢。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像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拿去吧,”金大班把右手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掷到了朱凤怀里,“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了。生了下来,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的下的……
金大班说著便把化妆室的门一摔开,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她也没答理,迳自跺著高跟鞋便摇了出去。外面舞池子里早挤满了人,雾一般的冷气中,闪著红红绿绿的灯光,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舞池中一队队都像扭股糖儿似的粘在了一起摇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她回头看时,原来却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专来捧小如意筱红美的。
“金大班,求求你做件好事。红美今夜的脾气不太好,恐怕要劳动你去请请才肯转过来,”周富瑞死捏住金大班的膀子,一脸焦灼的说道。
“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麼请我呢,”金大班笑道。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十桌酒席,怎样?。
“闲话一句!”金大班伸出手来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便摇到了筱红美那边,在她身边坐下,对她悄悄说道:“转完这一桌,过去吧。人家已经等掉魂了……

“管他呢,”筱红美正在和桌子上几个客人调笑,她头也不回就驳道“他的钞票又比别人的多值几文吗?你去跟他说:新加坡的蒙娜正在等他去吃消夜呢!。 说著几个转台子的舞女已经过来了,一个照面便让那群群小伙子搂到了舞池中,贴面婆娑起来。
“喂,小白脸,你的老相好呢?。 金大班正要走开的时候,却发现座上还有一个年青男人没有招人伴舞。 “我不大会跳,我是来看他们的,”那个年青男人嗫嚅的答道。
金大班不由得煞住了脚,朝它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恐怕还是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学生,穿戴得倒十分整齐,一套沙市井的浅灰西装,配著根红条子的领带,清清爽爽的,周身都露著怯态,一望便知是头一次到舞场来打野的嫩角色。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笑盈盈的说道:“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今晚我来倒贴你吧……
说著金大班便把那个扭怩的年青男人拉到了舞池里去。乐队正在奏著“小亲亲”,是一支慢四步。台上绿牡丹红牡丹两姐妹穿得一红一绿,互相搂著腰,妖妖娆娆的在唱著:“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麼你总对我冷冰冰?。
金大班借著舞池边的灯柱,微仰著头,端详起那个年青的男人来。她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清目秀,趣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贴,透著一阵阵贝林的甜香。
他并不敢贴近她的身体,只稍稍搂著她的腰肢,生硬的走著。走了几步,便踢到了他的高跟鞋上,他惶恐的抬起头,腼腆的对她笑著,一直含糊的对她说著对不起,雪白的脸上一下子通红了起来。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很感兴味的瞅著他,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角色才会脸红,到舞场来寻欢竟也会脸红——-大概她就爱上了会脸红的男人,
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她跳舞的时候,羞的连头都都不抬起来,脸上一阵又一阵的泛著红晕。当晚她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她把他的头紧紧的搂进她的怀里,贴在她赤裸的胸房上,两行热泪,突地涌下来。那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疼怜,得到了那样一个羞赧的男人的童贞,一霎那,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的玷辱和亵渎都随著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她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每次她都是偏过头去,把眼睛紧紧闭上的。可是那晚当月如熟睡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著月光,痴痴的看著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
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纤细的腰肢上,她好像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一个赤裸的男体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来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肉体,竟也会那样发狂般的痴恋起来的。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的偎到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青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的望著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於温柔的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著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青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的,柔柔的数著: 一二三——一二三——-
<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