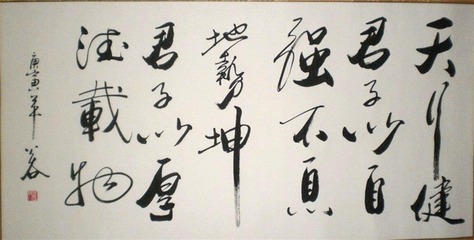在远处看郑鸣的新闻摄影阿城
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人讲了一个科特兹的故事,说某日科特兹到华盛顿广场广场旁边的商店买胶卷,华盛顿广场周围是纽约市立大学,再往南就是快不时髦的苏荷区,科特兹晚年住在附近。故事是,卖货的小姐对科特兹不太礼貌,于是有个年轻人对她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科特兹!
我不满意这个故事角度,它太像无数描写名人的廉价小品。科特兹1894年生于匈牙利,1985年死在纽约。我猜那位小姐卖货给科特兹的时候,科特兹正是美国人所说的脏老头儿的年纪。因此我猜科特兹可能挺高兴,瞧见了一张生动的脸。人不礼貌的时候,生动的可能性最大。科特兹是我喜欢的摄影师之一,其他还有像布列松、布拉塞等许多人,个个精彩。大体说来,他们构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新真实主义。其实是一种对关系本质的把握,简单讲,新真实主义就是对关系的把握不同以往了。摄影最容易被人认为就是真是本身,例如犯罪现场的照片,法律规定它的意义等同现场本身。其实真实是不可能另外有一个本身的。世界上大概为一可以另外有的本身是符号,就像这篇文字,用兰油墨还是用红油墨,用四号仿宋还是用五号仿宋印刷,都还是符号规定的本身。明确了这样一个表达得很罗嗦的前提,我们反而可以获得一种主观的自由,也就是在尊重对象的同时,你有权利自己把握你对关系本质的感应。布列松强调“决定的瞬间”就是不能干预的面临而非摆布对象,由摄影者主观地决定哪一瞬间按下快门,留住决定的瞬间。至于决定了什么,布列松很老实也很真实,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好像知道,但我们每个人知道的都不一样,于是瞬间的意义很丰富,中性的说法是意义不确定。新真实主义美学在映像上的端倪,我倾向于认为是印象派画家德加,德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描绘瞬间几乎就是他的绘画特征:舞蹈,打马球,跨入澡盆的浴女,打哈欠的洗衣妇。而且,相对于古典绘画几何美学的平衡,德加刻意的散漫,一条腿,一只手,一个头,很随便地就被画框切掉了,尊为心灵之窗的目光,随便乱看,不再被统一,德加在描绘瞬间的动作印象。摄影术那时发明了不就,我因此怀疑德加好此道,后来果然有美术史家证明德加有3000多张照片。德加是开放性画面的始作俑者,也是确立瞬间意义的一个人。要知道,当时许多画家也利用摄影,但目的多在于节省模特的摆布时间,而当时的摄影家按绘画的法则调整对象,按下快门。德加1917年去世,科特兹1912年买了第一部相机照布达佩斯街景,布列松1931年照第一张照片,布拉塞1926年认识科特兹,1930年成为摄影师,他们交往认识的人,有康定斯基、夏加尔、毕加索、小雷诺阿、马蒂斯……一句话,德加是上一代的人了,和塞尚一样,暮鼓晨钟,开启了下一代。中国也有一个画家是异数,就是齐白石。1983年北京中国美术馆有齐白石的遗作展,闭幕的那天我自外省赶到,竞走般地看了一圈便到了清场的时刻,往外走的时候心中留住一幅立轴,上画一只鱼头,下描半片鱼尾,自己笑道,条条大路通罗马。
布列松等人对真实的把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流行摄影语言,此中好手辈出。尤其科特兹、布列松等人又大多做过新闻记者,所以现在新闻摄影的质感,几乎都体现了新真实主义美学的特点。所以,我们再来看摆布而成的照片,难免恍如隔世。我还是趁早儿扯到郑鸣的摄影上来。不过有了前面,我们可以轻松了。郑鸣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学的摄影,同届的出了名二的人有富裕,像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一大帮子,各个儿都能横着走。也难怪,“文革”十年,只要敢玩儿政治,哪怕先天不足,也能混出个名堂,是那个世面。文革之后,天下交椅已定,空出的闭场,该另一拨人马踢打了。文化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运了10年气,该发功了。眼花缭乱又是10年。所谓眼花缭乱,是说创新已经成了通行广告语,好像是石英表先起哄,每天领导世界新潮流。创新不易,新的原理出现,才谓之创。试想想水真的往高处流,而且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中国画创新的讨论有不少日子了,久论未决,久试未果,其实是笔墨的原理已经完善得下不进蛆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美术,在造型原理上没有创新,原理已在中世纪和古希腊古埃及确立了,创新的是人文原理,到了19世纪末,因为光学的发现,才由印象派画家群创了造型原理中颜色部分的新,塞尚创的新比较多,所以开启了之后好几派的原理,德加则动摇了构图的平衡原理,由此我们才摸得着古典与现代的造型原理的分界,叹创新二字。

我的印象中,郑鸣很少谈创新,这倒也防他一下。郑鸣听人谈话,眼神儿虚直,过两天儿看他的活儿,心中一惊:这小子反应贼快,焉土匪。
郑鸣毕业后分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又转到中国青年报当摄影记者,又借出去搞了一部电影,幸亏有些麻烦还不能发行,否则也是叫评论界架起来放到创新的火上烤的主儿,他的几个同学都是大闹天宫叫太上老君炼了丹,郑鸣手里慢慢积了不少东西,我知道一定得闹出点儿乱子。果然,1985年他得了一个新闻摄影奖,全国性的。我不知道郑鸣照过签字仪式没有,方正官员和名人在他手里老变样儿。英国女王和她的丈夫神离貌亦不合,刚东张西望一下,咔嚓,郑鸣按了快门儿,安了个“望长城内外”的标题;法国影星阿兰德龙从北京机场候机厅出来,偏头儿向上一望,我估计飞过去一只蝇子,北京不缺小虫儿,咔嚓,郑鸣按了快门儿,说是“阿兰德龙很牛地进入北京”。郑鸣更多的是摄影“人民大众”,加引号儿是因为人民大众在形象上以往一直有个标准,从喜晒丰收粮到捧读红宝书,郑鸣拍的都是引号以外的,往学术上扯,郑鸣有他自己的决定瞬间。别的不说,郑鸣幽默,这一点在他电影学院的同学的作品里几乎找不到,平常聊天儿,一个赛着一个贫,一个比一个损,闹作品的时候,全都哲学了,怪。幽默的品性得有哲学,可哲学是土匪,幽默是焉土匪。郑鸣的作品有新真实主义摄影美学的特征,但不纯粹。布列松他们的作品常常只有地名和年份,看的人会以一种纯粹的眼光去判断,或者说引起全部的经验,而经验又被照片纯粹化了。布列松他不知道决定了什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知道被纯粹了什么,但经验使我们可以讲出无数的东西,不想大学二年级女学生常挂在嘴边儿的“感觉真好”,你问什么感觉,她说就是一种感觉嘛;你问什么好,她说就是好呗。虽说客气,倒有可爱在里头。我不敢说我被郑鸣的摄影所引发的经验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比如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听你讲中国,常说Than’sintorooting,that’swonderful,你别以为真是“有意思”、“奇妙的”,其实他们的意思只是中国人听到什么事儿,说,“嘿,中国的事太天方夜谭,新闻,是刚发生的事儿,还在人的经验过程里,否则是奇闻。”奇闻可要费点儿事儿讲子丑寅卯,所以我理解郑鸣给他的照片加了文字,所以有的照片像电影肿的定格,前后知道了,定格儿的瞬间就知道决定的是什么了。摄影文字其实很不好搞,郑鸣是此中妙手。科特兹有一张照片的标题是“火线之后,戈洛戈利,波兰,1915。照片上是斜对镜头坐在一条横木上的4个士兵,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儿草。仔细看,他们的裤裆都在膝盖处,科特兹写到:我照了一张4个如厕的兵的相,其中一个后来死了,我本来要给他老婆他最后一张照片,可我只有这一张了,她明白并且谢谢我。另外一张的标题是:等船,布达佩斯,1919。画面是8个坐着叙话的妇女。科特兹写道:我绝不为了题材跑好远,它们一般就在我们口儿的台阶儿上。我分析不了这回事儿,人家问我是怎么搞出来的,我不知道:事儿自己会说话。是,郑鸣的东西自己会说话。而且,有人早就隔过这篇文字在看货了。
 爱华网
爱华网